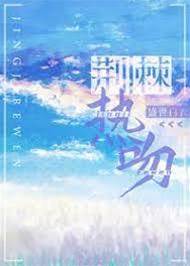《虐愛成癮,他的深情囚籠》 第23章 欠下的債總是要還的
顧墨寒在昏迷的這段時間裏不了學校醫院的診療費用,還在的學生卡裏充值了1w塊錢。
“謝,謝謝你。謝謝你來救我的命,我學生卡裏麵的錢,我會還給你的。”
夏淺眨著眼睛,看著手機屏幕上的餘額,知道天下就不會有免費的午餐。
“恩,你會有機會還的”。顧墨寒推了一下前麵的餐盤,讓快些吃。
最後夏淺實在是吃不下了,向食堂阿姨要了外賣餐盒準備打包拿回寢室。
兩人走出食堂,顧墨寒的車停在不遠。
今天的他的車裏麵沒有司機,是他自己開車來學校的。
可能是真的要辦什麽事才會路過學校吧,夏淺在心裏在麵想著。
夏淺目送著顧墨寒上了車,站在駕駛室的車窗邊,看著他坐上了車,乖巧的向顧墨寒揮手:“再見,路上注意安全。”
Advertisement
“上車。”顧墨寒看了一眼站在車窗外麵的夏淺。
夏淺停下了揮著手的作,瞪大了雙眼:“啊?我這幾天學校還有課,周末前不能回去。”
顧府,從來不會稱那裏為家。
“上車,沒說回家。”顧墨寒接著係上了安全帶。
“哦。你是要帶我出去嗎。”夏淺跑到車子後排,手去拉開車門。
隻聽顧墨寒冷冷的說了句:“坐前麵。”
其實隻是不想離顧墨寒那麽近而已,可被他這麽一說,又隻好乖乖的坐到副駕駛。
夏淺坐上車後係好了安全帶。
顧墨寒一腳油門,帶著駛離了學校。
車子開出離學校一段距離後,顧墨寒找了一僻靜無人的地方停下了車。
夏淺一臉懵的看了一眼車窗外麵,又看了看顧墨寒:“你帶我來這裏幹什麽。”
Advertisement
顧墨寒把車子熄掉了火,接著又把座椅靠背向後調整了一下角度。
他展了一下說:“欠下的債總是要還的。”
說著顧墨寒抬起手,胳膊一便攬過了夏淺的腰。
顧墨寒像是拎著一隻小貓一樣把夏淺抱到自己的上。
此時兩人鼻息相對,又是在這麽僻靜無人的地方。
夏淺明白了顧墨寒此刻要做什麽。
想起昨天晚上的事,臉“唰”一下紅了起來。
其實剛才就在顧墨寒抓起夏淺的手腕,喊疼的時候。那弱的聲音穿他的耳,他裏麵躁不安的那團火就已經被再次被勾起。
直到看著吃完午飯,他都一直強忍著裏的燥熱。
夏淺坐在他上。
顧墨寒的一隻手摟著的腰,另一隻手剛好在的小腹上:“中午吃飽嗎?”
顧墨寒的手放在腰上,把弄的直庠庠。
“恩,吃飽了。”夏淺用力的試圖推開顧墨寒放在腰上的那隻手。
“可我還沒吃飽。”說罷,顧墨寒抬手托住夏淺的後腦便吻上的。
他放在夏淺小腹上的那隻手,慢慢的向上探去。
“唔…唔…顧墨寒…你,你昨天晚上…還…還有今天早上。”夏淺紅著臉,用力的推開顧墨寒。
猜你喜歡
-
完結1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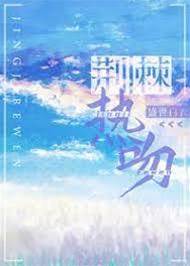
荊棘熱吻
季弦星有個秘密,她在十六歲的時候喜歡上了一個人——她小舅的朋友,一個大她八歲的男人,后來,無論她怎麼明示暗示,鐘熠只當她是小孩。她安靜的努力,等自己長大變成熟二十歲生日那天,她終于得償所愿,卻在不久聽到了他要訂婚的消息,至此她一聲不響跑到國外做交換生,從此音訊全無。再見面時,小丫頭長的越發艷麗逼人對著旁邊的男人笑的顧盼生輝。鐘熠走上前,旁若無人的笑道:“阿星,怎麼見到我都不知道叫人了。”季弦星看了他兩秒后说道,“鐘先生。”鐘熠心口一滯,當他看到旁邊那個眉眼有些熟悉的小孩時,更是不可置信,“誰的?”季弦星眼眨都沒眨,“反正不是你的。”向來沉穩內斂的鐘熠眼圈微紅,聲音啞的不像話,“我家阿星真是越來越會騙人了。” 鐘熠身邊總帶個小女孩,又乖又漂亮,后來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那姑娘離開了,鐘熠面上似乎沒什麼,事業蒸蒸日上,股票市值翻了好幾倍只不過人越發的低沉,害的哥幾個都不敢叫他出來玩,幾年以后,小姑娘又回來了,朋友們竟不約而同的松了口氣,再次見他出來,鐘熠眼底是不易察覺的春風得意,“沒空,要回家哄小孩睡覺。”
51.8萬字8.18 231245 -
完結1232 章

甜蜜來襲,專寵偽裝小蘿莉!
外表天然純,內心大腹黑。可愛像天使,切開是惡魔! 小希兒除了那張臉純真無害,渾身上下都是被寵出來的壞毛病。 爹地媽咪是商業界鼎鼎有名的大人物。上頭還有四位氣質不凡的親哥哥,又是家里唯一的寶貝閨女,簡直各個把她寵上了天。 當真應了那句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可偏偏就是有不怕死竟敢招惹她! 摸她小手就算了,還想親她小嘴!那就別怪爹媽哥哥一塊找上門了。 (前期爹娘寵,后期男友寵,總之就是寵拉~甜不死你算我輸)
109.6萬字8 41130 -
連載1118 章

離婚后,裴總追著求夫人虐
嫁給裴慕白兩年,他疼她寵她,把最好的一切都給她。她沉溺在愛河里無法自拔,他卻一紙協議要跟她離婚。蘇語兮微微一笑,把這幾年對裴慕白的感情全部化作工作的熱情。離開裴慕白的蘇語兮驚艷四座,連裴慕白的死對頭,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某霸總終于坐不住了,單膝跪在蘇語兮面前:“老婆,求你看看我。” ...
195.4萬字8.18 36788 -
完結122 章

強製囚愛,虐錯人後薄總真瘋批了
[女追男 複仇 追妻火葬場 大小姐 雙瘋批](狗血文狗血文非常狗血,別帶三觀看,前男主複仇後女主複仇,女主後期大變樣沒有心,男主骨灰級火葬場,不一定追的到!!!不一定he)那年的池粟,是江城公認的公主,高高在上,呼風喚雨,卻偏偏對一個人偏執入骨,追的人盡皆知。薄宴步步為營,以身入險,設下一場局。眾人都說他厭惡池粟厭惡到了骨子裏,不惜毀了池家毀了她。後來的池粟,是整個江城最聲名狼藉的女人,身無分文,連父親的醫藥費也付不起。池粟心死那天,他正和白月光出雙入對。她剪了婚紗砸了戒指,在雨夜消聲瀝跡。池粟花了十年的時間住進薄宴心裏,卻又在另一個十年裏對他棄之如敝,沒再分給他一個眼神。年少時他被逼著在胸口紋了一個粟字,也成了他一生的執念。誤以為她死後,薄宴瘋了,換上嚴重的心理疾病。再相見,女人一身紅裙,身邊有可愛的孩子,笑的妖豔豔。“薄先生,我從不知虧本的買賣。”他發了瘋著了魔,心甘情願養著她和別人的孩子,隻為讓她留下。後來謊言被一個個拆穿,才知道那才是他的地獄。可沒人知道,那段被埋葬的歲月裏,我對你執念入骨。
20.9萬字8 207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