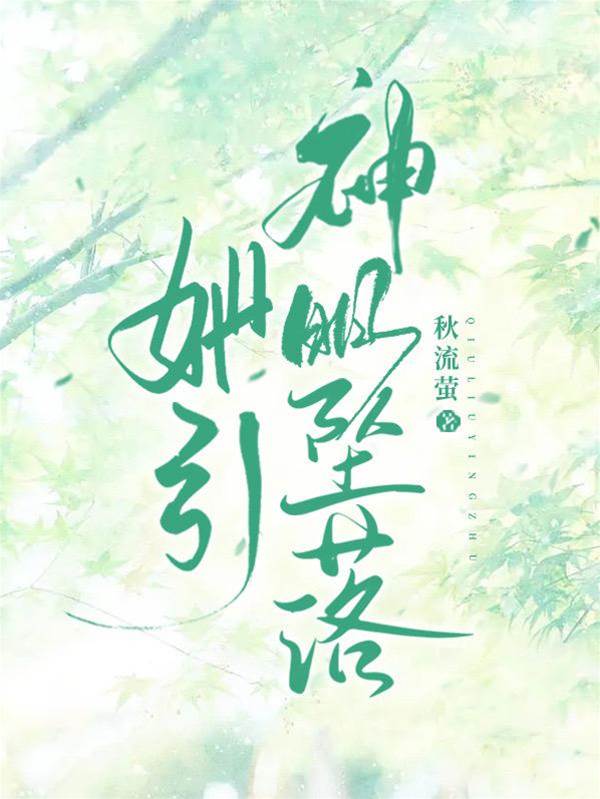《囚她》 第25章
施老夫人原是滿心的擔憂和張,生怕張家有要事,甫一聽見張夫人此言,滿是疑:“親家這說的是什麽話?什麽清清白白,害了你家?”
“我只問老夫人一句話,甜釀的生母王姨娘,到底是什麽個出?是什麽人?”
施老夫人聽得道王姨娘,臉瞬間凝住,當初施存善將王姨娘帶來江都,起先是瞞著府裏人在外頭住了兩年,後來懷胎進了施府,亦是編了個圓借口,前前後後商量了許多遭才點頭。
張夫人怒目盯著老夫人,見老夫人擡了擡下頜,緩聲道:“什麽出?是我兒子從吳江買的妾,家裏還有置妾文書在,夫人這話是何意思?”
“坊間傳的沸沸揚揚,甜釀的生母王姨娘是娼出,去年又跟男人逃家私奔,現在人人都在後恥笑我張家尋了門好親事。”張夫人怒不可遏,噼裏啪啦將一腔怒火掃出來:“我家以禮相待,未曾多計較府上姑娘的出,府上卻坑蒙拐騙,做了套誆我家往火坑裏跳。當初換庚帖、下聘書時,冰人也在場,府上如何說的,說孩兒的生母是正經人家出,家中蒙難才委為妾,品行不虧,我心中也納悶,正兒八經的妾室哪會是那個模樣打扮。去年上元節王姨娘被擄,我家還幫著找關系,到去尋人,府上卻支支吾吾,拖泥帶水的,如今想來,怪不得!怪不得會如此!這是把我家當冤大頭宰。”
“我家一家上下,俱是明磊落,坦坦,不曾害人半分,老夫人,你捫心自問,在兒親事上這般欺人騙人,這樣有傷鷙的事,如何能做的出來?”
施老夫人聽得說此話,心突突一跳,氣上湧,頭昏耳鳴,一口氣未曾提上來,堵的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巍巍被桂姨娘扶坐在椅上順氣。
Advertisement
“夫人,夫人……我家老夫人年歲已高,不得氣,您這話說的實在令人心寒……請夫人坐、坐,有話好好說,慢慢說……”桂姨娘喚圓荷端茶遞水,要鼻煙壺。
施老夫人氣的面鐵青,半晌才朦朦朧朧看見眼前人影,將邊一圈人都喝退下去,嘶啞著嗓子道:“親家是從哪來的風言風語,直怒氣沖沖的撞進來,我施家在這哨子橋下住了三四十年,誰不誇我家生意誠信,為人本分,在親家裏,如何又了坑蒙拐騙之徒。”
張夫人冰著一張臉,亦是臉可怖:“此話街坊都已傳遍,空來風,句句在理,難不還有假。”
桂姨娘帶著屋裏的嬤嬤婢子都退在外頭廊下,聽著裏頭靜,心頭琢磨了一回,有些暢意,細想又覺得懾人,連忙喊了個婢子:“去見曦園尋大哥兒來。”
“親家說的外頭流言,我施家上下從未有一人聽過,王姨娘是我兒納的妾,有正正經經的納妾文書,在我們施家就是正兒八經的良家婦人,我家一句謊話也沒有。當初是親家請冰人上門提的親,先要問的是子四行,我們養兒,最要的也是品德行,我家這孩子,親家也千百般端詳過,又左右打聽過,的長短,人相問的那些話,一五一十,我家句句屬實相告,三書六禮,樣樣都是依著時禮來,又何來坑蒙拐騙之說?”
施老夫人深吸了一口氣:“婚事在即,親家氣沖沖來詰問的生母,又是什麽意思?流言傳的沸沸揚揚,可有憑有據?是從哪裏傳出來的?”
張夫人聽言心中生出一不妥,轉念一想又不對,正要辯駁,外頭進來兩人,一是施連,一是張圓。
張優見自己母親怒火攻心往施家來討個說法,怕生什麽事,連喊人去找張圓,張圓匆忙趕來,正遇上從見曦園出來的施連,兩人一言未置,急忙忙往施老夫人屋裏來。
Advertisement
“夫人不過聽進去一兩句流言,不辨真假,就氣沖沖的趕來討說法,心頭還是看不起我家,看不上我妹妹是個妾生的,看不起我家是個俗氣商戶,高攀不上府上。”
施連拂袖進來,聲音冰冷,一雙眼雪一樣亮,從張夫人面上掃過:“張夫人就這樣跑來,要把甜姐兒置于何地?是不打算娶了?”
張圓急的滿頭是汗,先向施老夫人作揖,再去拉自己母親:“母親如何在這時糊塗,外頭的話如何能信……”
“如真是世清清白白,正正經經的良家子,我家自然娶……”
施連冷笑一聲:“什麽是清清白白,什麽是正正經經,這世上誰生下不清白正經,份有三六九等,人也分三六九等麽?仗著你們是半拉子的書香門第,就高人一等,清顯些?不分青紅皂白,張口就來,順意趾高氣揚,逆水搖尾乞憐,這就是讀書人的風骨和典範?”
“大哥,大哥……請恕我家無禮之罪。”張圓見屋氣氛劍拔弩張,左右揖手陪不是,拉著自己的母親就走,“母親,母親我們回家去。”
張夫人臉這時也有些不好,一不坐在椅上,半晌道:“王姨娘…… ”
“是有心人故意說這些話以洩私憤,也許是看我施家生意興隆,也許是看貴府上喜事連連……這倒要夫人回去好好想想,是不是近來風頭太大,招惹了什麽人給自己添堵。”施連將嫁妝單子拋在張夫人手邊:“我家妹妹這樣的容貌品德,這樣的嫁妝單子,若不是早定了親,還到你家來挑揀?”
施老夫人低頭喝茶,施連冷意蓬,張圓愧無,張夫人愣愣看著手邊的單子,滿室寂然,張夫人還未回過神來,簾進來一人:”祖母。”
Advertisement
甜釀也是匆匆而來,鬢角還散著,趿著雙月白的繡鞋:“祖母。”
“你怎麽來了?”
跪在施老夫人前,神黯然:“祖母……甜釀求祖母……把這婚事退回。”
“甜妹妹!”張圓面煞白,“不能退婚。”
甜釀轉面對張夫人,端端正正的行了個禮:“我的婢正看見夫人急匆匆來,我擔心有事,來祖母這看看,略聽了幾句話。”
”承蒙府上看得起甜釀,聘做新婦,甜釀心頭也一直視夫人如親人,盼著早日對舅姑盡孝,扶持夫婿,闔家滿度日,夫人在外頭聽的那些流言,真真假假,外人不盡知,但甜釀有些話說。”
“我是七歲上下,和姨娘一道被爹爹帶回江都的,此前一直都在吳江生活。孤兒寡母,居人籬下,全靠著善心人接濟才賴以存活,您從坊間聽來的話,可能真是空來風,姨娘相貌好,又熱鬧,但其實本純良,命又苦,為了一點活計,常被浮浪子弟欺侮,也無訴苦,人言可畏,裏的污水說潑就潑,不花一點兒力氣,只要有一人說不潔,三人虎,什麽煙花子,風月之地,捕風捉影,沒完沒了,永不得翻,但姨娘若真是那樣的人,我爹爹,祖母,整個施家又豈會真心對,這麽多年又豈能安安穩穩的生活。”
“去年被賊人擄去,甜釀是眼睜睜看著那賊人將姨娘拖在水上,是私奔還是被擄,只有姨娘和那賊人才知道真相,但在施家有兒有,有家有業,不盡的福,又何必跟人去私奔,我們尋不到,也怕尋到時,被賊人拐在煙花之地,前半生過的辛苦,難道後半生也要凄涼度日,祖母和家裏的苦衷,甜釀都知道,說自欺欺人也好,說心存僥幸也罷,我日日夜夜只求上天保佑,保佑我的姨娘遇上個好心人,過上好日子。”
Advertisement
“但無論如何,無論是以前日子的欺辱,還是可能淪落至煙花之地的悲慘境地,這都不是姨娘的錯,也是孤苦無依,被人害,被人,這世道容不得一個鮮亮服,說話熱鬧的獨子,但若有朝一日回來,還是我的娘親。我請祖母退婚,不願因我的生母的事損傷府上清譽,給人笑柄,以後圓哥哥走的遠,我也不願牽累他。”
轉向施老夫人:“祖母,我施府不過數年,在您邊盡孝日短,我也想在祖母邊多待幾年,共天倫之樂。”
又轉向張圓,無語凝噎,深深一斂衽,而後對施連道: “大哥哥,夜深祖母要歇了,能否請大哥哥送夫人和圓哥哥家去。”
話語完畢,不看屋人,扭頭轉向一盞銀燈。
張圓聽話語,已是癡了,心又憐又酸,思緒萬千,再見影,煢煢獨立,孤單伶俜,幾番哽咽:“甜妹妹……”
沒有面對任何一個人,而是對著一盞孤獨的燈,銀釭高照,點燈如豆,剪出薄薄的一個影,因來的匆忙,上披著件出爐銀的春衫。
出爐銀,那是種極其微妙的,銀水燒出爐的彩,被高溫灼燒的白裏夾帶著一縷淡淡的,淺白紅,自銀水裏洗出的淡紅,清而不寡,像人,又親切,卻不可太過狎昵。
施連要送客,張圓淚已先下:“我非妹妹不娶,明日再來和妹妹賠罪,也求妹妹不要退婚……”
人已遠去,甜釀默默的轉,去扶施老夫人:“祖母,我扶您回房歇息。”
施老夫人拍拍的手:“你方才那些話……”
“世上沒有不風的牆,總會有人知道,總得先說些什麽……”甜釀答道,“ 因我的事,讓祖母心累,我一萬個不安心。”
服侍淨面浣手,卸下釵環,等施老夫人安穩睡下,才落下簾子,換了圓荷值守,自己回繡閣去。
出來見施連在外頭游廊下站著。
這是暖春的夜,風是暖綿綿,潤的草木的青氣息,蟲鳴,星和紫的天幕。
“嫁他,就那麽好嗎?”他擡頭看著月,淡淡問,“就值得妹妹這樣用心良苦。”
“總要嫁的不是嗎?”也微笑,手,裳和月融為一。
張夫人母子兩人出了施府,門外有家人等候,見張夫人神木然,張圓失神落魄,召喚母子兩人上車。
張夫人被這一頓鬧的生氣全無,只覺無地自容,又覺得有些地方有些奇怪,張圓怪自己母親無理取鬧:“明兒再來給老夫人賠禮道歉吧。”
第二日一早,甜釀向施老夫人請願,要去廟裏小住數日:“想找個清靜些的山寺散散心,隔幾日就回來,祖母就應了我吧。”
施老夫人道:“張家再來……”
“就請祖母做主,看著辦吧,能在祖母多待幾年,最好不過。”
該有的敲打不可,免得嫁過去後再吃苦頭,也必得殺殺張夫人的氣焰。
甜釀在繡閣收拾,昨夜苗兒和同睡,知道張夫人匆匆來,又匆匆去,再看甜釀回來倒頭就睡,這會終于忍不住問:“到底出了什麽事,要去廟裏住?”
甜釀搖搖頭:“也沒什麽。”
帶走兩個新婢,把寶月留下:“你在府裏好生待著,把書箱裏的書都拿出來好好曬一曬,太落山收回來。”
張家請了族裏的尊老來施家說話,又帶了不禮,連張遠舟都親自上門來致歉,施老夫人冷了幾日才轉圜,張圓不見甜釀,只說二小姐不在家,也不知道去了哪兒,好不容易私下找到寶月,聽說是甜釀去了寺廟裏小住。
甜釀也沒打算避他,見了來人:“圓哥哥這幾日可好?”
他黯然的點點頭,聲音嘶啞:“我只怕妹妹不好。”
給他斟茶:“我很好,只是在家住煩了,出來散散心。”
他坐了半晌,說了好一會話,甜釀撐著頭顱,懶懶的不說話,兩人去後林走走。
“母親行事魯莽,我亦未曾料到,這幾日家裏人也勸了許多,母親也知愧,恨不得親自向妹妹道歉,妹妹這回就原諒吧。”
“甜釀對夫人,心中向來敬重,從來未怪過。只是經此一事,彼此心中有了芥,以後再如何修補,也是有了隔閡。”嘆氣。
“我會好好護著你,絕不讓你半分委屈,我的心始終是向著妹妹的。”張圓看著,“明年秋闈,我要專心念書……父親有座小宅子,我去看過,略簡略些,但很清幽,離府學很近,我和家裏說,婚後我們搬去住好不好。”
“可以嗎?”笑盈盈的,“這樣似乎不太好?”
“可以的,我有辦法。”他握住的手。
欣喜的點頭,目盈盈的看著他,抓住他的袖子,青的年郎,眼淚像水一樣澄淨,像桃花瓣一樣和,手,微涼的手指輕輕上他的瓣,輕聲道:“圓哥哥。”
桃花正豔,杏花初放,風熏草暖,他慢慢俯低,只有經過磋磨的才愈加濃烈,的攀著他肩膀,將柳腰搦在他手下:“郎哥哥。”
他第一次初嘗脂滋味,是一種芬芳又清淡的香,回味無窮,那香甜之後,是甜的,溫熱膩的舌,巍巍在他齒間,需要他的憐。
洶湧的浪無法抑制,肆意拍,最後都化作舌尖的一點閃亮銀線,來回勾勒著彼此齒的模樣。
願有人終眷屬。
“想要快點把你娶回家。”
有一雙單薄的眼在杏林一晃而過,停在外頭的馬車緩緩啓,蹄聲粼粼,敲在潤的青石板地上,一聲聲,一聲聲……
猜你喜歡
-
完結428 章

年代甜炸了:寡婦她男人回來啦
(全文架空)【空間+年代+甜爽】一覺醒來,白玖穿越到了爺爺奶奶小時候講的那個缺衣少食,物資稀缺的年代。好在白玖在穿越前得了一個空間,她雖不知空間為何而來,但得到空間的第一時間她就開始囤貨,手有余糧心不慌嘛,空間里她可沒少往里囤放東西。穿越后…
97.7萬字8 28516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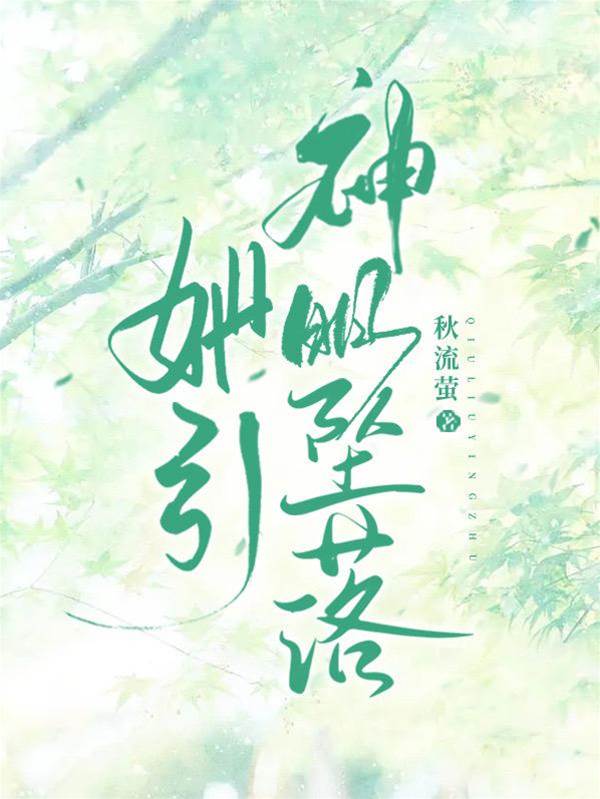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221 章

春意入我懷
【大學校園 男二上位 浪子回頭 男追女 單向救贖】【痞壞浪拽vs倔強清冷】虞惜從中學開始就是遠近聞名的冰美人,向來孤僻,沒什麼朋友,對前仆後繼的追求者更是不屑一顧。直到大學,她碰上個硬茬,一個花名在外的紈絝公子哥———靳灼霄。靳灼霄這人,家世好、長得帥,唯二的缺點就是性格極壞和浪得沒邊。兩人在一起如同冰火,勢必馴服一方。*“寶貝,按照現在的遊戲規則,進來的人可得先親我一口。”男人眉眼桀驁,聲音跟長相一樣,帶著濃重的荷爾蒙和侵略性,讓人無法忽視。初見,虞惜便知道靳灼霄是個什麼樣的男人,魅力十足又危險,像個玩弄人心的惡魔,躲不過隻能妥協。*兩廂情願的曖昧無關愛情,隻有各取所需,可關係如履薄冰,一觸就碎。放假後,虞惜單方麵斷絕所有聯係,消失的無影無蹤。再次碰麵,靳灼霄把她抵在牆邊,低沉的嗓音像在醞釀一場風暴:“看見我就跑?”*虞惜是凜冬的獨行客,她在等有人破寒而來,對她說:“虞惜,春天來了。”
39.6萬字8.18 627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