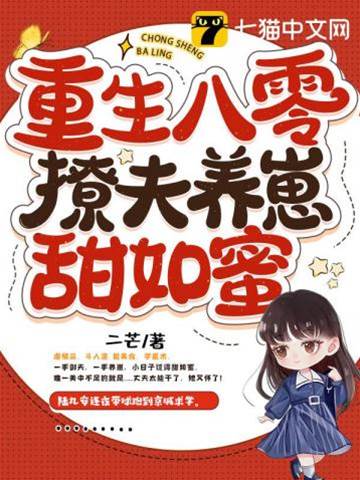《情陷京港》 第1卷 第23章 夜色撩人
左庭樾纖細的腰肢,手上使力,潯鳶吃痛,離開他的,拉扯出勾纏的曖昧。
“潯潯”
他低聲喊的名字,低沉的嗓音著的沙啞。
聲音落潯鳶耳中,漾在耳廓,然后,像是石子墜湖底的靜,叩響心房,睫跟著,格外的人心弦。
左庭樾的手指靈活地解開旗袍的盤扣,這次沒撕,他有耐,是調。
一層一層剝開花,看花枝在風的輕下,最后,瞧見里面人的風景。
他低頭在面前,極盡攀纏。
烏黑的長發凌點綴在男人的頸間,黑與白的視覺沖擊,曖昧難明。
“……別”
潯鳶挨不住,急促又低弱的聲音,全然不復清冷沉靜,聽起來,又無助。
“什麼別?”
低沉的嗓音到讓人耳朵懷孕,是,陷在漩渦里的。
他作沒停,不斷流連在雪白的上,這種時候,很難說,他不是故意這麼問的。
潯鳶纖細白的脖子努力躲開他,得以息,見針。
“……別這樣”
回應潯鳶的是一聲短促的笑意和愈漸猛烈的靜。
腦海里的思緒越發混,潯鳶覺得自己像是漂浮在云層上,腳底綿綿的,落不到實,偏生周又火燒火燎的,烈火焚,也不過如此。
Advertisement
夜人。
潯鳶覺得自己要瘋。
被他磨的。
……
汗水浸鬢角的頭發,粘在酡紅的臉蛋。
一片混中,男人沙啞暗沉的嗓音響起,伴隨著他牽引潯鳶的手落在扣子上。
“幫我解開。”
磁的聲音落在潯鳶耳畔,反應遲鈍,抬起那雙乎乎的眸子看他,沁了的淚,盛在漂亮的眼里,綽態,嫵嬈。
的風,無需故作姿態。
左庭樾眼底的暗更濃,雜的深淵,稠艷到滿溢。
潯鳶被燙到,眸,后知后覺懂他的話。
“……別”
還是這個字,大腦遲緩,一時也說不出別的話。
比這方面的臉皮,潯鳶還是比不過他。
他玩兒的太野。
……
最后的最后,是怎麼樣結束的呢?
潯鳶一點也不想回憶,太。
只記得,到后面太疲倦,昏昏沉沉的睡過去了,一覺醒來已經是第二天。
邊的位置已經泛涼,潯鳶了然,男人走了有段時間了。
起床拉開窗簾,港城的雨停了,推開窗,意彌漫,撲打在臉上,乎乎的。
酒店的地理位置夠好,登高而俯瞰大片江景,港城最繁華的景盡收眼底,那種萬都在腳下的覺,很難不令人生出野心和豪。
潯鳶見的多了,心中生不出一波瀾,生來就立于群山之巔,于而言,風景就只是風景。
Advertisement
穿長睡,頭發散落在腦后,發尾微卷,剛起床,面上還帶著懶倦,眼底的澤淡然平靜,目看著遠方,眉目如畫,染著點春的余味,襯得那張臉萬般嫵。
等大腦徹底清醒過來,潯鳶出酒店,沒回淺水灣,去的是工作室,新接的文修復的工作還沒做完,得抓時間。
一整天的時間,潯鳶都待在工作室里,忙著修復文,就連午飯都是在工作室解決的。
晚上回到淺水灣,理國外的郵件,期間,接到一個國外的來電。
備注是:丫頭。
起走到客廳的落地窗前,接通電話。
——“我在忙工作呀。”
——“你想要什麼禮?”
——“短時間沒辦法回國看你了,等我閑下來就去國外找你好不好?”
和對面的人說話,語氣稔,話語里出來的都是親昵,聲音很溫和,像是在哄小孩子。
落地窗的鏡子明亮干凈,上面投出致的面容,是難得的溫婉約,是那種難得一見的平和模樣。
毋庸置疑。
電話對面的人,對一定很重要。
那邊的人不知道說了什麼,潯鳶眉尖微,皺了皺。
“老實在國外呆著,等我回去看你,聽管家伯伯的話。”
哄幾句,潯鳶才掛斷電話。
Advertisement
看著黑屏的手機幾秒,翻出一位聯系人,撥過去。
電話響過幾聲,接通。
“老板”
是一道干凈好聽的男聲,聲音謙和。
“他們在國外的業務有什麼變化嗎?”
“沒有明顯的變化,只是他們在接東南亞那邊的礦場主,我猜測是原料出什麼事了或者他們在開拓第二條產業鏈。”
潯鳶默默聽著,手指搭在胳膊上,不住地輕點,眼神在夜中深沉淡靜。
“繼續盯他們,另外,找人和東南亞那邊的人接,無論他們是什麼目的,我要那批礦石原料。”
潯鳶頓了頓,又說:“金三角地帶,找人查一下……”
突然停住,握著手機的手收。
“先不用查。”
那一道男聲話語很堅定,執行力很強的覺。
“我明白,老板。”
潯鳶掛斷電話,突然有一點疲憊,看一眼時間,十一點,已是深夜,難怪覺得有點疲倦。
之前還想要不要再開家店,這個不的想法在今晚徹底掐斷,必須讓它夭折在搖籃里。
潯鳶理好工作后去臥室休息,這一夜,或許是因為睡前提到,久違的畫面再次出現在腦海中。
暴雨如注。
鮮淋漓。
有人從遠追來,像是瘋狗一樣,不要命地追趕們,潯鳶只能拼命地奔跑。
Advertisement
“別讓那小娘們兒跑了。”
“分開找。”
“東西沒找到,肯定在那兒小娘們兒手里。”
潯鳶在夢境里,能夠清晰地聽到他們的話。
“踏馬的,人呢?”
……
黑暗中,潯鳶猛然睜開眼,又是這樣。
他們到底在找什麼呢?
潯鳶不知道。
夢到過許多次那天的場景,可確定沒有他們口中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呢?
潯鳶覺得頭疼,每次夢到那件事醒來后,當晚就別想再睡。
在嘗試睡無果后,潯鳶坐起來,開燈,房子空的,覺得沒意思。
沉思幾秒后,果斷換服,拿車鑰匙出門。
猜你喜歡
-
完結1722 章

快穿之女配功德無量
從混沌中醒來的蘇離沒有記憶,身上也沒有系統,只是按照冥冥之中的指引,淡然的過好每一次的輪迴的生活 慢慢的她發現,她每一世的身份均是下場不太好的砲灰..... 百世輪迴,積累了無量的功德金光的蘇離才發現,事情遠不是她認為的那樣簡單
292.3萬字8 27087 -
完結719 章
穿書後我成了娛樂圈天花板
一覺醒來,秦暖穿成了虐文小說里最慘的女主角。面對要被惡毒女二和絕情男主欺負的命運,秦暖冷冷一笑,她現在可是手握整個劇本的女主角。什麼?說她戀愛腦、傻白甜、演技差?拜拜男主,虐虐女二,影后獎盃拿到手!當紅小花:「暖姐是我姐妹!」頂流歌神:「暖姐是我爸爸!」秦家父子+八千萬暖陽:「暖姐是我寶貝!」這時,某個小號暗戳戳發了一條:「暖姐是我小祖宗!」娛樂記者嗅到一絲不尋常,當天#秦暖疑似戀愛##秦暖男友#上了圍脖熱搜。秦暖剛拿完新獎,走下舞臺,被記者圍住。「秦小姐,請問你的男朋友是厲氏總裁嗎?」「秦小姐,請問你是不是和歌神在一起了?」面對記者的採訪,秦暖朝著鏡頭嫵媚一笑,一句話解決了所有緋聞。「要男人有什麼用?只會影響我出劍的速度。」當晚,秦暖就被圈內三獎大滿貫的影帝按進了被子里,咬著耳朵命令:「官宣,現在,立刻,馬上。」第二天,秦暖揉著小腰委屈巴巴地發了一條圍脖:「男人只會影響我出劍的速度,所以……我把劍扔了。」
69.3萬字8 47376 -
完結94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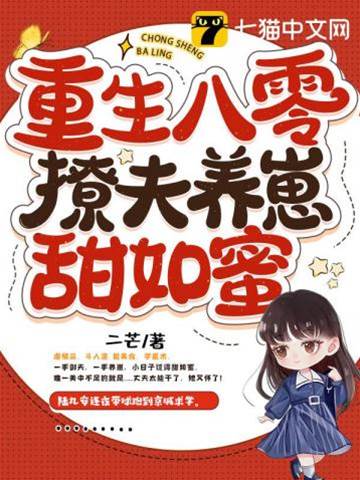
重生八零撩夫養崽甜如蜜
一場綁架,陸九安重回八零年的新婚夜,她果斷選擇收拾包袱跟著新婚丈夫謝蘊寧到林場。虐極品、斗人渣。做美食、學醫術。一手御夫,一手養崽,小日子過得甜如蜜。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丈夫太能干了,她又懷了!怕了怕了!陸九安連夜帶球跑到京城求學。卻發現自己的丈夫站在三尺講臺上,成了她的老師!救命!她真的不想再生崽了!!
174.3萬字8.18 74899 -
完結711 章

高考首富身份曝光,攻略高冷學姐
[都市日常](偏日常+1V1+無系統+學姐+校園戀愛)(女主十章內出現) “兒子,你爸其實是龍國首富!” 老媽的一句話直接給林尋干懵了。 在工地搬磚的老爸
123.7萬字8.33 18213 -
完結242 章

圓橙
直到離開學校許多年後。 在得到那句遲來的抱歉之前。舒沅記憶裏揮之不去的,仍是少年時代那間黑漆漆的器材室倉庫、永遠“不經意”被反鎖的大門、得不到回應的拍打——以及所謂同學們看向她,那些自以為並不傷人的眼神與玩笑話。她記了很多年。 而老天爺對她的眷顧,算起來,卻大概只有一件。 那就是後來,她如願嫁給了那個為她拍案而起、為她打開倉庫大門、為她遮風避雨的人。 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從來屢見不鮮。 連她自己也一直以為,和蔣成的婚姻,不過源於後者的憐憫與成全。 只有蔣成知道。 由始至終真正握住風箏線的人,其實一直都是舒沅。 * 少年時,她是圓滾滾一粒橙,時而微甘時而泛苦。他常把玩著,拿捏著,覺得逗趣,意味盎然。從沒想過,多年後他栽在她手裏,才嘗到真正酸澀滋味。 他愛她到幾近落淚。 庸俗且愚昧。如她當年。
36.8萬字8 103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