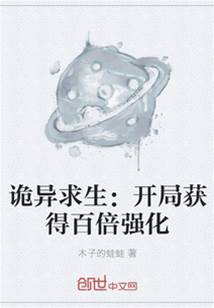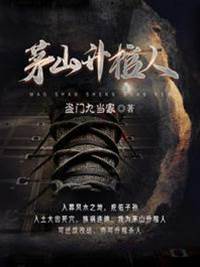《黑水屍棺》 第十六章 怪鄰居
當然,從始至終,我爸都沒見過小張口中的老居士。
那天,劉尚昂他爸開著車駛進郵局家屬院的巷子口時,已經過了上班點,巷子裡原本一個人都沒有,可就在車開過衚衕拐角的時候,我卻看見車後有一個人,一個穿著大紅子、頭髮很長的人,背對著我,我看不清的樣子,隻知道是一個人。
看到的時候,我總覺得有點不對勁,可也說不出是什麼地方不對勁。
家屬院一共有四棟樓,每棟三個單元,我的新家就在第四棟樓的二單元二樓。劉尚昂他爸幫我們把行李搬上樓之後,就說廠裡還有事,急匆匆地走了。我爸媽送走劉尚昂他爸之後就開始收拾屋子,我沒什麼事乾,就在新家裡逛了起來。
看得出來,這間房也有些年頭了,暖氣卻是新裝不久,上麵綠綠的新油漆和整個房子的陳舊格格不。屋子裡的傢是現的,我爸將我們家的老電視放在了客廳的櫃子上,然後就開始拭客廳裡的舊沙發。
按說以我爸湊到的那些錢,是租不到帶傢的房子的,更何況在那時候,在這種家屬院裡,很有人會把自己的房子租給外人住。可這套房子不但租金低、傢全,而且沒有任何抵押金。這也讓我爸更加確信,郵局家屬院,的確是一個難得的吉地。
電視還沒接通天線,我滿心無聊,就來到朝南的臺上,靠著窗戶向外張。
那時候的樓房普遍不高,我們家雖然在二樓,可依舊能有很好的採。太有點刺眼,我把手搭在額頭上擋著,然後就從餘看到樓下有一片很重的。我就朝著窗戶下麵看,可看到的景象,卻讓我渾難。
一片漆黑,我所看到的,就是一片漆黑。
Advertisement
我們樓下就是一樓,郵局家屬院的一樓都有一個很大的院子,在別人家的院子裡,都種了一些花花草草,看起來也舒服,可我們樓下的那一家,院子上方卻支起了一個很大黑布,將整個院子都遮了起來,而且那黑布很厚,連都照不進去。
我心裡就奇怪了,什麼樣的人會在院子裡張起這樣一塊布,好像生怕太照進他家院子裡似的。
這時候我媽也來到的臺上。臺上有一個很大的櫃子,我媽本來是想將一些暫時穿不著的厚服放進去,看見我站在窗戶跟前發獃,就問了我一句「,在這幹麼呢?」
我指著樓下的那塊黑布「媽,你看,他家院子都用布遮起來了。」
我媽也湊到窗戶上看了一眼,頓時皺起了眉頭「誰家會在院子裡掛黑布啊,怪不吉利的。」
我爸正著沙發,聽到我媽的話,就遠遠喊道「之前房東說了,咱們樓下那家有人得了白化病,不能曬太。你們娘倆別在窗戶跟前議論,讓人聽見了不好。」
就在我爸說話的時候,我看見那個穿紅子的人進了一樓的院子,雖然看得不是太清楚,但我能確信,走路的時候,是背對著院門,倒著走的。
我還是頭一次聽說白化病,心想,得了這種病的人難道不不能曬太,難道連走路都要倒著走?而我也終於想明白為什麼覺得那個人奇怪了,那天太不大,但我見到的時候,卻打著一把很大的黑雨傘。
不過既然白化病不能曬太,打著傘,似乎也能說得過去吧。
而當時的我也不知道,得了白化病的人雖然麵板比常人更容易被太灼傷,但並不像傳言中那麼怕,他們頭髮的彩,也都是漂亮的白或者金,可那個人,卻有著一頭純黑的長髮。
Advertisement
我爸和我媽一直從中午收拾到晚上,吃過晚飯後,爸媽很早就睡了,而我也有了人生中第一個獨立的小臥室,裡麵有一張寫字檯,上麵放著老柴頭給我的那些小玩意兒,在靠牆角的地方還有一張小床鋪,屋子很小,除了寫字檯和小床,屋裡幾乎沒有太多空閑的空間了。
老柴頭的小玩意兒都是我的寶貝,我隨手拿了一個木頭雕的小馬,將它放在枕頭邊上,好像這樣一來,老柴頭就在我邊了似的,說真的,經歷過那些事以後,讓我一個人睡我還真的有些害怕。
我躺在床上,腦子裡就不斷想著老柴頭給我講過的那些故事,還有老柴頭曾經為我做的那種濃湯,想著想著就睡著了。
這一覺我睡得很不踏實,總是在床上翻過來翻過去,迷迷糊糊中,就覺上很難,天明明很熱,我脖子裡全是黏黏的汗,可上流著汗的同時,我又覺有點冷,窗戶關著,可總能覺到一陣陣冰涼的風吹進來,那種風不讓人覺得涼爽,反而給人一種很悶的覺。
不是悶熱,就是單純的悶,就好像有一口氣憋在口,呼不出來,也咽不下去。
就在這時候,窗戶突然被什麼人敲響了,發出一陣「咚咚咚」的聲音,我一下就清醒過來,心裡一陣一陣地發。
我們家可是在二樓啊,可那聲音,明明就是從窗外傳來的!
我不敢睜眼,怕又看到什麼嚇人的東西,就用手抓著老柴頭給我的小木馬,閉著眼,裝睡。
老柴頭曾經對我說過,如果遇上邪祟,最好的辦法就是在它發現你的之前逃走,一旦被發現了,肯定是逃不掉的,這時候千萬不要慌,該做什麼做什麼,就當它不存在,如果邪祟不是太兇,你不理它,通常來說,它也不會把你怎麼樣。
Advertisement
可外麵的人還在不停地敲著窗戶,我的心撲通撲通跳個不停,上流著汗,手腳卻早就涼了,隻有手裡的小木馬,彷彿正散發著一暖意,讓我安心。
直到清晨的快要照進屋子的時候,敲窗戶的聲音才消失,我趕從床上爬起來,逃命似地跑進了我爸媽屋裡。
搬家之前,我媽就提前聯絡到了一份清早送牛的工作,畢竟廠裡效益不行,加上又欠著一屁外債,總還是要想辦法賺些錢的。
這天我媽起得很早,見我一臉著急地進了臥室,就問我「,怎著了?」
我心裡還在後怕,口齒不清地說「有……有人敲我窗戶!」
我爸也被我吵醒了,睡眼惺忪地從床上坐起來,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媽一眼,迷迷糊糊地說了句「幹麼呢,大清早的。」
我媽沒理會我爸,隻是問我「有人敲窗戶?怎著回事啊,慢點說。」
我吞了口唾沫,過了半天,才很勉強地對我媽解釋「昨天晚上,有人在外麵敲我屋窗戶。」
我爸和我媽對了一眼,幾乎是同時意識到了事不對勁,我爸趕下床,著腳跑到了我的臥室,我媽也跟著過去了。
本來我是打死都不想回那個古怪的小臥室的,可又不敢一個人待著,也跟在我媽後跑了過去。
我爸進了我屋裡之後,第一件事就是開啟窗戶朝外麵看,就看見一樓和二樓間的牆筆直筆直的,除了牆上附著幾電線,本沒有落腳的地方。
我媽也湊到窗戶前向下看,這一看,臉刷的一下就白了。
窗戶外麵是無法站人的,既然無法站人,那昨天晚上敲我窗戶的,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我爸關了窗戶,一臉懊惱地坐在我的小床上,低著頭,也不知道在想什麼。
Advertisement
我媽的第一反應是怕,過了一會,又埋怨起了我爸「都是你,怎麼就不聽柴大爺的話呢,這才搬過來一晚上,就又上了那東西,這以後的日子,可怎著過啊!」
我爸重重地嘆了口氣,終究也沒說什麼。
而我媽,也沒再繼續埋怨下去。我媽知道,我爸之所以沒有搬到汽車站附近,一方麵確實是因為對老柴頭有心結,但更多的,則是為了我的學業。
我爸沉默了一陣子,就催著我媽去上班,我媽還是有些不放心,可我爸讓我媽安心幹活,他有辦法。
在當時的我和我媽看來,我爸肯定是要去找老柴頭了,反正不管到什麼事,隻要老柴頭來了,就肯定能解決,正是因為對老柴頭的這份信任,讓我媽打消了一些顧慮,收拾一番之後就去上班了。
快到七點的時候,我爸簡單做了頓早飯,又讓我穿好服,帶著我一起上班。
那時候廠裡管得不嚴,帶著孩子進廠,隻要不進車間,是沒人管的,所以我過去也跟著我爸去過幾次橡膠廠。不過那地方無聊的很,加上這些年效益不好,廠裡的大人總是一張心事重重的臉,我特別不願意見到他們。
可又想著很快就能見到老柴頭了,我心裡就格外高興,更讓我高興的是,那天劉尚昂也跟著他爸來到了廠裡,我有了玩伴,自然把那些煩心的事拋在了腦後。
廠裡也沒什麼可玩的東西,雖然在廠院後麵有一些碎石頭堆、沙子堆可以玩,可那地方是不讓我們進的,我和劉尚昂就趴在樓道的欄桿上聊天。
小孩子之間的聊天,大多圍繞著電視,聊到最近電視上播的畫片時,還會很即興地進行一次角扮演,我當擎天柱,劉尚昂就當威震天,要麼就是我當蠍子,劉尚昂當葫蘆娃,分配好角之後,兩個人就在辦公室外的樓廊上追逐瞎鬧。
猜你喜歡
-
完結82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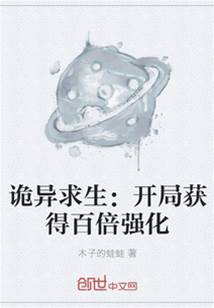
詭異求生:開局獲得百倍強化
【【起點國際·出海作品征文大賽】參賽作品】全世界人類降臨到詭異世界,每人一間小黑屋。白天,請你盡快去尋找物資和辟邪之物,夜晚,最好呆在小黑屋,外面處處都是詭異。夜晚,詭異來敲門,詭異規則將會把你籠罩。第一夜,全世界遭遇詭異規則:詭吹燈,蠟燭熄滅了就會死。蘇原覺醒百倍強化的天賦,強化后的蠟燭,來吹啊!屋里的詭異直接被嚇走了。夜晚的世界,到處都是寶箱,為什麼不去?怕死?不怕,百倍強化后,咱有一百條命!死一次算什麼?
149.8萬字8 13260 -
連載83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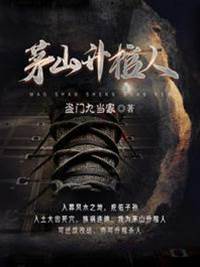
茅山升棺人
我從一出生,就被人暗中陷害,讓我母親提前分娩,更改了我的生辰八字,八字刑克父母命,父母在我出生的同一天,雙雙過世,但暗中之人還想要將我趕盡殺絕,無路可逃的我,最終成為一名茅山升棺人!升棺,乃為遷墳,人之死后,應葬于風水之地,庇佑子孫,但也有其先人葬于兇惡之地,給子孫后代帶來了無盡的災禍,從而有人升棺人這個職業。
153萬字8 952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