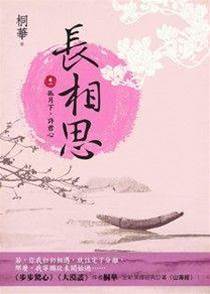《他定有過人之處》 第一百零七章
撲過來的剎那, 山宗的口都如同被重重撞了一下,沒握刀的那隻手上後頸,往下一直重重過背上, 了口氣“真沒事?”
神容抬起頭,臉輕過他的領“嗯。”
山宗此時纔看見臉上微微的紅,著他的前還在不住的起伏,手臂一收, 將往自己懷裡按了, 低頭埋在頸邊深深吸了口氣, 自己的膛裡纔算平靜下來。
遠仍有急促馬蹄聲在奔走, 胡十一在傳他的命令留活口, 似乎所有人都回來了。
山宗終於鬆開神容, 帶走去自己那匹馬下,抱著送上去, 翻而上,趕回馬車旁。
廝殺聲已經停歇,長孫家有不護衛都了傷,被東來帶著退去了道旁,此時一地首中站著的僅剩一群持刀的彪悍影。
山宗扯了下馬韁,手在神容臉側撥一下。
神容的臉頓時他膛,沒能多看,聽見他聲音在頭頂問“沒有活口?”
胡十一在前方大聲回答“沒有, 這群狗賊見苗頭不對就想跑, 跑不就自盡了。”山宗冷冷說“清理乾凈。”
又回到那座十裡亭前,神容才抬起頭往道上看了一眼, 那一群鐵騎長雖然是後來殺進來的,卻顯然是殺得最兇的, 駱沖此時還蹲在那兒往一個倒地的敵兵上刀,惡狠狠地呸了一聲,一旁的人在迅速清理。
扭過頭沒再看了。
“下來。”山宗手接住下馬,進了亭中。
神容被他按著坐下,平復了輕,又見他走去了亭外。
薄仲回來了,帶著兩三個同行的鐵騎長騎馬到了亭外,下來後快步走到他跟前,頭上滿是汗“頭兒,那群土匪不堪一擊,不過是尋常地流氓,已解決好了。”
Advertisement
“問出了什麼?”山宗問。
薄仲抹把額上的汗“他們是拿錢辦事,被指使了來擾咱們的,在這裡等了有一陣子了,今日等到就下了手。”
山宗頷首,一言不發地又回了亭。
神容看著他“既然是早就等著的,那就是準備好要引你走開,他們的目的是我。”
山宗沉著眼“沒錯。”
胡十一和其他鐵騎長也都過來了,老遠就聽見胡十一氣沖沖的聲音“頭兒,都是關外的兵,一定就是那孫子的人了!”
山宗冷笑“這還用說。”
不是他還能是誰,難怪幽州沒靜,他本沒盯著幽州。
“看來姓孫的是鐵了心了,就是搶也要把人給搶回去了。”駱沖在胡十一邊笑,順帶瞅一眼亭的神容。
神容蹙了蹙眉,去看山宗,他就站在前,馬靴挨著的擺,一不,如在沉思。
胡十一看那邊清理地差不多了,忍不住問“頭兒,咱這就上路?可要我先行回幽州帶人過來?”
山宗腳下了一步,轉說“不用,就這麼走,你們先去,我還有些事。”
胡十一抓抓下,瞄一眼亭子裡坐著的神容,明白了,朝旁招招手,所有人都退走了。
山宗回頭,手將神容拉起來“孫過折為人狡詐,應該會分出接應的人,你被盯上了,不能就這麼走。”
神容問“那你方纔還說要就這麼走?”
山宗笑一下“我是說我們,沒說你。”
神容盯著他的臉,眼神輕輕轉。
山宗在眼裡稍低頭,認真說“放心,有我在,誰也別想你。”
心頭頓時一麻“嗯,我記住了。”
……
隊伍繼續出發,往幽州方向前行。
路上隻他們這一行,馬蹄聲不疾不徐。
那輛馬車依然被好好護在隊中,卻不見長孫家那群護衛,前後左右隻是那十數人的鐵騎長隊伍,山宗打馬走在最前方。
Advertisement
胡十一瞄瞄那車,騎著馬靠近前方去,小聲問“頭兒,咱為何做這樣的安排,何不乾脆走快些,早日回到幽州不就安心了。”
山宗一手抓著韁繩,一手提著刀,目視前方“走那麼快做什麼,關外讓我不安心,我豈能讓他們安心。”
胡十一聽他這口氣就覺得不善,心想還是為了金,誰讓關外的敢他的人。
“聽著靜。”山宗忽然掃了眼左右。
胡十一回神,馬上就戒備起來。
四周安靜的出奇,冷不丁一聲尖嘯破風而來,一支飛箭在馬車上,一匹靠得最近的馬當即抬蹄,一聲長嘶。
山宗刀,朝出箭的方向疾馳而去。
胡十一跟其後,一群鐵騎長一瞬間都往那裡奔出。
馬車邊隻剩下了兩三人還圍守著,很快道旁就鉆出了人,朝他們沖了過來。
來的是十幾個人,皆如之前那群偽裝的敵兵一樣裝束,外罩黑皮甲,乍一看還以為是幽州軍,仔細看才會看出細微的差別。
唯有他們手裡的刀,因為用不慣中原兵,拿的還是寬口的彎刀。
守在馬車邊的兩三個鐵騎長刀抵擋了一番,作勢往山宗剛追去的方向退,似已顧不上馬車。
那十幾個手持彎刀的敵兵趁勢直沖向馬車。
當先一個跳上車,掀開車簾就想往裡去,卻忽然退出,大驚失地用契丹語向同伴們低喝――
裡麵沒人。
馬蹄陣陣,已自周圍奔來。
山宗帶著人疾馳而回,手裡的刀寒凜凜。
十幾人立即想撤,已來不及,刀還沒舉起來,左右殺至的人已直接襲向他們要害。
不過片刻,山宗收刀,策馬回視,十幾人已死的死,傷的傷。
胡十一揪住一個剛將刀架到脖子上的敵兵,一手著他,不讓他自盡,解了口氣般喊道“頭兒,這回總算抓到個活口了!”
Advertisement
山宗在馬上看了一眼“去審問清楚。”
胡十一二話不說拖著那敵兵去了遠。
山宗在馬上等著,一麵看了眼那輛華蓋豪奢的空馬車。
這是計劃好的,離開之前差點出事的地方時,他已經和神容分開,他去前方掃清餘敵,讓神容跟在他後麵不遠,隻走他清除過的路。
又過片刻,遠沒了聲響,胡十一理好回來了。
“頭兒,他們一共就混了這麼多人,這十幾個是等在這裡接應的,見前麵的沒得手就又下了一次手。”
山宗問“目的問出來了?”
胡十一氣道“沒!這人說就知道這些,咱幾人都下狠手也沒問出啥,可見是真話。他隻說是他們城主吩咐的,無論如何都要將人帶回去,帶活的!”
若非怕山宗不高興,胡十一都快要說是不是姓孫的真對金起心思了,還真就非要將弄到手了。
悄悄看一眼山宗,果然見他麵沉如水,眼底黑沉,他老老實實沒敢吱聲。
山宗扯一下馬韁,往前走“到檀州了,再往前去搜一遍,以防他們有應。”
胡十一趕上馬跟上。
眾人利落乾凈地理了四下,繼續前行。
駱沖在馬上跟龐錄笑著嘀咕“有意思,盧龍軍被帶回來了,姓孫的不報復咱們,倒隻顧著搶人了。”
不出十裡,荒道之上,遠塵煙拖拽而來,在沉涼薄的天裡看來不太分明。
龐錄騎著馬走在前麵,一看到就回頭示警“好像又是兵。”
駱沖當即就想拔刀。
山宗看了兩眼,說“那是檀州軍。”
檀州軍著灰甲,很容易辨別,一隊人約有四五十,看來是慣常巡視的隊伍,自遠而來,直沖著這裡方向。
山宗勒馬停下,看著領頭而來的人。
對方著泛藍胡,配寬刀,打馬而至,一雙細長的眼早就看著他,是周均本人。
Advertisement
“我的兵來報,這裡剛有手靜。”他一到麵前就道。
山宗嗯一聲“我們在你地界上了手,不過是關外兵馬,沒道理不手。”
周均上下看他兩眼,這次居然沒有找事,反而說了句“聽聞你去過長安了。”
“看來我被查的事已經誰都知道了。”山宗漫不經心地一笑。
周均眼睛在他後那群跟著的影上一一看過去,尤其在最眼的龐錄上停了停,又道“還能在我地界上和關外的手,看來你也沒什麼事,正好,送你一份大禮。”
山宗眼睛掃去,見他從後招了下手,兩個檀州兵下馬,將最後方馬背上的一個人拖下來。
那人雙手被綁著,被一路拽過來,一下撲跪在地上,麵容枯槁,發髻散,朝著他慌忙喊“山大郎君!山大郎君饒命!”
山宗打量他好幾眼,才認了出來“柳鶴通?”
“是是是,是我……”
山宗看一眼周均“你抓到的?”
周均口氣慣常是涼的“也不算,你們手的時候我率人趕過來,這個人在逃,正好撞上我人馬,晚一步,你們就到了,他還是逃不掉。他自稱是幽州大獄裡的犯人,自願回幽州大獄。”
柳鶴通立即道“是,我自願回幽州大獄!隻求山大郎君饒我一命!”
山宗大概有數了,搜這一遍居然搜出了他來,一偏頭,朝後方看一眼“十一。”
胡十一從馬上跳下來,幾步過來,拖了柳鶴通就回了隊伍。
柳鶴通嚇得直哆嗦,也不敢多言。
“帶回去細審。”山宗抓住韁繩一扯,又看一眼周均“大禮我收了,告辭。”
周均看他所行方向並不是往前直去幽州,卻仍在他檀州地界上,皺眉問“你還要去何?”
“去接我夫人。”山宗已徑自策馬遠去了。
一路順暢,再無危險。
山宗疾馳,一馬當先,直到約定好的地方,看到那座悉的道觀山門。
長孫家的護衛們似乎剛到,正在進出山門忙碌,觀前停著一輛普通馬車,隻兩馬拉就,毫不起眼。他一躍下馬,大步過去,左右頓時迴避。
馬車門簾垂著,安安穩穩。
山宗一直走到車旁,對著簾子看了好幾眼,心纔算徹底歸了位,出手,屈指在車上敲了兩下。
“誰?”裡麵神容警覺地問。
山宗不揚起角“我,找人。”
裡麵頓了一頓,神容聲音放平緩了“你找誰啊?”
山宗抱臂,盯著車簾,不急不緩地說“找一位金貴小祖宗。”
“是麼,哪家的小祖宗?”
沒有了迴音。
神容在車裡,手指正著袖間的那塊崇字白玉墜,忽然察覺外麵沒了聲音,還以為他走了,立即掀簾探出去。
人被一把接住了。
山宗的雙臂牢牢抓著抱住,臉近,蹭了下的鼻尖,角輕勾“我家的。”
神容怔了一下,搭著他的肩,慢慢牽起了。
他定有過人之
猜你喜歡
-
完結585 章

侯府真千金她重生了
重回十年前的江善(周溪亭),站在前往京城的船只上,目光冷淡而平靜。她是被人惡意調換的文陽侯府的真千金,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里的容妃娘娘是她姨母,溫潤如玉的二皇子表哥是太子之位的熱門人選,出生既頂端的她本該萬千寵愛、榮華富貴且波瀾不驚地過完一生。但十六年前的一場人為意外,打破了她既定的人生......等她得知身世,回到文陽侯府,取代她身份地位的江瓊,已經成為父母的掌心寶。前世她豬油蒙了心,一心爭奪那不屬于自己的東西,不論是父母的寵愛,還是江瓊身份高貴的未婚夫,這一世,她只想快快活活地活一...
107.9萬字8 330552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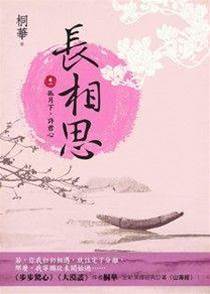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0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