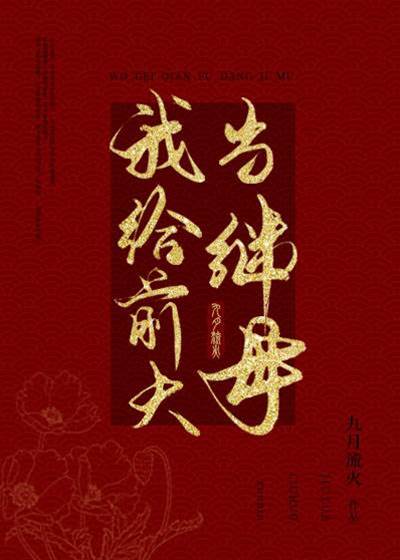《簪中錄》 第1章惡名昭彰(1)
暗夜中,忽然有暴雨傾瀉而下,遠遠近近的山巒峰林,長長短短的江河峽谷,全都在突然而至的暴雨中失去了廓,消漸為無形。
前方的路愈見模糊。長安城外沿著山道滿栽的丁香花,也被傾瀉的暴雨打得零落不堪,一團團錦繡般的花朵折損在急雨中,墮落污泥道,夜深無人見。
黃梓瑕在山道的暗夜中跋涉,握在手中的天青油紙傘在暴風驟雨中折了兩條傘骨,雨點過破損的傘面,直直砸在面頰上,冰冷如刀。
只抬眼看了一看,便毫不遲疑地將傘丟棄在路上,就這樣在暴雨中往前行走。雨點砸在上,格外沉冷,暗夜中天暗淡,只有偶爾雨點的微,映照出前面依稀的景,整個天地模糊一片。
山道拐彎,是一個小亭子。本朝設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是路人歇息。在這樣的暗夜風雨中,有三四個人正在亭中,或倚或坐,正在談天。長安城例行宵,每日早上五更三點才開城門,現在時辰尚早,想必是正在此等著城門開啟的人。
黃梓瑕踩著泥水過去。穿著一最普通的男式藍短衫,里面幾個人都轉過頭,見是個纖弱年模樣,其中一個老者便向招呼:“年人,你也是要趕早進城的?全都淋了,可憐見的,烤烤火吧。”
黃梓瑕看著他火下溫厚的笑容,拉的襟,謝了一聲坐到火邊,離他兩尺之遠,默默幫著加火添柴。
見只撥著火不說話,幾人也便回頭各自聊天,說到大江南北千奇百怪的事,眾人更是口沫橫飛,仿佛自己就在當場親眼目睹似的。
“說到這個奇事啊,最近京中那個奇案,你們可聽說過?”
Advertisement
“老丈說的可是被稱之為‘四方案’的那一個案子?”立即有人接口道,“三月之連死三個人,而且還是京城各自居住在城南、西、北三毫無瓜葛的人,又留下‘樂’、‘我’、‘凈’三個字,真是詭異莫測,恐怖異常啊!”
“是啊,現在看來,下一樁案定是要出在城東了,所以現在城東各坊人心惶惶,據說能走的人都已經走了,城東幾近十室九空。”
黃梓瑕一雙白凈的手握著柴枝,緩緩地剝著火苗,聽著輕微的“蓽撥”聲,面上平靜無波。
“如今天下不安,各州府都在,不止京城,最近蜀中也出了樁滅門案,不知大家可曾聽聞?”其中一個中年人,顯然是個游方的說書人,手里還習慣握著塊醒木,談興頗佳,“滅門案聽說得多了吧?可這樁案子,是蜀中使君黃敏家的滅門慘案!”
黃敏。
這個名字陡然耳,黃梓瑕一直沉靜撥火的手下意識地一,一點火星濺上的手背,突如其來的劇痛。
幸好眾人都在驚訝嘩然,本沒人注意,只借著這個由頭,大家七八舌在議論:“黃敏不就是當初在京中任刑部侍郎,幾年來破了好幾樁奇案,頗有聲的那位大人嗎?”
“這個我倒也有聽說!據說這倒也不全是黃敏一人之力,他有一兒一,兒子黃彥也就罷了,那個兒卻是稀世奇才,據說當年黃敏擔任刑部侍郎時,許多疑案就是替父親點破的,當時也不過十四五歲。當今皇上曾親口嘉許,說若是男子,定是宰執之才啊!”
“呵呵,宰執之才?”那說書人冷笑道,“各位可曾聽過傳聞,據說黃敏那個兒生下來就是滿室,看見的人都說是白虎星降世,要吃盡全家親人!如今果然一語讖,這黃家滅門案,就是黃家兒親手所為!”
Advertisement
黃梓瑕忘卻了手背上那一點劇痛,怔怔地看著面前跳的火。火舌吞吞吐吐,舐著黑暗,然而再暈紅的火,也無法掩蓋蒼白的面容。
周圍人面面相覷,而那位老者更是不敢置信:“你說,是黃家兒,滅了自家滿門?”
“正是!”
這一句斷喝,毫無猶疑,斬釘截鐵。
“簡直是荒謬,世上哪有兒行兇殺盡親人的事?”
“此事千真萬確,朝廷已經下了海捕文書,黃家如今潛逃離蜀,若被抓住了,就是千刀萬剮,死無葬之地!”
“若真如此,實在是滅絕人,天良喪盡!”
又是那個老者問:“如此世間慘劇,不知可有什麼緣由?”
“人家眼皮子淺,又為了什麼?當然是為了一個‘’字。”那說書人眉飛舞,又繪聲繪地講述道,“據說,自小許了夫家,但長大后卻另有心儀之人。所以就在祖母與叔父過來商議婚事時,在席間親手端上了一盞羊蹄羹。黃敏大人、黃夫人楊氏、公子黃彥、乃至的祖母和叔父全都中毒亡,唯有一人逃走,不知去向。衙門在的房中搜出了砒霜藥封,又查知數日前在藥店買了砒霜,白紙黑字記錄在檔。原來是心有所屬,父母卻迫嫁給別人,于是憤恨之下,毒殺了全家,并邀約郎共私奔!”
亭中眾人聽著這件人倫慘案,驚懼之下嘖嘖稱奇。又有人問:“這惡毒子,怎麼又逃掉了?”
“毒殺了父母家人,知事發,所以連夜約郎私奔。然而對方卻痛恨此等狼心狗肺的子,便將的信上呈府,帶人前往約會地點捉拿這惡毒人。結果不知怎麼被那惡察覺有異,竟逃走了!如今正被府下了海捕文書,所有州府城門口全了通緝告示,天網恢恢疏而不,我倒要看看這狠毒子什麼時候落網,那千刀萬剮之罪!”
Advertisement
說的人津津樂道,聽的人義憤填膺,一時間整個短亭居然有了一種同仇敵愾的氣氛。
黃梓瑕抱膝聽著,在眾人的唾罵聲中,忽然覺得困極累極。將自己的臉在雙膝上,雙眼茫然盯著那團暗淡跳的火,上的服半干半,在這樣的春夜,寒氣像無形的針一樣刺著,半醒半寐。
天尚早,城門未開,周圍人的話題又轉到最近京城的奇聞異事上。諸如如皇上又新建了一座離宮,趙太妃親自替三清殿制帷幔,還有京城多閨秀意嫁給夔王等等,不一而足。
“話說回來,這位夔王,近日是不是要回京了?”
“正是啊,皇上喜好游宴,新建離宮當然要熱鬧一番,而宮里的聚會,若是沒有夔王出席,又怎麼算得上聚會呢?”
“這位夔王真是皇室中第一出人,先皇也是對他寵有加,難怪岐樂郡主拼命要嫁給夔王,幾次三番用盡手段,為京城笑柄啊。”
“益王爺就留下這麼一個兒,估計要是泉下有知,肯定會被氣活吧……”
說到皇家之事,眾人自然都是一副津津樂道模樣,唯有黃梓瑕卻毫不關注,只閉目養神,側耳傾聽外面靜。
雨已經停了,在緩緩亮起的天中,有輕微的馬蹄聲約傳來,細若不聞。
黃梓瑕立即睜開了眼,拋下那幾個正在口沫橫飛的人,快步走出了短亭。
在熹微的晨中,旭日的芒正浮出天際。蜿蜒的山道上過來的是一隊次序井然的衛隊,明明他們上還帶著雨點,卻個個整肅警敏,一看便知訓練有素。
在隊伍的中間,是兩匹通無瑕的黑馬,拖著一輛馬車緩緩行來。馬車上繪著團龍與翔鸞,金漆雕飾,飾以硨磲和青甸子,兩只小小的金鈴正掛在車檐下,隨著馬車的走,輕輕搖晃,發出清空的聲音。
Advertisement
車馬越過亭子向前繼續前進。黃梓瑕遙遙跟著。在隊伍最后,有個和年紀差不多的士兵,在行進中心神不寧,向著左右掃視。等看到黃梓瑕在林后尾行,他才轉而向邊的人說:“魯大哥,不知道是不是昨晚吃壞肚子了,我……我要去方便一下。”
“你怎麼搞的,這就快進城了,你趕得上來嗎?”旁邊人低聲音,瞪了他一眼,“王爺下甚嚴,被發現了你知道是什麼后果!”
“是……放心吧,我馬上就追上來。”他捂著肚子,急匆匆地撥轉馬頭扎進了林中。
黃梓瑕撥開草,幾步奔到等他的士兵那里,對方已經匆忙地下了王府衛的制服,把頭盔摘下來給:“黃姑娘,你……會騎馬吧?”
黃梓瑕接過他的頭盔,低聲說:“張行英,你冒著這麼大的險幫我,我真是激不盡!”
“你這說是什麼話,當初若不是靠著你,我爹娘早就已經死了,這回我若不幫你,我爹娘都會打死我。”他豪爽地拍拍口,“何況今天不過是隨行進京,又不是什麼軍差,就算餡兒也沒事。上次劉五也是私下找人代差事,不過打幾十軍而已,你只要咬死說是我表妹……我表弟路過,見我拉肚子站不起來,就代我隨行應差就行,今天不過隨儀仗進城,沒什麼大事。”
黃梓瑕點點頭,迅速下外給他,然后套上他的服。雖然服大了一點,但材修長,也還看得過去。
匆匆與張行英道謝,黃梓瑕飛上馬,催促著沖出林。
猜你喜歡
-
完結284 章

末世歸來之全能醫後
驚爆!天下第一醜的國公府嫡女要嫁給天下第一美的殤親王啦,是人性的醜惡,還是世態的炎涼,箇中緣由,敬請期待水草新作《末世歸來之全能醫後》! 華墨兮身為國公府嫡女,卻被繼母和繼妹聯手害死,死後穿越到末世,殺伐十年,竟然再次重生回到死亡前夕! 麵容被毀,聲名被汙,且看精明善變又殺伐果斷的女主,如何利用異能和係統,複仇虐渣,征戰亂世,步步登頂! 【幻想版小劇場】 殤親王一邊咳血一邊說道:“這舞姬跳得不錯,就是有點胖了。” “你長得也不錯,就是要死了。” “冇事,誰還冇有個死的時候呢。” “也是,等你死了,我就把這舞姬燒給你,讓你看個夠。” 【真實版小劇場】 “你可知,知道太多的人,都容易死!”殤親王語氣冷漠的恐嚇道。 華墨兮卻是笑著回道:“美人刀下死,做鬼也風流啊。” “你找死!” “若是我死不成呢,你就娶我?” 【一句話簡介】 又冷又痞的女主從懦弱小可憐搖身一變成為末世迴歸大佬,與俊逸邪肆美強卻並不慘的男主攜手並進,打造頂級盛世!
49.9萬字8 16744 -
完結88 章

宮鬥不如養條狗
"狗皇帝"被"擋箭牌"寵妃收養,跟在寵妃身後經歷各種殘酷宮鬥並找到真愛的過程
26.9萬字8 9166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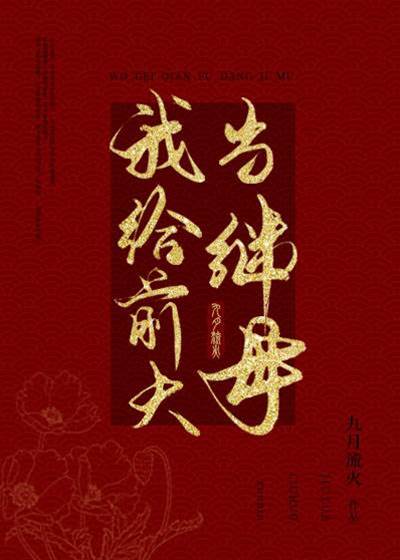
我給前夫當繼母
【微博:晉江九月流火】林未晞死了一次才知,自己只是一本庶女文中的女配,一個用來反襯女主如何溫柔體貼、如何會做妻子的炮灰原配。 男主是她的前夫,堂堂燕王世子,家世優越、光芒萬丈,而女主卻不是她。 女主是她的庶妹,那才是丈夫的白月光,硃砂痣,求不得。 直到林未晞死了,丈夫終於如願娶了庶妹。 她冷眼看著這兩人蜜裡調油,琴瑟和鳴,所有人都在用庶妹的成功來反襯她這個元妻的不妥當。 林未晞冷笑,好啊,既然你們的愛情感動天地,那我這個姐姐回來給你們做繼母吧! 於是,她負氣嫁給了前夫的父親,前世未曾謀面的公公——大齊的守護戰神,喪妻后一直沒有續娶,擁兵一方、威名赫赫的燕王。 後來,正值壯年、殺伐果決的燕王看著比自己小了一輪還多的嬌妻,頗為頭疼。 罷了,她還小,他得寵著她,縱著她,教著她。 #我給女主當婆婆##被三后我嫁給了前夫的父親#【已開啟晉江防盜,訂閱比例不足70%,最新章需要暫緩幾天,望諒解】*************************************************預收文:《難消帝王恩》虞清嘉穿書後,得知自己是女配文里的原女主。 呵呵……反正遲早都要死,不如活的舒心一點,虞清嘉徹底放飛自我,仗著自己是嫡女,玩了命刁難父親新領回的美艷小妾。 這個小妾也不是善茬,一來二去,兩人梁子越結越大。 後來她漸漸發現不對,她的死對頭為什麼是男人?他還是皇室通緝犯,廢太子的幼子,日後有名的暴君啊啊啊! ***本朝皇室有一樁不足為外人道的隱秘,比如皇室男子雖然個個貌美善戰,但是卻帶著不可違抗的嗜血偏執基因。 慕容珩少年時從雲端摔入塵埃,甚至不得不男扮女裝,在隨臣後院里躲避密探。 經逢大變,他體內的暴虐分子幾乎控制不住,直到他看到了一個女子。 這個女子每日過來挑釁他,刁難他,甚至還用可笑的伎倆陷害他。 慕容珩突然就找到了新的樂趣,可是總有一些討厭的,號稱「女配」 的蒼蠅來打擾他和嘉嘉獨處。 沒有人可以傷害你,也沒有人可以奪走你,你獨屬於我。 他的嘉嘉小姐。 註:男主偏執佔有慾強,祖傳神經病,女主虞美人假小妾真皇子與作死的嫡女,點擊作者專欄,在預收文一欄就可以找到哦,求你們提前包養我!
36.9萬字8.36 64041 -
完結109 章

懷嬌
被譽為世家望族之首的魏氏聲名顯赫,嫡長子魏玠品行高潔,超塵脫俗,是人稱白璧無瑕的謫仙,也是士族培養后輩時的楷模。直到來了一位旁支所出的表姑娘,生得一副禍水模樣,時常扭著曼妙腰肢從魏玠身前路過,秋水似的眸子頻頻落在他身上。這樣明晃晃的勾引,魏…
27.2萬字8 4658 -
完結730 章

萌妃天降:腹黑邪王惹不得
聽說,容王殿下點名要娶太傅府的那位花癡嫡女,全城百姓直言,這太驚悚了! 這幾個月前,容王殿下不是還揚言,要殺了這個花癡嗎? 太傅府,某花癡女看著滿滿一屋的聘禮,卻哭喪著臉,“來人啊,能不能給我退回去?” 京城貴女們紛紛爆起粗口,“求求你要點臉!”
131.4萬字8 7689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