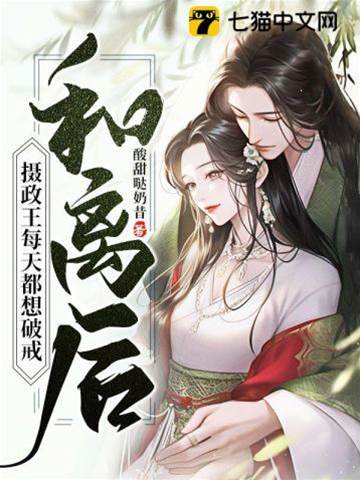《重生為后不賢》 第69章 前塵舊夢難續盡
魏太醫近日犯了難,都說天心難測,果然不假。
且不知道皇上又玩的什麼花樣,傳他來,說要做一些珍珠大小的藥丸。
說起制藥,魏太醫從來皆是自信,各宮各殿的主子們每月都有調理用藥,比如懿太后喝不慣湯藥,用的一直都是蜂裹藥丸,也并非難事。
但皇上的要求十分古怪,要用本是養氣的當歸、人參等藥材做出麝香的味道。
著手心里一顆烏溜溜的藥丸,魏太醫只好去花園和藥田里一面聞著一面尋。
明日就是期限,皇上限他今晚便要連夜趕制,出宮自然是不可能了。
及至夜,魏太醫這才從花園里摘了幾種花蕊心和藥,打算回去研制。
豈料才出了花園,卻遇見了溫淑妃。
他躬見了禮,便側過子垂首立在道旁,可良久,溫淑妃也并未走過去,再抬頭就見微微笑著過來,“久聞魏太醫醫冠絕太醫院,本宮正好有些事要向你討教一二。”
魏太醫連忙搖頭,“娘娘謬贊,微臣愧不敢當,只是聽聞您的脈是給孫太醫診理,有什麼話孫太醫自然會言無不盡的。”
溫淑妃立在前面,擋住了路,夜風徐徐吹在嫵的臉容上,“這世上可有什麼藥,服食下去可以狀似懷娠,延遲月事麼?”
魏太醫大驚,登時便聯想到婉貴妃小產之事…他并非沒懷疑過,但后來胎落本無從查證,更何況看皇上的意思,定然是在意婉貴妃的。
此事越想越是心驚,乃為他的一塊心病,若當真其中有所古怪的話,自己便是欺君的大罪。
所以后來每每去毓秀宮,總是提著心兒,生怕婉貴妃再想出什麼法子來,好在后面平平靜靜,小產一事無人再提。
Advertisement
可原本以為已經翻過去的舊賬,忽然間被溫淑妃提起。
“淑妃娘娘玩笑了,十月懷胎,一朝分娩,懷娠豈可做的了假。”魏太醫保持著穩定的神,科打諢帶過去。
溫淑妃卻冷冷一笑,進一步往前,“可若半路小產了,那豈不就可以以假真,天無了?”
魏太醫心中發虛,越聽越是心驚,便連忙告辭道,“微臣還有事務在,這廂告退。”
然而魏太醫沒走出幾步,后傳來的一句話,便教他再移不開一步。
“小產當日,有人親耳聽到魏太醫你說脈象不對,為何沒有雜沖脈緩之兆是也不是?”
那是當日急之下口而出,卻不想竟然會落人口實。
魏太醫收回步子,不言語。
溫淑妃咄咄人,“婉貴妃從來都沒有懷孕,那一胎是假的,而魏太醫你便是幫兇!”
話音剛落,但見后小徑上沙沙作響,兩人俱都回頭,不知何時,已有一條修長的人影立在不遠。
那人從樹影里緩緩而出,清俊的面容現了出來。
魏太醫和溫淑妃皆是大驚失,連忙行禮,“參見陛下!”
溫淑妃心驚之下忽而生出幾許旁思。
方才的話,皇上定然是聽見了。
既然無心柳,已然假借魏太醫的口說出,被皇上撞見了,也許事便更好辦些。
如此,便免去自己刻意為之的嫌疑。
當真是如有神助,天無。
溫淑妃悄悄了一眼皇上,清俊的臉容越發清冷如霜,在夏夜里亦散發著重重寒意。
“溫淑妃這些話是從哪里聽來的?”
一笑,帶著為難的神,溫淑妃開口,“陛下恕臣妾多言,只是偶然聽到了流言,心下始終疑。”
Advertisement
見皇上不語,便更壯了膽子道,“那周才人固然有罪,但當初已然是皇貴妃的高位,又得太后娘娘支持,沒有理由去害婉貴妃的孩子…”
說的言辭懇切,以為皇上定然會聽進去,從而徹查此事。
卻不知,此刻封禛心下翻江倒海,如臨深淵。
回想當初,陳婠先是一心想要避過宮,滄州相見時,自己并未像份,就連陳棠都不知道,可現下想來的舉似乎都在暗示著想要避開自己的強烈意愿。
后來宮,從來都不爭不問,仿佛在極力撇清和后宮的干系。
昨日發現避子藥丸時,他震驚之余,仍是有些愧疚的,以為陳婠是因為小產之事害怕懷胎,多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可今夜這周驟然揭開偽裝之下的掩蓋,真相卻是如此令他難堪。
獨寵的妃子,竟然從來都不想為自己生孩子。
如此的目的,絕不會是為了爭寵。
那些寵,本就不在乎,若會去爭,自己心里也能好過半分。
腦海里縷縷,在想到那三株石竹花時,腦中仿佛被狠狠一刺。
怎麼會將這樣重要的事都忘記了?
陳婠從前并不認識石竹花,當時太子種花時,隨口問了自己一句那是什麼花這樣好看,從前沒有見過的…所有的一切都找到了突破口!
一定是和自己一樣,有了前世的記憶,而且要比自己還要早!只怕從相遇的第一日起,陳婠就已經將他拒之千里之外了。
和從前爭寵奪位的心截然不同,可以說如今做的每一件事,皆是相反。
在冷宮的十年,永遠是他們之間無可挽回的錯過。
“陛下?您若不相信,可以去見一見周才人。”溫淑妃見他神思游離,便一口將責任推到周才人上,來一個一石二鳥之計。
Advertisement
就在得意之時,皇上冷寂的目掃過來,“朕信得過魏太醫,你先下去吧。”
魏太醫一冷汗,就在以為會有滅頂之禍時,突然峰回路轉,柳暗花明,自然是連忙謝恩離開。
時下花樹寂靜,封禛緩步靠近,正停在溫淑妃的前,因為量相差許多,那種無形的迫便愈發明顯。
溫淑妃并不蠢鈍,皇上的反應顯然和預料中的不同。
“后宮風言風語,朕從來皆是當做耳旁風不做理會。但關于此事,到此為止,溫淑妃替朕著想的心意雖好,但若是日后再聽到任何誹謗議論之詞,朕便不會如此輕饒了。”
這分明是告誡之意。
溫淑妃不明白,皇上在聽到婉貴妃假孕的消息時,不應該雷霆震怒麼?
怎會是這樣的結果…
忍著不甘,恭順地應下。
封禛手將下輕輕抬起,視著的眸,“可是記得清明?”
溫淑妃低眉順眼,被他強勢的態度所攝住,皇上在面前,還從未有過如此狠厲的模樣。
“臣妾謹記,不敢有違圣訓。”
封禛這才松了手,“如此便好,回宮去吧。”
--
自從婉貴妃回了陳府,本就不大的庭院登時熱鬧起來,闔家上下一團喜氣。
說起來,如今大小姐是天子邊地位最高的寵妃,階上即便是陳老爺見了,也要叩拜行禮的。
但陳婠不喜歡鋪排場面兒,將皇上賜的件分發下去,便與家人在一室,毫無貴妃的架子。
住了幾日,府中仆從倒是覺得好似大小姐仍在家中一般。
母親的病發的極,各人質不盡相同,盡管太醫院派了孫太醫來,但起效甚微。
陳婠歸寧當日,母親仍是起不來床。
Advertisement
父親奔波于朝堂之上,亦是鞠躬盡瘁效命天子。
陳婠這一住下,便日日陪在母親病榻前,時而說會話兒,時而給母親讀寫話本聽,過得格外安寧,一時不思歸。
皇上來書詢問,便以母親病為由一拖再拖,如此就拖延了十日之久。
說來也巧,就在第七日,大哥從邊關寄來的包裹送到家中,除了一封簡明扼要的書信之外,余下的是一大包外敷用的藥草。
信上過短短幾行字,陳婠便能悟到大哥如今海闊天空的壯志豪,如此看來,他對溫的執念,終究是放下了。
草藥是從西域烏蒙得來的偏方,烏蒙國素以岐黃之文明四海,出了不名醫圣手,但烏蒙國的醫很晦,大不相同于中原。
但見母親難過的,陳婠便依著方子上的用法替母親煎藥熱敷。
大哥的藥,果然有奇效,當晚頭風發熱的癥狀便緩解了一二。
但聽大哥信中的意思,那位岐黃圣手在邊關,若是能接母親過去醫治,也許能一舉除。
但路途迢迢,一時半刻是行不通的。
這已經是用藥的第三日,母親安穩睡下,陳婠這才回到自己的閨房歇息。
沈青桑說宮里晌午又來了信,說明日就接娘娘回宮,一再拖延的選秀將要舉行。
陳婠為貴妃,自然是避過不的。
正說著話,突然見家匆忙跑進了小院兒,隔著門道,“貴妃娘娘,陛下、陛下來了。”
陳婠與沈青桑先是對視一眼,愣了愣,旋即才明白過來。
“陛下怎會來陳府…”沈青桑在宮中這麼多年,從沒見過如此行事的。
總歸是逃不過的,陳婠便過前院去接駕。
封禛連夜從皇宮出來,為了掩人耳目,并未用六馬輅車,而是轉乘了大臣規格的兩馬驅車而來。
陳府小巷幽深,夜深人靜。
這是他第二次來到陳家,起初迎門的管家并不認得皇上,寧春淡淡地出示了玉佩,這才驚全府,陳老爺被弄得措手不及,連忙教下人去將睡下的陳夫人也喚起來迎駕。
卻被皇上制止,說是此次微服出宮,不想大干戈,正好順路來探一探婉貴妃。
陳老爺如何機敏,當即就知道了皇上是沖著兒來的。
而眾目睽睽之下,陳婠前來迎駕時,只是穿著件藕荷的家常衫,發髻微微攏起,看上去十分隨淡然。
人前不得一番君臣寒暄,做做樣子。
而后皇上陪著陳婠回閨房安置,陳府下人卻都聚在后院柴房,心激地品頭論足一番,原以為自家大公子已是人中龍,今日一見天子真,登時驚為天人。
此卻不提。
陳婠的閨房不大卻十分溫馨,布置地雅致秀凈,“陛下怎地親自來了,家中不比宮中,恐怠慢了。”
一面兒整理著床鋪,秀雅纖細的段在眼前晃來晃去。
背過去,陳婠敏銳地覺出今晚皇上的表和從前有些不太一樣,同樣是喚婠婠,卻顯得別有意味。
千種滋味,萬種思量,皆是化作脈脈無語。
封禛始終凝著一舉一,陳婠被他目弄得十分不自在,便道,“夜深了,陛下在臣妾床上歇著,臣妾去陪母親同睡,明兒一早,再啟程回宮。”
豈料封禛將攔腰一橫,旋兒就抱在懷里,黑眸深深,像是要將人吸進去一般。
“陳夫人病未愈,婠婠陪朕一起,不許走。”
陳婠心頭一驚,歸家匆忙,也不曾料到皇上會過來,就沒帶麝香白鷺丸…
而后壯的軀已經覆蓋上來,不給毫退路。
封禛邊揚起一抹弧度,他覺到了懷中人兒的抗拒,正印證了自己的猜測。
只不過,他如今要用行來力行,那些個虛言妄語,只怕是難以降服倔強的陳婠。
“婠婠若是喜歡,明日朕正巧休朝,可以再陪你住上一日。”繾綣的纏綿繞了上來,令沒有任何退路。
便在這略顯窄小的床榻上,一室春溫濃。
而從來逆來順的陳婠,今夜格外的不配合,像只張牙舞爪的貓兒。
但封禛是鐵了心要達所愿,自然不會放過。
燭火熄滅時,已然是子夜。
春汗,終于一解連日思。
只不過陳婠一心擔心孕,而不知后男人的大網才剛剛撒下。
猜你喜歡
-
完結56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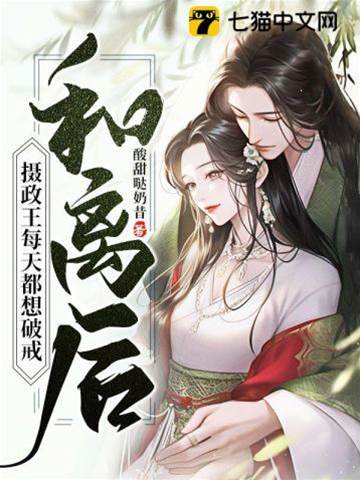
和離後攝政王每天都想破戒
葉芳一朝穿越,竟然穿成了一個醜得不能再醜的小可憐?無才,無貌,無權,無勢。新婚之夜,更是被夫君聯合郡主逼著喝下絕子藥,自降為妾?笑話,她葉芳菲是什麼都沒有,可是偏偏有錢,你能奈我如何?渣男貪圖她嫁妝,不肯和離,那她不介意讓渣男身敗名裂!郡主仗著身份欺辱她,高高在上,那她就把她拉下神壇!眾人恥笑她麵容醜陋,然而等她再次露麵的時候,眾人皆驚!開醫館,揚美名,葉芳菲活的風生水起,隻是再回頭的時候,身邊竟然不知道何時多了一個拉著她手非要娶她的攝政王。
99.6萬字8 9218 -
完結665 章

首輔大人的寵妾
顧府奴婢四月生得烏發雪膚,動人好似蓮中仙,唯一心愿就是攢夠銀子出府卻不知早被覬覦良久的顧府長子顧容珩視為囊中之物。當朝首輔顧容珩一步步設下陷阱,不給她任何逃跑的機會。低微的丫頭從來逃不過貴人的手心,在顧恒訂親之際,她被迫成為了他的妾室。人人都道四月走了運,等孩子生下來就能母憑子貴,升為貴妾了。四月卻在背后偷偷紅了眼睛。再后來,那位倨傲提醒她不要妄想太多的年輕權臣,竟紅著眼求她:做我的妻
122.4萬字8.18 233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