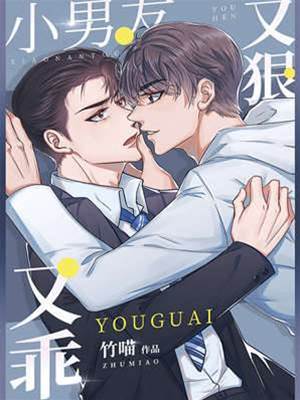《宰相男妻》 38庶四爺要納妾
誰都知道王家不會善罷甘休,可就在大老爺等王家後繼作時,縣丞也就是王家婿以讓人措手不及的速度轉調外縣,新縣丞不過三天就上了任,爾後王家速度與新縣丞家敲定了親事。
這一變故讓人看的是眼花繚,無比錯鄂。
這事後難堪的就數庶三房。
事落幕,老太爺在易雲松一次說知曉了事真相,當下氣的青筋直暴,喊來庶三爺當著大老爺跟庶四爺的面狠狠的給其吃了頓家法!並且勒令這三代之不得再與家結親。
庶三爺被這晴天霹靂給直接霹懵了。他廢盡心思跟王家結親,甚至還想說和王家小姐的婚事為的是什麼?不就是想讓自己的兒子娶家小姐嗎?可老太爺這一說話他的心思不是全白廢了還平白得罪狠了大房。
不說老太爺如何著庶三房不許再與家結親,這廂冬在聽說王家小姐已經結親的消息,一直懸著的心總算悄悄放下,安安心心過自己的日子。
一場桃花風波就這麼看似平靜的落了幕,轉眼又過半月,時節到了整年最炎熱的時候。
“冬,後屋井裡冰了西瓜,你去撈個上來切了吃。”餘氏倒好納涼喝的茶轉頭對冬道。時節實在是太熱,一般莊稼百姓家裡都會在吃罷晚飯後便在屋前搬些躺椅納涼,等夜半的涼風吹開屋子裡的悶這才回屋睡覺。
冬正待應聲,易雲卿走了來:“娘,我去。”
不過從井裡撈個西瓜切了也不是多大點事,餘氏擺擺手讓他去,這邊與冬一起把涼椅搬到屋前,擺上涼茶點上被祛蚊的香。大老爺從書房捧了兩本書來,打算就著夜教易謙解書。易謙手上拿著各自納涼的草扇,待到大人們坐定一人手上發一把。
Advertisement
易雲卿切了冰好的西瓜端了來,另一手還提了剛從深井裡打上來的泉水。
餘氏瞧了:“這泉水太涼,可別喝多了。特別是你,”視線轉向易謙:“這泉水最多就喝兩杯,不然不給西瓜你吃。”
易謙聞言,苦著臉撒:“~~~”
餘氏拿手他額頭:“你可別以為跟你說著玩。”
“可爹爹跟小爹爹都可以喝很多……”易謙委屈的癟著。家裡有兩口井,一口是家用的淺水井,一口就是專用來喝的深水井。深水井裡的泉水是地地道道的山泉,喝著冰冰的最是解熱而且還有子泉水的清甜。
“你還小脾胃弱,可比不得你爹爹小爹爹,他們正當年壯得住這點冷熱。”
大老爺半笑道:“好了好了,你呀真是越來越羅嗦連孩子喝點水都要管。”
餘氏嗔他一眼:“我是為謙兒好,這時候羅嗦些總比貪吃多了涼的最後鬧肚子得好。”
“謙兒都五歲了,哪有你說的那麼弱?”
“五歲了那也是小孩子。我正想說呢,老爺。你別每天追著謙兒學這學那的,總要給孩子點玩鬧時間。”
大老爺被頂撞的瞪眼:“婦人之見!孩子就是因為小才讓他多學些定定子,玩鬧的多了野了心,以後學什麼都學不上了!再說,我給謙兒的課業一點都不重,想當初,卿兒的課業是謙兒現在課業的五倍。”
易雲卿瞧著這邊,把躺椅搬遠些,搖著折扇給冬納涼順帶說些悄悄話。至於那爭論的兩老嘛,嗯,好不易有個共同的語言讓他們‘說’的起勁,他就不打擾了。
易謙則乖乖坐在旁邊啃著自己的西瓜,啃的歡快了還微微瞇著眼,晃著懸在椅子上的小短,瞧那一個遐意。
Advertisement
只有冬有點擔心,聽兩老的語氣生恐他們吵起來。
明月當空掛,被皎白月照亮的天邊掛著幾顆稀疏的星星,田野邊飛著亮閃閃的瑩火蟲,耳邊聽著蟲蛙聲,吹著越見涼爽的清風,易雲卿心境奇好,張口便是兩首述說眼下境的詩詞。
大老爺掌輕歎:“妙!”
餘氏含慎似怒的瞪兩父子一眼:“我可告訴你們,別拿這酸的掉牙的什麼詩呀什麼詞的來鬧心人!要作詩要作詞,可以!回書房去,隨你們父子作個千來百首的沒人說你們一句!”
“庸俗!”大老爺惱餘氏不解風。
易雲卿尷尬咳聲。
冬抬眼瞧他,以眼神詢問是不是不舒服,眼沒有他附庸風雅的鄙視,而是一片崇敬跟點點傾慕。
心一,易雲卿牽了冬手,起去給易謙抓瑩火蟲。雖然月皎白目一片清晰,可仍怕草叢中有毒蛇,好在這季節瑩火蟲這是多的,兩人在屋前院子就抓了不,拿明細紗制的口袋裝了再用繩子一紮,繩子上頭綁上子,最神奇的自然燈籠就了。
收到自己意外的禮,易謙把開心的笑聲洋溢到整個屋子都聽得到。
氣溫隨著夜深而逐漸涼爽,大老爺跟餘氏回房休息,囑咐三人不要貪涼到大晚。
仍舊是明月高掛,竹床上易謙已經攤開睡著,冬躺在旁邊半睡不睡,易雲卿半躺半臥在那裡給這一大一小搖扇子。下半夜,抱起易謙送回房,自己則拿了條薄毯回來給冬蓋了肚子,順勢也躺到旁邊。
炎熱的夏季過,很快便是莊稼人期待的收獲季節。秋。
大房的田地不多,易雲卿請了短工不過三天就弄完了。閑著無事,兩人找易雲春和記上山打獵。不想,獵是打得多可麻煩也隨之而來,並且是誰都沒料想過的麻煩。在這個麻煩發之前,易雲卿毫不知,而且四房也發了一件糟心事。
Advertisement
庶四娘連夜帶著雲松哭到老宅,跪到老太爺老夫人面前哭哭啼啼請他們作主。老太爺被庶四娘那幅天塌下來的模樣給嚇了一跳,心中一慌還以為庶四爺發生了什麼,一問才知既然是那麼一件糟心事。
庶四爺要納妾。
納妾在這重男輕的世道並不意外,三妻四妾的男人多的是而且被普遍認為是天經地義,按說庶四爺要納妾庶四娘這妻子為了自己的名聲不即不能阻止還要自主為庶四爺張羅,不然就會被說善妒。七出之條中,善妒一條可是赫然在列。
要說庶四娘的為人事,也該知道這事就算求到老太爺面前也可能於事無補,可還是求了,而且這求的理由嘛,還真不好說。
庶四爺要納的妾不是什麼良家清白子,而是本地富戶守寡的兒。雖然本朝沒有勒令寡婦不能再嫁,可說出去畢竟不好聽,庶四娘就是抓住這一點,哭著信誓旦旦說庶四爺要想納妾一定自主給其張羅挑選家清白的子,可寡婦!那是要毀易家名聲的呀!說著拉易雲松跪下,哭著說不要讓雲松出門被人指指點點論事非,說他家有個寡婦姨娘!
老太爺不知是該氣還是該怒,這氣這怒又該向誰發!納妾是小事,畢竟四房現在還只有雲松一個兒子,如果這庶四娘再不能生養或許老太爺都會約提一句子嗣,可這納寡婦?老太爺閉著眼睛覺著腦袋一片麻。如果他們還自持世家出,那這納寡婦就絕計不可能,可他們現在不是曾經的平赫然世家,而是待罪流放之,這納寡婦一事就…老太爺覺著他的頭有點疼。
老夫人不是庶四爺親母,也不想擺嫡母的款,只在旁輕語安庶四娘,對這一事的決卻是決口不提。
Advertisement
大老爺與作氏聽聞庶四娘哭著上門也是驚了一跳,趕忙過了來,一聽是這糟心事兩人恨不得當個明人。
老太爺不好自作決定,只讓老夫人好生勸了,老夫人則讓餘氏這嫂子陪著一起勸。當晚餘氏便一起睡在老宅,大老爺安排好雲松的住,回來時說了庶四房發生的事。末了對易雲卿一句歎:“你三叔跟你四叔真是……”不好用詞便一再搖頭:“放著好好的日子不過偏要生些事端,家宅不寧,他們就能舒坦?”
晚間躺在床上,冬歎氣,老久都睡不著。
易雲卿拍了拍他:“還在想四叔的事?”
“老太爺會同意讓四老爺納這房妾麼?”
笑下:“問題不是在於爺爺。你忘了?易家現在已經分家了,分出去的四叔完全可以自主納妾。”
“可四老爺納的是……”
“這件事你不需想太多。四叔會說服爺爺,四嬸也不是真心想阻止四爺納這房妾,今天這糟呀,可以說全然是場戲。”
“……?”冬眨眼,明明聽的清他說的話,可為什麼愣是聽不懂?
猜你喜歡
-
連載9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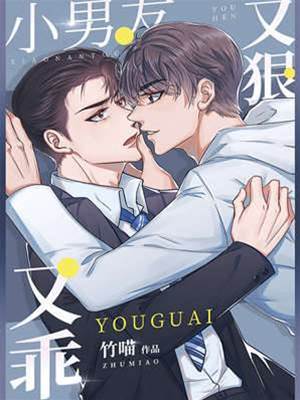
小男友又狠又乖
江別故第一次見到容錯,他坐在車裡,容錯在車外的垃圾桶旁邊翻找,十一月的天氣,那孩子腳上還是一雙破舊的涼鞋,單衣單褲,讓人看著心疼。 江別故給了他幾張紙幣,告訴他要好好上學,容錯似乎說了什麼,江別故沒有聽到,他是個聾子,心情不佳也懶得去看脣語。 第二次見到容錯是在流浪動物救助站,江別故本來想去領養一隻狗,卻看到了正在喂養流浪狗的容錯。 他看著自己,眼睛亮亮的,比那些等待被領養的流浪狗的眼神還要有所期待。 江別故問他:“這麼看著我,是想跟我走嗎?” “可以嗎?”容錯問的小心翼翼。 江別故這次看清了他的話,笑了下,覺得養個小孩兒可能要比養條狗更能排解寂寞,於是當真將他領了回去。 * 後來,人人都知道江別故的身邊有了個狼崽子,誰的話都不聽,什麼人也不認,眼裡心裡都只有一個江別故。 欺負他或許沒事兒,但誰要是說江別故一句不好,狼崽子都是會衝上去咬人的。 再後來,狼崽子有了心事,仗著江別故聽不到,在他看不見的地方悄悄說了很多心裡話,左右不過一句‘我喜歡你’。 後來的後來,在容錯又一次說出這句話的時候,江別故終於沒忍住嘆出一口氣: “我聽到了。” 聽力障礙但卻很有錢的溫文爾
56.5萬字8 6649 -
完結388 章
穿成男頻文裡的惡霸炮灰
《帝業》一書中,男主霍延出身將門,因朝廷腐敗,家破人亡,入慶王府為奴。 慶王世子心狠跋扈,霍延遭受欺辱虐待數年,幾次差點傷重而亡。 直到亂世來臨,他逃出王府,一步一步執掌兵權,霸圖天下。 登基後,將慶王世子五馬分屍。 樓喻好死不死,穿成下場淒慘的慶王世子。 為保小命,他決定—— 廣積糧,高築牆,緩稱王。 種糧食,搞建設,拓商路,興兵甲,在亂世中開闢一條生路。 漸漸地,他發現男主的眼神越來越不對勁。 某一天敵軍來犯,男主身披鎧甲,手執利刃,眉目英俊宛若戰神降臨。 擊退敵軍後,他來討要獎勵—— 浮世萬千,惟願與君朝朝暮暮。
81.3萬字8 10097 -
完結253 章

助理建築師
建築系畢業生張思毅回國求職期間,在咖啡館與前女友發生了爭執, 前女友憤怒之下將一杯咖啡潑向他,他敏捷躲閃避過,卻讓恰巧起身離席的隔壁桌帥哥遭了秧。 隔日,張思毅前往一家公司面試,竟然發現面試自己的人正是替自己挨了那杯咖啡的帥哥! 心如死灰的張思毅本以為這工作鐵定沒戲,不料那帥哥「不計前嫌」地錄用了他,還成了他的直屬上司。 當張思毅對帥哥的善良大度感激涕零之時,他還不知道,自己「悲慘」的命運這才剛剛開始…… 張思毅:「次奧,老子就害你被潑了一杯咖啡,你特麼至於嘛!TAT」
65.8萬字8 2981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