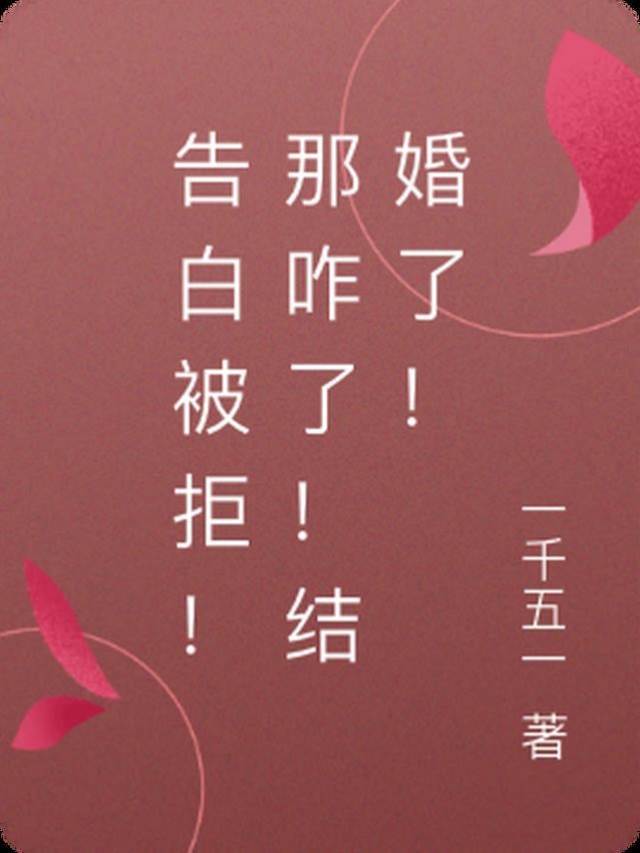《終身妥協》 第7章 晉江獨家首發
夜彌漫,濃墨灑滿蒼穹。
窗外是五十的霓虹燈,車子疾馳駛過江大橋,明明滅滅的線切割在里面,為車平添危險的氣息。
安棠被迫仰起頭,出修長的天鵝頸,的眼神落到賀言郁臉上,那張臉真的使無法生氣。
“你弄疼我了。”說。
“疼才知道長記。”
賀言郁松開那縷纏在手指上的發,五指埋安棠的發間,以絕對的掌控扣著的后腦勺,“說你喜歡我。”
像這種話,賀言郁最喜歡聽了,尤其是這半年多以來,無論是跟行魚水之歡,亦或者干其他事,他想起便會說。
嗎?還是沒有安全?安棠覺得都不是,他只是想表達自己的占有而已。
安棠像例行公事般,“我喜歡你。”
“真乖。”賀言郁扣著的后腦勺,垂在側的右手抓住安棠的,用極致的合與十指扣。
他俯親吻安棠的眉眼,作溫而有耐心,“以后別再說話,你知道的我不喜歡。”
安棠沒有應他。
賀言郁卻有些不滿,惡狠狠的咬了下安棠的,的而有彈,被他這樣碾磨后直接破皮,甚至有溢出來。
淡淡的腥氣彌漫開,安棠手想推開他,卻被賀言郁攬在懷里。
“又不聽我的話了,看來,蔣青黎在你心中的分量不輕。”賀言郁惻惻的笑,“我養的東西,他也敢染指,看來是活膩了。”
好歹也是幫過忙的人,安棠不能害他被連累,聞言,微攏眉頭問:“你又想干什麼?”
“這就急了?”
“我沒有,只是我兩的事,不想牽連無辜而已。”
安棠表認真,態度也堅決,似乎只要賀言郁敢來,這事就不能輕易揭篇。
Advertisement
賀言郁輕輕笑出聲,指尖點了點安棠的心口,“我可不覺得牽連無辜,他可是把你的心都給勾走了。”
“你簡直是無理取鬧。”安棠撇開眼,不去看他那張臉,否則怕自己連強的話都說不出來。
“我跟蔣青黎頂多算劇組里的同事關系,他今天見我一個人走紅毯,邊沒有男伴,所以出于好心替我解圍。”
“至于采訪我時問的問題,我只是針對我寫書的習慣說的。”
這話說得真真假假,究竟為何只有安棠自己心里清楚,盯著窗外一閃而過的夜,反將一軍道:“這些天你干的那些事,我都沒審問你,你倒反過來追問我,甚至還懷疑我。”
“你覺得這公平嗎?”
車氣氛瞬間凝滯,開車的司機背脊冷汗淋漓。
賀言郁盯著,安棠側背對著,只留給他朦朧恬靜的側臉。
半晌,車里響起淺淺的、愉悅的悶笑,賀言郁手,從背后環抱著安棠。
他的臉埋在安棠的脖頸,手臂收,懶懶散散的說:“我很樂意接棠棠的審問。”
輕輕的又帶著點散漫調侃的語調,就像人的蠱,勾起人心底深的,溫熱的呼吸噴灑在脖頸間,弄得安棠有些發,了,被賀言郁抱得更了。
賀言郁這個人,安棠有時候也捉不,就像他現在,前一秒明明還在發瘋,下一秒就有心思跟開玩笑。
不知道是不是他現在心很好,聽了安棠剛剛的話,難得跟解釋:“我跟楊佳蕓沒有任何關系,你別胡思想。”
都說男人的話信不得,安棠也不信他的花言巧語,被賀言郁磨夠了,也想翻一次,更何況泥人還有三分脾氣。
Advertisement
“你兩的緋聞鬧得滿天飛,這沒有關系?”
“把我的獎項改的,這也沒有關系?”
賀言郁也不惱,反而還敢笑出聲,他輕輕啄了啄安棠的耳垂,啞著嗓音說:“子虛烏有的緋聞算得了什麼?又不是真的,等哪天你親眼看到我包養其他人,那才是真的。”
“……”
“至于本該屬于你的獎項。”賀言郁低頭啃咬的肩頸,“那本來是我想送給你的生日禮,可惜了,誰你和蔣青黎走得太近,然后被我撞見。”
“我不高興,你自然也別好過。”
“……”
這些話旁人聽了,估計拳頭都要,安棠不在乎,自然也不會放在心上。
賀言郁抱著,見不說話,“行了,一個獎項而已,丟了就丟了,今天是你生日,想要什麼?”
他執起安棠的右手,親了親的手背,視線瞥見手腕上戴著一老舊的紅繩,賀言郁突然想起,今晚出席IP作者大會,渾上下竟沒有一件珠寶首飾。
家里堆了很多,從不佩戴,安棠不說,也不索取,賀言郁自然不知道喜歡什麼。
賀言郁有些嫌棄那紅繩,“這麼老舊的東西還戴在上,看著沒什麼用,丟了吧。”
見賀言郁在撥弄自己的紅繩,安棠的反應很大,甚至想也沒想拍開他的手。
“啪——”
使的手勁很大,竟讓賀言郁的手背開始泛紅。
“別它!”
安棠立馬坐得遠遠的,蹙著眉警惕的看著賀言郁,仿佛他是要搶紅繩的小。
賀言郁原本剛有的好興致又沒了,他惻惻的盯著安棠,視線落到手腕上的紅繩。
他的腦海里又想起幾天前回到家,看到的那幅畫面。
Advertisement
安棠把紅繩重新戴在右手上,走到臺,抬手對著明的線,下紅繩有,面帶微笑,闔眼真摯而虔誠的吻了吻。
那孩般滿足的赤忱笑容,讓似乎沉浸在旁人不知道的喜悅里。
很喜歡那紅繩。
賀言郁又想起,從初遇安棠起,的手上就有這麼一紅繩。
“這麼寶貝?連我都不得?”賀言郁冷笑。
安棠不言。
兩人有時候都是倔子,誰也不肯服,安棠這副模樣,倒是讓賀言郁越發想要折斷的傲骨和翅膀。
他把人扯過來錮在懷里,直接手去的紅繩。
安棠像是被了逆鱗,拼命掙扎著,最后竟然抓著他結實修韌的小臂死死咬下去。
賀言郁悶哼著,眼神更冷了。
安棠跟了他兩年半,前兩年對他死纏爛打,他得死去活來,雖然這半年對他的漸漸淡下去,但每次看到他,眼里還是有熾熱的意。
他,勝過自己的命,可如今為了一破舊的紅繩,竟然敢不要命的咬他。
賀言郁的眼神帶著戾氣,他甚至會惡劣的揣測,這紅繩于安棠而言,怕是哪個讓不能忘懷的男人送的。
想到這,他心里更是堆積著郁氣,狠心下紅繩丟出窗外。
安棠氣得頭暈眼花,里滿是腥味,甚至想也沒想就要打開車門跳下去。
賀言郁只覺得瘋了,把人抓回來摁在懷里。
“你是不是不要命了?!”他著安棠的下顎,眼神兇狠的質問:“這麼在意那紅繩,安棠,你是不是有事瞞著我?”
“啪——”安棠生氣得甩了他一掌,著氣,眼睛紅紅的,里面還藏著薄霧。
“賀言郁,你是不是有病?誰讓你扔我東西的?你有什麼資格這麼做?!”
Advertisement
越說越氣,越說越急,子開始不控制的發抖,指尖的發麻告訴,沒控制住緒,病又開始了。
車子不知不覺已經停在別墅外,安棠推開車門想原路返回去找丟下的紅繩,賀言郁的臉上頂著五指印,他臉沉得厲害,見安棠還想回去,他想也沒想,走過去拽著的手腕。
“我扔的東西,你能找回來,算我輸。”
他把不斷掙扎的人打橫抱起,任憑安棠對他又打又咬又發瘋,就是不肯松手。
賀言郁把人帶上樓,甚至還吩咐別墅的傭人好好守著,不準安棠跑出去。
周嬸聽見二樓傳來“砰”的一聲關門聲,嚇得抖了抖。
在別墅做工那麼久,還是第一次見賀言郁這麼生氣。
這小兩口最近怎麼經常吵架?
賀言郁把發瘋的安棠丟在床上,他站在床邊,居高臨下睥睨著發瘋的人,那副模樣,跟兩年半前纏著他時沒什麼兩樣。
“不就是一紅繩而已,扔就扔了,你以后要多,我可以給你多。”
安棠抱著腦袋急促的息,聽到這話更是大吼大的發瘋,不斷抄起東西砸他,語氣里抖的惡意:“滾!你給我滾!我不想再看到你!”
“滾啊——”
“不可理喻!”
賀言郁自知對已經夠好了,可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惹他生氣。
他冷冷的丟下一句話,轉離開房間,房門重新關上,安棠渾栗,不控制的發抖,指尖又麻又冷,急促的呼吸,像是瀕臨死亡的游魚。
跌跌撞撞又落魄的爬向床邊的屜,抖著手拉開,抓起撕了標簽的藥瓶,擰開,胡的將大把藥倒進里。
安棠的手在發抖,有些白藥粒從邊滾落到地上,近乎狼吞虎咽的咽下,因吃得過急,又忍不住想要干嘔。
這時,臺刮起風,將半掩的窗簾吹得輕輕飛舞,初夏時節,總是多雷雨。
沒過多久,外面傳來樹葉的沙沙聲,狂風大作,隨之而來的是電閃雷鳴。
隨著轟隆一聲驚雷炸響,屋里被閃電照得锃亮,安棠臉煞白,大了一聲,捂著耳朵蜷在床角。
“不……不要……”
“啊——”
猜你喜歡
-
連載938 章
厲少,你家影後又被拐跑了
那天與厲修年美麗的“邂逅”,蘇小悠便入了厲修年的坑。意想不到的是,厲修年身份不一般,咳嗽一聲!整個A市都要因為他顫三顫!麵對強勢如此厲修年費儘心機的製造“偶遇”,還有那隻對你一人的小溫柔,順利一點點收攏蘇小悠內心。蘇小悠:我要好好拍戲,努力賺錢,玩轉花花世界,迎娶高富帥,走上人生巔峰!厲修年:小悠,錢我有,你隻需要…來娶我。蘇小悠:厲先生,我從小無父無母窮的一批恐怕配不上你。厲修年:那便認祖歸宗,以後,我便是你的人生巔峰。
84.4萬字8 7324 -
完結1181 章

嚴爺家的小祖宗不能惹
【女強+玄學+甜爽】她說,她能壓制他身上的煞氣,他默許了他們交換來的婚約。訂婚宴剛過,她失蹤了。六年后,她帶著孩子回來,并在陰陽巷開了一間陰陽風水鋪。棺材鋪和香燭鋪送來棺材小件和金銀紙錢花籃,圍觀人群:怕不是砸場子的?明落塵笑著說:“百無禁忌,升棺發財,金銀滾滾來。”她算天算地算兇吉,一句話能斷人生死,成為風水界的頂級風水師。有人算計他和孩子,她為了他們,把這京城的天捅破了又如何?
224.3萬字8.33 54681 -
完結1007 章

和首富老公離婚後我爆紅了
三年前盛惜嫁給了A市第一首富陸劭崢。 她努力當好溫順本份的妻子,換來的卻是不屑一顧。 盛惜幡然醒悟,搞男人不如搞事業。 很快陸首富就收到了一份離婚協議書。 * 離婚前,在陸劭崢眼裏,盛惜溫柔漂亮聽話,但卻老實木訥毫無情趣可言。 而離婚後—— 公司旗下的直播平臺,甜美豪放的某一姐人氣火爆。 娛樂圈出了個當紅女王,身邊圍繞著各種俊男鮮肉大獻殷勤。 後來,某俱樂部里陸總又偶遇浪的沒邊,笑的不要太開心的女人。 女人感嘆:「果然還是年輕男人好啊,看看這腹肌,馬甲,人魚線」 「……」 陸總一張俊臉都氣歪了。 去他媽的老實乖順,這位前妻路子野的很! 一點也不老實! 當死對頭也拿著大鑽戒,笑的一臉風騷:「嫁給我,氣死你前夫」 陸首富:「???」 一個個都覬覦他老婆,當他是死的?!
88.4萬字8 149977 -
完結1006 章

退婚后被權爺寵上天
醉酒后,她主動招惹了他。男人目光如刃,薄情冷性,將她抵在墻角:“別招惹我,我怕你玩不起。” 后來,退婚、無家可歸的徐挽寧,跟他回了家。 結婚后, 徐挽寧成了后媽,養著別人的孩子,也明白他娶自己,不僅是因為自己聽話好拿捏,還因為她長得像一個人。 提出離婚時,他從身后擁住她,嗓音喑啞,“不離,行不行?” 她只勾唇輕笑:“二爺,您是不是玩不起。”
178.3萬字8 66443 -
完結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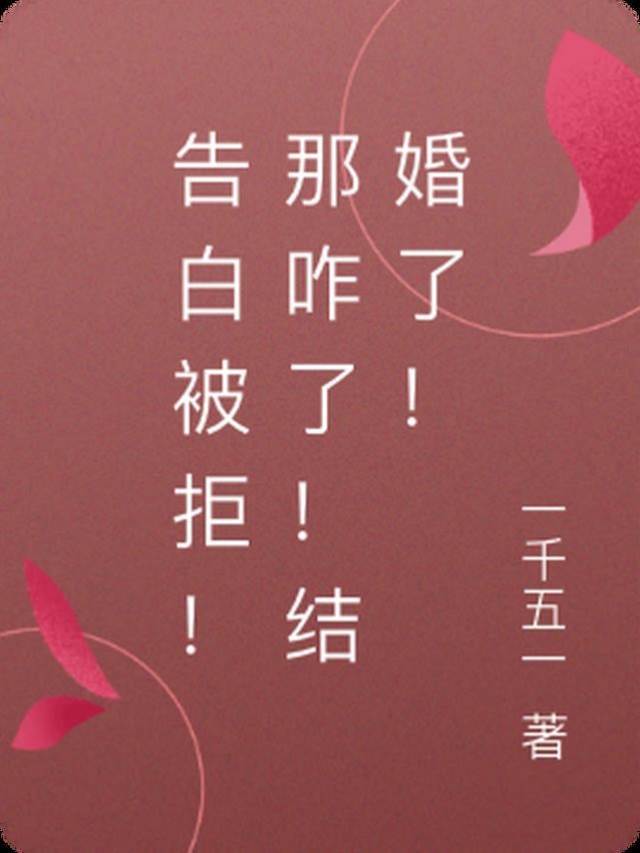
告白被拒!那咋了!結婚了!
【明著冷暗著騷男主VS明媚又慫但勇女主】(暗戀 雙潔 甜寵 豪門)蘇檸饞路遲緒許久,終於告白了——當著公司全高層的麵。然後被無情辭退。當晚她就撿漏把路遲緒給睡了,蘇檸覺得這波不虧。事發後,她準備跑路,一隻腳還沒踏上飛機,就被連人帶行李的綁了回來。36度的嘴說出讓人聽不懂的話:“結婚。”蘇檸:“腦子不好就去治。”後來,真結婚了。但是路遲緒出差了。蘇檸這麽過上了老公今晚不在家,喝酒蹦迪點男模,夜夜笙歌的瀟灑日子。直到某人提前回國,當場在酒店逮住蘇檸。“正好,這房開了不浪費。”蘇檸雙手被領帶捆在床頭,微微顫顫,後悔莫及。立意:見色起意,春風乍起。
26.9萬字8 988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