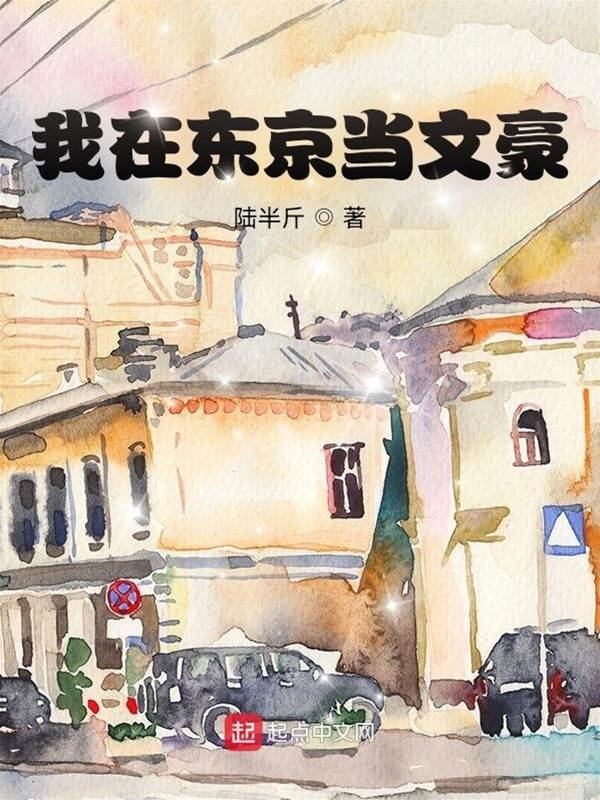《首輔為后:陛下,臣有罪!》 第三百一十四章 誰是登徒子
“爺,現在要怎麼辦?”
阿武恨不得立刻沖進去把那假扮顧文君的人揪出來,可是顧文君沒有下命令,阿武只能等在原地聽候吩咐。
他一向是很乖的。
顧文君腦海里轉過千萬種思緒,思考地很快,沒過多久就從短暫的驚疑之中恢復過來。
“既然來都已經來了。”顧文君一邊說著,一邊用扇子拿在手里把玩,“擇日不如撞日,今天我們就來看看,顧長禮到底是被什麼妖迷得找不著南北了!”
“是爺。”阿武恭敬地點了點頭,他足尖一點,便要撲倒墻壁上,順著這圍墻翻到屋檐潛這間屋子。
可下一刻顧文君就向他了手,“帶了荷包沒有?”
阿武的作生生被打斷,他愣怔地從懷里掏出一個鼓鼓的囊袋,“只帶了這些。”
顧文君接過來掂量了兩下:“也足夠了。”
扭手腕轉了轉扇子,將尾端抬起指向那間閉上大門的屋子,“阿武,你去敲門。”
“啊?!”這下阿武睜大眼,驚愕地張開了一句。
他滿心以為,顧文君要探查的意思,便是飛檐走壁潛探聽消息。這也是阿武從小到大到的訓練。
可現在顧文君卻打破了這個深固的念頭,還放話直接讓阿武去敲門。
阿武傻了。
“就這麼去敲門嗎?”他又問了一句。
“去!”顧文君強調,“之前問客棧店家的時候,我們不就是說自己想要買房子嗎,現在就裝像一點。”
顧文君抿一彎,勾出一抹笑:“我還就偏偏看中這一套了。”
聽了這話,阿武乖乖的去拍了那大門,只是因為爺被人假冒而生著氣,力氣難免大了點。
加上阿武本就是久經訓練的,那聲勢可就不一般了。
Advertisement
“啪啪啪!”
門被砸得作響,斑駁沉舊的門里還落下一些細碎的木屑。
顧文君凝眸觀察了一會兒,心里暗想:“看來顧長禮也是被管得,也就只能讓自己寵的人住這樣的地方。”
阿武拍門那樣用力,方圓幾里都能聽到,那屋子的主人也無法裝作聽不見。
僵持了半晌,最后還是有人來開門了。
木栓子被拉開,大門一開,木門的后面出了一張意秀的致容貌,眉黛細長,朱彎彎,眼波流轉間一顰一笑俱是迷人。
那人搭在門邊上,怯怯地著顧文君和阿武:“敢問這位公子,為何你家小廝敲奴家的門呀?”
那吳儂語,聽得人骨頭都了。
可惜,這態擺在顧文君和阿武面前,是演給瞎子看了。他們一個是假扮男子的兒,一個則是從小訓的太監暗衛,全是白費功夫。
相反阿武兩眼一圓,當即就了手指對準那子的臉。阿武是認出來了。
雖然這人會一兩手易容改貌的法子,可惜也沒有學到顧文君那般爐火純青的地步,還是有跡可循。
加上急匆匆地換了打扮出來,暴的地方就更多。
就比如那凌的發,沒有涂抹全的紅,還有畫出邊的眉……這麼多,就是阿武也能一眼辨認出不對。
這的,就是之前假扮顧文君的,氣勢洶洶的“面書生”!
“咳!”顧文君見不得那一張易容得滿是瑕疵的臉,故作掩飾地打開折扇遮了邊,免得笑出來,了餡。
那個子還以為是自己的了顧文君,含似怯地咬了咬,倒是有一天然帶的風。
“這位公子,奴家畢竟是單一人住在這里的,可不能再和你說話了,否則會傳出不好聽的話。”
Advertisement
顧文君收起扇子,客氣拜道:“抱歉,在下是來徽州趕考的,想要挑一風水寶地,特意找算命先生算了一卦,就是姑娘這住宅最能旺我。不知道姑娘能否割?”
只是一瞬間,顧文君便不假思索地想出了無可指摘的借口。
而且說起來淡定自若,一點也不像是編的。
要不是阿武跟著,他也要以為爺真是來買房的。
“啊!原來是這樣。”子終于松口:“奴家名柳柳,這是老爺給奴家買的,奴家也不知道能不能賣,還得問一問老爺才行。”
顧文君明眸微閃。
這人竟然真的是顧長禮養在外面的外室柳柳!
這柳柳此時看著弱弱,卻敢天化日跑到客棧里去假扮顧文君。若不是顧文君親眼所見,是不會信這樣的事。
這是想敗壞的名氣?還是想要算計什麼?
總不可能是顧長禮授意讓一個小妾去拋頭面吧,難不就是為了抹臟一個兒子的風評?顧文君百思不得其解。
怎麼就這麼巧。
柳柳扮“顧文君”,剛好挑中了這個真的顧文君在的客棧。
看起來,這位還沒有進顧家門的柳柳姨娘,甚至都不認得這個真正的顧文君。
一定有鬼!
顧文君沖阿武暗暗使了個眼,隨即試探:“那,能不能先讓我和我家小廝看一看宅子。”
“這……看這位公子,也不像是壞人。好吧,你們進來。”柳柳上下看了他們兩人好幾眼,尤其是在顧文君那張完如玉的臉上停留了片刻。
柳柳道:“但是門不能關上,否則胡同里又要傳些七八糟的事。”
顧文君記下這句話。
似乎這位柳柳,住在徽州也不平靜嘛。孤的貌子獨自住在偏僻的宅院,左鄰右舍應該有不閑話。
Advertisement
開始好奇,柳柳是怎麼接到顧長禮的。
柳柳在前面領路,顧文君和阿武跟上,暗中阿武傳來一句:“公子小心,這柳柳似乎有些功夫跟腳。”
顧文君也看出一些,但發現這功夫底子不深。
這柳柳一定是有問題的,可偏偏這些問題都大大咧咧地暴在顧文君眼前,幾乎一覽無余,反而讓顧文君覺更加疑心。
真不知道是這算計的人太心,還是另有圖謀。
顧文君盯著前面那道婀娜的姿不放,細細觀察,總覺得哪里有些不對勁。
“公子!”
不曾想,那柳柳陡然轉過,嗔怒起來:“你可別是登徒子吧,一直盯著奴家作甚!”
呸!
爺這樣一個天上謫仙般的人,豈能看到的上柳柳這種庸俗貨,倒也好意思說爺!
阿武不能發作,氣得鼓起臉。
顧文君為了掩飾自己的盯梢只好勾起一抹笑,假意調戲:“柳柳姑娘實在貌,在下也是難自。”
“哎呀討厭!”柳柳捂了捂臉,拒還迎的樣子倒真是一點都看不出不愿。
也不知道顧長禮若是看到這一幕,心里會作何他想。
顧文君不再一味看柳柳,而是打量四周。
雖然這屋子是破了些,可是里面的設施打扮卻是一應俱全的,大到桌椅屏風小到皿首飾,均是顧文君在江東顧家見到過的。
那顧長禮竟然把顧家的家當搬過來,給外室用。
真是迷昏了頭瘋啊!
恐怕那位繼母,都快要嫉恨到發瘋了吧。
柳柳還在往前面走著,再往前,可就是臥室床榻了。顧文君猛然警醒了過來,頓時剎住腳步。
不對!
這個柳柳說是要避嫌才把大門開著,不讓關。可柳柳如果真的那麼在意,怎麼可能連的名字都不問一聲,就直接將顧文君帶進來。
Advertisement
除非,這柳柳早就知道,顧文君是誰!
“在下看夠了,柳柳姑娘,這就先告辭了。”顧文君倉促行禮,便用余對著阿武一掃,示意撤退。
可柳柳卻如閃電般折過來,一反剛才弱姿態,一把拉住了顧文君,“等等呀,公子再進來看看吧!不是要買房子嗎?”
那的聲音此時卻讓人起皮疙瘩了。
顧文君竟然聽出了三分悉的覺,仿佛之前也在哪里聽過這個子的聲音。額頭微微冒汗,強作鎮定,“這還是等你老爺回來,再商議買房的事吧。”
“呵呵。”柳柳笑,“顧公子,你還是那麼聰明。”
這的果然是一早就認出了顧文君!
顧文君預不妙。
阿武圓目大睜,高喝道:“放開爺!”
然而他的聲音卻被柳柳乍然響起的尖完全了過去:“啊啊啊!來人呀,救命!有人非禮奴家!”
柳柳眼睛一便落了淚,哭花了妝容,一邊自己撕了一邊。
“是顧文君!是顧文君闖進來的!”
外面的大門敞開,聲音輕易便能傳出去,引來人。
顧文君總算是知道,柳柳為什麼假扮“顧文君”了,要是能引來真的顧文君,是最好不過,要是引不來,扮假的自導自演,也能一半事。
心中一窒,只想知道一件事,到底是誰在背后這麼算計?!
猜你喜歡
-
完結1574 章

盛世天驕
她是華夏第一神醫,扁鵲傳人,活死人、生白骨。 她年少得志,光芒萬丈,風頭無人能敵。 嫁給那個男人后,卻被他丟棄在別院,人人可欺……他是東林第一戰神,北國天驕,平四方,震天下。 他威名赫赫,驚才絕艷,縱橫沙場無敵手,卻栽在那個女人手上,如她所愿臣服在她身下…… 她一手醫術救人無數,他一把長槍殺人如麻;世家名門敬她如上賓,權貴重臣視他如猛虎。 她驕傲,他狂妄;她聰慧,他腹黑;她倔強,他強勢;她喜歡他卻不說,他心悅她卻不言…… 天驕遇神醫,試問蒼茫大地,誰先低頭?
279.3萬字8 167970 -
完結1597 章

嫡長女她又美又颯
前世,鎮國公府,一朝傾塌灰飛煙滅。 此生,嫡長女白卿言重生一世,絕不讓白家再步前世后塵。 白家男兒已死,大都城再無白家立錐之地? 大魏國富商蕭容衍道:百年將門鎮國公府白家,從不出廢物,女兒家也不例外。 后來…… 白家大姑娘,是一代戰神,成就不敗神話。 白家二姑娘,是朝堂新貴忠勇侯府手段了得的當家主母。 白家三姑娘,是天下第二富商,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商界翹楚。 · 白卿言感念蕭容衍上輩子曾幫她數次,暗中送了幾次消息。 雪夜,被堵城外。 蕭容衍:白姑娘三番四次救蕭某于水火,是否心悅蕭某? 白卿言:蕭公子誤會。 蕭容衍:蕭某三番四次救白姑娘于水火,白姑娘可否心悅蕭某? 白卿言:…… 標簽:重生 寵文 殺伐果斷 權謀 爽文
284.8萬字8 148905 -
連載912 章

扛著AK闖大明
崇禎十七年春,闖軍圍困北京城, 延續兩百七十餘年的大明王朝風雨飄搖, 當是時, 北有滿清多爾袞,南有黃虎張獻忠, 西有闖王李自成,東有海盜鄭芝龍, 值此危難之際, 醫科大學的大三學生劉鴻漸魂穿到一個破落的士族家庭, 靠著一百把AKM, 拳打內賊東林黨, 腳踢北蠻多爾袞,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怀揣著中興大明的夢想, 且看劉鴻漸如何上演一番波瀾壯闊的大明風流
185.3萬字8 14247 -
連載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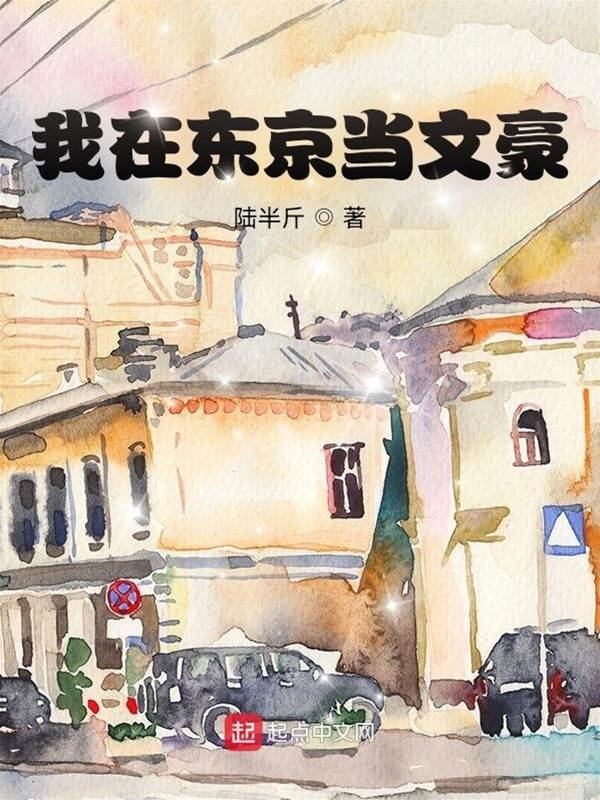
我在東京當文豪
這個霓虹似乎不太一樣,泡沫被戳破之後,一切都呈現出下劃線。 原本那些本該出現的作家沒有出現,反而是一些筆者在無力的批判這個世界…… 這個霓虹需要一個文豪,一個思想標桿…… 穿越到這個世界的陳初成爲了一位居酒屋內的夥計北島駒,看著孑然一身的自己,以及對未來的迷茫;北島駒決定用他所具有的優勢去賺錢,於是一本叫做暮景的鏡小說撬開了新潮的大門,而後這本書被賦予了一個唯美的名字:雪國。 之後,北島駒這個名字成爲了各類文學刊物上的常客。 所有的人都會說:看吧,這個時候,我們有了我們精神的歸屬……
41.5萬字8.18 140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