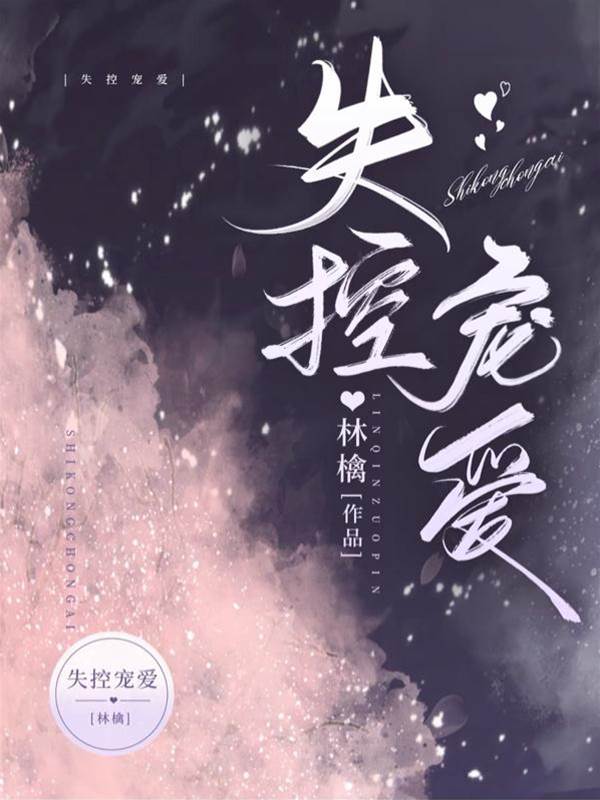《強勢暖婚:總裁別撩我》 第一章:片場驚魂
真是看錯了人,趁火打劫這種事,他比他媽做的更順手!
桌面上的手機響起,不用看也知道是他打來的。
白木嵐不接,它就一直響。
氣的拿起手機一把砸在了門上!
啪嗒一聲,手機摔了兩半。
鈴聲終于消失了。
白木嵐跌坐在辦公椅上,深吸幾口氣,撥通了助理的電話:“幫我聯系廖導,今晚就進組。”
眼不見心不煩,或許不看到他,就不會想起昨晚的事。
但實際上,即便睡在劇組安排好的酒店里,也依然睡不著覺。
在夢里,那些片段翻過來調過去的閃現,直到天空發白,始終揮之不去。
白木嵐又又氣,怕是要神經衰弱了。
掀開被子,洗漱完后便抱著劇本就去了片場。
片場位于S市的一個山上,山明水秀,鳥語花香。
倒是讓舒服了不。
“嵐姐,早。”
“早。”
白木嵐微笑,一路跟攝制組的人打招呼。
突然邊傳來一聲冷笑,一個小姑娘從邊大搖大擺地走了過去。
Advertisement
白木嵐沒在意,可抬眸就見那姑娘揚著尖下雙手抱站在屋子門前的臺階上斜眼看。
一副黑超遮住大半個臉,只留下半個尖下高高揚起。
一個助理給撐著遮傘,一個助理給拎著大包小包。
拿下墨鏡,從上到下冷冷的打量著,然后撐著下,不屑的說了聲:“不過如此。”
這是——新生代小花陳晨?
白木嵐擰起了眉,這莫名的敵意,從何而來啊?
還沒開口,就聽到廖明義氣急敗環的聲音:“陳晨,幾點了,還楞干什麼,快去換戲服!”
那個陳晨的小花立馬不服氣的進了屋。
廖明義噠噠噠的跑來招呼,臉上都快笑出了褶子,“木嵐啊,跟組苦,你要是有什麼需要盡管提,別什麼都藏在肚子里,讓自己委屈。”
他還在因為上次的事自責,可早就不介意了,人在江湖,誰都有自己的不得已。
白木嵐把清風吹散的頭發撥弄到耳后,笑意的說:“廖導,有您關照,我會什麼委屈啊,您放心,我都好著呢。”
Advertisement
廖明義憨笑,您白大小姐要是不好就要到他不好了,三更半夜接到浩瀚集團那位的電話,差點沒把他嚇死。
人家臨時注資一個億,什麼都不求,只為了自己的人過的舒服點。
他要是再不識相,恐怕以后在業界也不用混了。
“木嵐啊,還是你大度,不計前嫌,有什麼問題盡管提,千萬別跟我客氣!”
白木嵐客氣的笑笑,在劇組里是主創陣容,整個劇組都客氣三分,還能有什麼問題。
難不還會跟人勾心斗角啊,那是小演員為求鏡頭干的事,也不到啊。
白木嵐一笑而過,轉頭的瞬間,猝不及防對上一雙蔑視的雙眼。
又是那個陳晨。
白木嵐偏著頭,掀開眼簾,勾起一抹冷笑:“陳小姐,仁和醫院的眼科我有悉的朋友,如果你需要,我可以介紹給你。”
什麼意思?
這個丑八怪竟然拐彎抹角的說眼睛有問題!
陳晨氣的當即跳腳,邊的助理拉都拉不住就聽罵了出來:“姓白的,你眼睛才有問題呢!”
Advertisement
“沒問題怎麼老斜著眼看人呢?”白木嵐臉上堆著笑,冷哼一聲,扭頭就走。
才沒這閑功夫跟浪費時間。
陳晨反應過來罵,當即揚起了掌要扇,小助理眼疾手快齊齊拉住了,氣的直朝走的方向踢。
“哼,長得那麼丑,陸總會看上?一定是勾引他的!”
白木嵐沒有走遠,被這一句話停了腳步,轉過,角噙著一抹若有若無的笑意,冷冷的看著,“你再說一遍?”
那目冷徹如寒冰,旁邊看熱鬧的人都止不住渾打怵。
旁邊小助理忙堵住陳晨的跟道歉:“嵐姐,陳晨還小,口不擇言,您大人大量!”
二十出頭了還小?怎麼不讓媽媽抱著,寸步不離啊?
廖明義看這邊氣氛不對,擰著眉過來厲聲喊:“都杵著干什麼?開拍了!”
圍觀的人群紛紛散開。
廖明義著臉勸白木嵐,“木嵐啊,陳晨可是我們高價請來的,這開拍第一天就有的戲,您可不能在這個關頭讓我白忙活一場,不懂事,等會拍戲的時候,我找機會幫你教訓!”
Advertisement
呵,幫公報私仇?
這廖導對還真夠偏。
白木嵐冷酷的瞥了們一眼,然后揚起白皙的臉,沖廖明義笑笑,“廖導,小事一樁,您就別開玩笑了。”
廖明義得了白木嵐的態度,便立刻飛回了拍攝組,他的時間寶貴,每浪費一秒,劇組就會損失大筆的開支,他必須保證拍攝工作如期完。
白木嵐走的慢,突然后一聲尖:“小心!”
轉頭,只見搭好的場景旁邊,一高高的燈架直直向來!
這要是砸到,非毀容不可!
白木嵐的大腦一片空白,整個人都忘記了反應。
猜你喜歡
-
完結1121 章

盛世婚寵:霸道老公好纏人
她愛他,愛入骨髓。但他於她除了陰謀就是欺騙。原來,在他心裡,最重要的那個人,並不是她。
192.8萬字8 11224 -
完結1606 章

替嫁后我被大佬纏上了
所有人都說,戰家大少爺是個死過三個老婆、還慘遭毀容的無能變態……喬希希看了一眼身旁長相極其俊美、馬甲一大籮筐的腹黑男人,“戰梟寒,你到底還有多少事瞞著我?”某男聞言,撲通一聲就跪在了搓衣板上,小聲嚶嚶,“老婆,跪到晚上可不可以進房?”
283.7萬字8.18 203657 -
完結304 章

寵婚入骨,陸爺放肆撩
甜寵+虐渣+微馬甲上一世,許楠清被渣男賤女所害,北城人人艷羨的一朵紅玫瑰被碾到泥里,最后落得一個慘死的下場而被她厭棄了一輩子的男人,為她報了仇,最后孤獨一生直到死去重生后,許楠清發誓要撕白蓮,虐渣男,以及——化身自家老公腿上的掛件,努力把他拐上床“老公,你的衣服都濕了呢,不脫下來嗎……”“老公,外面打雷了,我要和你一起睡……”“老公,我不嫌你年紀大……”外界傳聞高冷禁欲的北城陸爺,低頭看著攥著自己衣領的小姑娘,眼眸微深,卻不為所動直到她心灰意冷轉身之際,卻被他一把摟進懷里“不是說……一起睡?”
68.1萬字8 19307 -
完結235 章
退婚后,她被財閥大佬嬌養了
前腳退婚后腳閃婚。看著身邊新鮮出爐的老公,雖然介紹人說他又窮又窩囊,但安寧決定,看在這張臉的份兒上,她忍了。婚后沒多久,安寧忍不了了。“不是說鉆戒是九塊九包郵的嗎?為什麼我領導說是真的,價值一個億?”“她少看了一個零。”“……”“房子呢?”“自家的。一整個別墅區,都是。”“……”“陸!擎!澤!”“寶貝兒別生氣,小心動了胎氣!”
43萬字8.18 64823 -
完結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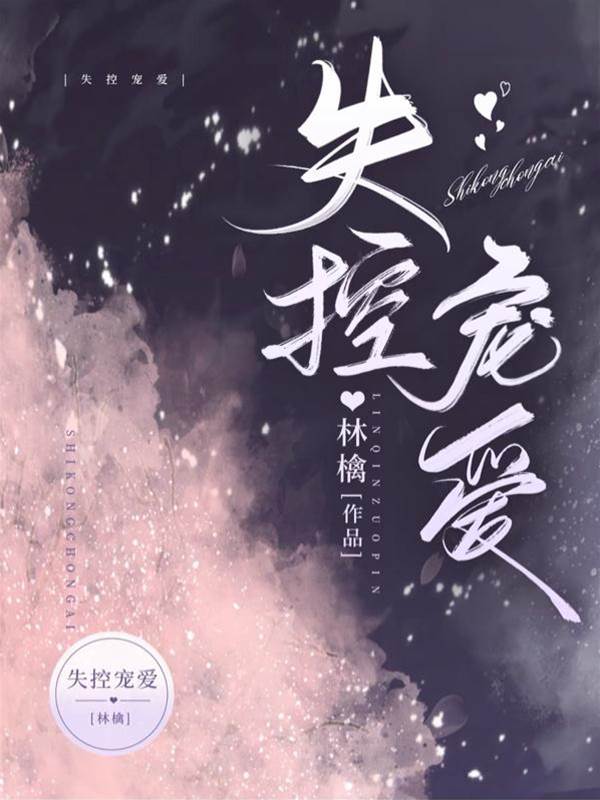
寵愛失控
【爆甜 雙潔 青梅竹馬養成係 男主暗戀】【腹黑爹係x直球甜心】對比親哥許初衍,許悄絕大部分的時間,都是被養在鄰家哥哥陸寂淵的身邊。許悄一直認為自己長大後一定會像長輩們說的那樣嫁給陸寂淵。直到有一天,室友疑雲滿腹的湊到她耳邊:“哪有人會在喜歡的人麵前活得跟個親爹似的啊?”“你們的認識這麼久了他都不告白...而且我昨天還看到他和一個女生在操場...”室友善意提醒:“悄悄,你別被他騙了。”-許悄覺得室友說的有道理。於是想抓住早戀的尾巴,來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就在許悄跟人約會的第一天,陸寂淵黑著一張臉找上門。被人掐著腰抵在牆上,許悄被親的喘不過氣,最後隻能無力的趴男人在身前。室內昏暗,陸寂淵的指腹摩挲著她的唇瓣,聲音低沉又危險。“小乖真是長大了啊。”連膽子都跟著大了起來。
19萬字8 1238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