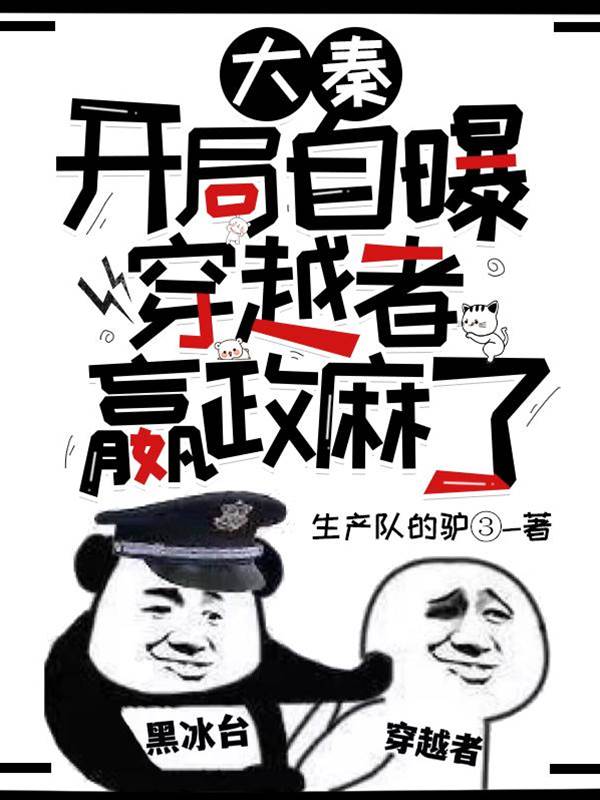《神醫嫡女》 第1230章 待嫁新娘
想容已經能出門了,雖然神頭兒還是沒有生病以前好,但總算沒了生命危險。羽珩說,只要保持心愉悅,按時吃飯吃藥,病就可以控制在一個可以承的程度。通常來說,這種心衰之癥往往都出現在上了年紀的人上,十幾歲的孩子就心衰實在見,只怪想容這孩子心事太重,自己把自己給折磨了這樣。但也好在足夠年輕,病好控制,也有恢復的可能。
三月初九,黛出嫁的前一晚,很多人都來到了居住的那間小院兒。羽珩、想容、任惜楓、風天玉、白芙蓉、安氏,還有一些京裡跟這幾位關係要好的小姐們也都過來給黛捧場。畢竟黛本並沒有什麼際,在京裡連一個真正的朋友都沒有,認識的人也不過就是在幾次宴會上說過幾句話,那樣的不足以讓人家帶著賀禮來賀的大婚。
但婚一回,沒有些姐妹送嫁也是不好看,好在羽珩和想容的人緣好,再加上任惜楓們也把自己的好友給張羅了來,這送嫁的隊伍一湊,也是十分壯觀,畢竟能跟羽珩任惜楓們好的小姐們都是很上檔次的。還有子睿,也從蕭州回了來,正帶著小寶在外廳玩耍,時不時的往裡面看一眼,面上掛著難掩的笑。
這些人的到來讓黛十分,在很久以前曾經想過,自己的大婚一定要風風,就算只是個庶,但那也是丞相府的庶,任何人衝著父親瑾元的面子也得給足了面。可是沒想到,家居然沒了,所以後來,就一度認爲自己的大婚會冷冷清清,因爲並沒有什麼好友可以邀請,就算黎王府會大宴賓朋,那也都是五皇子的面子,跟黛沒半點關係。
Advertisement
以前在府的時候,是庶,老太太總說一個庶就不要總是拋頭面,所以,跟想容從來都是被關在府裡輕易不讓出門的。後來能自己做自己的主了,卻又生分了心,跟誰都合不到一塊兒去。一來二去的,放眼整個兒京城,居然連一個能說得上話的朋友都沒有。
友歸友,親歸親,友人們到來,送了添妝之禮,說說笑笑好一陣後就依次散了,就連任惜楓三人也沒有多留。們都知道,家的孩子好不容易聚到一,總是要好好說說話的。
對於黛來說,不管外面來多人,唯有羽珩、想容還有安氏的到來,纔是最開心的。婚前最後一晚的小聚這主意是由羽珩主提及,跟黛說:“孩子出嫁以後就隨了夫姓,從今往後就是別人家裡的媳婦了,你的家庭員裡將不再有我們,一段新的生活即將開啓。那麼,對於過去種種,總是該有個告別的。我們今天來,一是爲你添妝,二也算是咱們姐妹在你婚前最後一次小聚,慶祝你即將嫁爲人婦。”
看著黛,這些年這孩子有了很多變化,樣子長開了,比小時候好看了,眼角眉稍有了瑾元的影子,再加上韓氏的好容,優點全都集中在黛這張臉上,憑心說,比跟想容都好看。“我這樣好看的妹妹,若是以後在黎王府捱了欺負,二姐姐一定替你做主。”
在外廳裡玩耍的小寶聽到了這話,大聲著:“不會!都是姐姐欺負姐夫。”
黛臉一紅,轉頭瞪了小寶一眼,然後不好意思地笑了開:“以前不懂事,爭取到這門親事的時候是爲了跟你們攀比,後來又覺得他沒長勁的,滿足不了我的虛榮心。可是後來,好像就是一夜之間,突然就覺得以前所在意的那些事是那麼的可笑,再回過頭想想玄天琰,才發現自己險些錯過了那麼好的一個人。二姐姐,你說我是不是特別傻,也特別招人煩?”
Advertisement
羽珩沒說話,想容到是先笑了開:“可不是麼,忒招人煩,小時候像個小跟屁蟲似的跟在我後,甩都甩不掉。”得知玄天華並沒有死,想容的心境也逐漸恢復,整個兒人又明朗了許多。跟黛說:“我記得小時候有一次我好不容易進了公中的大廚房,想兩個包子留著夜裡了吃。結果你就一直跟在我後面,怎麼也趕不走。後來沒辦法,好不容易來的兩個包子到底還是分了你一個。你說說,你是不是就爲了吃個包子?”
提起兒時的事,黛也來了神,同樣笑話想容:“你還好意思說我,又是誰總會地跟著二姐姐走啊?不敢靠近,就遠遠的,二姐姐一回頭你就往樹後頭鑽,小時候你那麼胖,一棵樹怎麼可能藏得住你。二姐姐,你到是說說,是不是發現了很多次,只是沒有揭穿而已?”
這是穿越以前的事,羽珩想了想,印象到不是很深。原主從前子冷淡,對府裡的庶姐庶妹都不是很親近,只能記得總會看到扎著兩顆丸子頭的想容會從遠地看,對於什麼藏到後頭的事,到是想不太起來。
見皺眉思索,想容和黛也是鬱悶了,想容說:“我們都能記得,二姐姐卻忘了,可見小時候二姐姐是真的不怎麼喜歡我們。”
黛也嘆氣,“是啊!我還記得有一次我摔了一跤,二姐姐看見了,只是下人過來扶我,自己卻轉走了,我當時傷心的。”回憶從前,沒有怨言,只是覺得在即將出嫁的日子裡說起往事,十分溫暖。
羽珩有些不好意思,出手,了兩個姐姐的頭,突然發現再做這樣的作已經有些不太協調了。十八歲,這兩個妹妹十六歲,黛長得量高些,已經快要超過,不是小孩子了,不能再頭。
Advertisement
慨,“一轉眼,咱們都長大了。離開府以前的很多事我都記得不是很清楚,因爲過得並不開心,所以刻意的不願去記。”
“二姐姐過得也不開心嗎?”問話的是黛,“其實這話我一直都很想問,因爲我沒做過府的嫡,從前又那麼的想做府嫡,所以我就特別想知道,做嫡到底是個什麼滋味?姚家出事之前,二姐姐是府裡最金貴的孩子,父親當時給你請了先生,又是教學問又是教琴棋書畫,我一直以爲你會很開心的。”
羽珩搖頭,“沒什麼開心的。”順著原主的記往回想,“那個時候……恩,已經有了對事非最基本的判斷能力,知道府裡在除了我母親之外還有很多姨娘。說實在的,你跟想容還算是好一些,除了你長到六七歲的時候就比較任之外,到是沒有別的太深印象。只是對沉魚記得多一些,因爲年長,已經學會怎麼欺負人。”
時值今日再提起沉魚,三人都已經沒了當初那種憎恨。時過境遷,恩怨仇都隨著生命的逝去了過眼煙雲,沉魚再可惡,也爲的所作所爲付出了該有的代價。若是再去因而生恨,那麼放不下的,可就是們了。》≠》≠》≠》≠,
想容說:“我有的時候就會想,如果當初不是這樣的,如果當初大姐姐心眼不壞,父親不偏心,不送走姚夫人,也不對大姐姐那樣的偏寵,說不定憑著的貌,真的能保家百年興旺。”
“哪有那麼些如果啊!”黛說,“這些事我在揚了瑾元骨灰那會兒就已經想過無數次,可就算人生能夠重來,你們信不信,沈氏和沉魚的心,依舊還會如此。”說完,又看向羽珩,猶豫了好半天,終於開口問道:“二姐姐以前對我們那樣冷淡,是不是因爲姨娘的緣故?姚夫人是主母,可父親的小妾卻一個接著一個的往府裡擡,孩子也一個接著一個的生,我還能記得姚夫人落寞的樣子,二姐姐肯定也討厭我們吧?”
Advertisement
羽珩又開始搜索原主的記憶,到還真如黛說得那樣,以前因爲們是庶庶子,所以原主從心裡往外的就排斥。還能想起姚氏不只一次地對原主說,男人三妻四妾是平常事,家家都是這樣過的。可原主當初怎麼回答的呢?說:姚家人男不納妾不爲妾,這個我是知道的。雖然母親不是妾,可父親納了妾,就是對母親最大的辱。
說起來,到底還是年紀小,不懂得理解母親。瑾元要娶,姚氏能有什麼辦法呢?
沒有避諱,衝著黛點頭道:“的確,我打從心裡瞧不起納妾的男人,也瞧不起爲妾的子,但卻又不得不對這樣的社會做以妥協。小時候不懂事,只一味的排斥,長大了才知,妻也好妾也罷,都不是人們能夠決定的。瑾元當初爲一朝左相,有錢有權有勢,被他看上了,不相嫁又能怎樣?”說罷,看了安氏一眼,“安姨娘不就是個例子嗎?我聽母親說過,你是不願嫁的,可因我母親府之後一直沒有孕,老太太著父親趕納妾爲家開枝散葉,後來父親就相中了你。”
提起往事,安氏也是一肚子的苦:“我當時跪著求到姚夫人,可姚夫人又能有什麼辦法呢?跟你們父親提了,結果被他打了一掌,說善妒,還被老太太關了佛堂。”
家的事一籮筐,以前誰都不願意提,可是今日再說起來,竟也覺有趣。幾人就好像是場外之人一樣,笑談府中事,到也愜意……
猜你喜歡
-
完結444 章

七零炮灰小辣妻
陸清清一覺睡醒來到了七零年代,懷裏躺了個崽子張嘴就喊娘。 可崽子他爹要離婚,大嫂二哥要分家,剩下個三哥是傻瓜....... 陸清清扶額,她這是穿到了死對頭寫的破書裏! 好巧不巧,她還有她全家,都是書裏的無名小炮灰..... 炮灰? 誓死不做! 七零小傻妻,身揣空間金手指,腳踩極品力虐渣,帶領全家翻身逆襲!
85.2萬字8 100967 -
完結94 章

穿成女兒奴大佬的前妻
江柔第一次看到那個男人是在審訊室里。落魄、沉默、陰鷙.狠辣的眼神,嘴角嘲諷的笑,但這人無疑又是好看的,哪怕已經四十了,眼角染上了細紋,依舊俊美非凡,很難想象他年輕那會兒是什麼模樣。這人叫黎宵,是警方追蹤了十一年的逃犯,這次能將他逮捕歸案,也…
37.7萬字8 10553 -
連載1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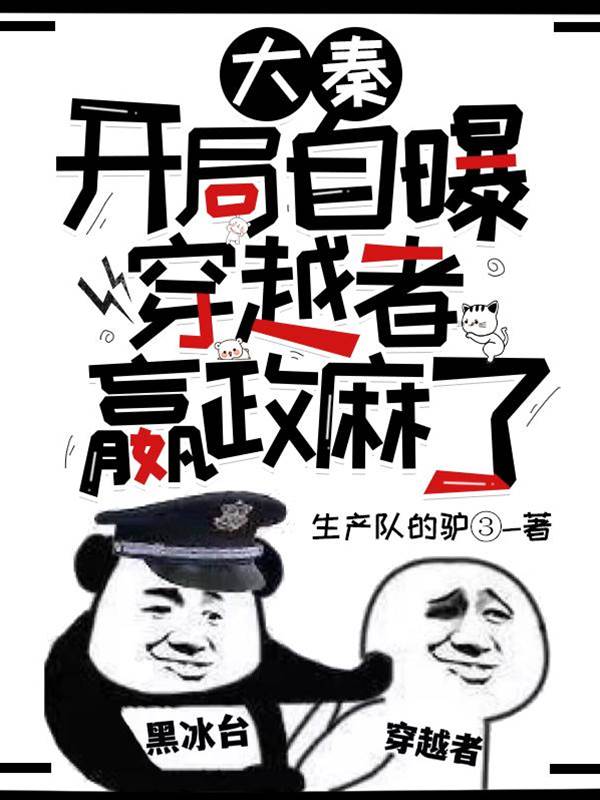
大秦:開局自曝穿越者,嬴政麻了
始皇帝三十二年。 千古一帝秦始皇第四次出巡,途经代郡左近。 闻听有豪强广聚钱粮,私铸刀兵,意图不轨,下令黑冰台派人彻查。 陈庆无奈之下,自曝穿越者身份,被刀剑架在脖子上押赴咸阳宫。 祖龙:寡人横扫六国,威加海内,尓安敢作乱犯上? 陈庆:陛下,我没想造反呀! 祖龙:那你积攒钱粮刀兵是为何? 陈庆:小民起码没想要造您的反。 祖龙:???你是说……不可能!就算没有寡人,还有扶苏! 陈庆:要是扶苏殿下没当皇帝呢? 祖龙:无论谁当这一国之君,大秦内有贤臣,外有良将,江山自然稳如泰山! 陈庆:要是您的贤臣和内侍勾结皇子造反呢? 祖龙:……谁干的?!我不管,只要是寡人的子孙在位,天下始终是大秦的! 陈庆:陛下,您的好大儿三年就把天下丢了。 祖龙:你你你……! 嬴政整个人都麻了!
247.2萬字8 911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