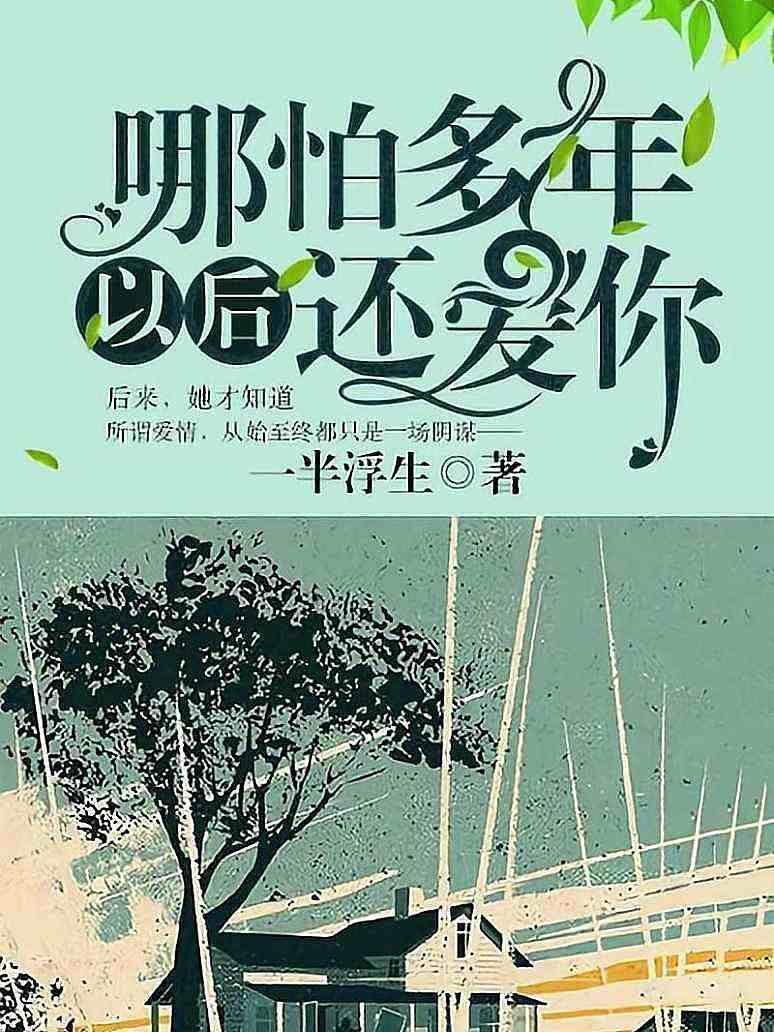《美人宜修》 第八十七章
隔天上午十點,戚年和葉長安簽了版權合同,正式開始合作。除了影視版權之外,葉長安又單獨準備了一份經紀合約。
這份合同是今早剛擬定的草約,葉長安名之初就簽署過一份經紀合約。質就和明星的經紀人差不多,有一個專業的經紀人打理各項版權,幫助理工作事宜。
如果戚年有全職的打算,這不失為是一個絕佳的選擇。
戚年從未對自己的漫畫生涯做過規劃,支撐站起來走到至今的理由已經沒有了,而下半年就將面臨實習就業的選擇,留給“小世界”的空余時間被。還沒有想好,這條路是否要繼續走下去。
大概是看穿了戚年的想法,葉長安邊挽起長發邊淡道:“大學的時候,我的時間很充裕。在別人還不諳世事的時候,我已經小有就。等一踏社會,邊的人還在忙碌庸擾何去何從的時候,我已經比們先登上了臺階。
現實生活的工作很難和這份職業相兼顧,我曾經也投過簡歷工作了一段時間。但我本不太適合哪種快節奏的工作生活,三個月后剛可以轉正我就離職全職寫文了。”
葉長安挽好長發,笑盈盈地看了一眼:“所有的選擇都是在嘗試后做出的,不用急著把你心里的回答告訴我。也許你更適合朝九晚五的工作,也許你也可以試著兩者兼顧,出于對你自己意愿的尊重,等想好之后再聯系我吧。這期間有任何工作問題,我會聯系你。”
話落,抬腕看了眼時間,推開椅子起:“我要去等阿哲一起吃午飯了,一起吧?”
0.0要、要一起嗎?
沒等戚年糾結出結果來,葉長安已經兀自替決定了:“一起吧,正好提前認識下導演,下次開策劃會就不用特意介紹了。”
Advertisement
葉長安說的導演……就是的先生沈默哲。沈默哲是娛樂圈當紅的一線大腕,這些年漸漸開始轉幕后,做過投資也做過出品,第一次下水執導就抱回了一座小金獎。
戚年想了想,問:“那我可以再帶一個人嗎?”
葉長安是知道戚年是一個人來的B市,就連酒店的房間都是定下的單人房,哪來的第二個人?
當下有些詫異地看了一眼,突然想起簽合同時眼角余瞄到的戒指。看到時還沒覺得什麼,現在定神看了眼,當下就有了答案:“可以啊,正好都認識。”
——
昨晚太晚,好吧,這不是理由。反正昨晚,戚年留宿在紀言信的房里,大約是太興,將近凌晨三點才睡著。這期間,翻個,起來喝口水……吵得紀言信也沒能睡好。
直到戚年困得沒力了,饒是神再,都昏昏沉沉地睡了過去。只不過,紀言信向來淺眠,被吵醒后,再沒能睡著。等九點醒戚年去簽合同后這才重新睡下……也不知道醒了沒有。
按了兩遍門鈴,才等到紀言信來開門。
剛洗過澡,上的白襯只隨意系了中間兩顆紐扣,松松垮垮地套在上。頭發半,他正用巾隨意地著,那袖口順著他高舉著手的作至手肘,出線條結實的小臂。
戚年默默地吞了口口水,強迫自己移開眼,剛對上他的視線,臉不住一紅,手足無措起來。
見杵在門口不進來,紀言信彎腰靠近,目和平視。剛清醒的聲音還帶著一厚重的磁,低聲問:“不進來?”
戚年這才想起過來的目的,咬了咬下,暗罵了一句沉迷沒出息。抬起頭時,格外神采奕奕地詢問:“要不要一起去吃飯?”
Advertisement
一起去?
紀言信挑眉,敏銳地察覺出的“一起”里面不止包括他。他頭發的作微頓了頓,握住的手腕把拉進房間,反手關上門的同時一步近把退兩步直抵在門后,輕輕松松地雙手一撐,把圈在了自己的勢力范圍。
驟然靠近的,那強烈的屬于他的氣息像一張無形的大網,在頃刻間把圍困在他的雙手之間,彈不得。
雖然……總時不時地被突襲,可總也沒習慣……
很滿意地看到的耳圈又開始泛紅,紀言信把手里的巾順手丟在進門的架子上。低頭輕咬了一口的下以示懲罰,這才含糊著問:“還有誰?”
“葉長安……”戚年被他咬疼了,嘶嘶地吸了兩口氣,想去捂又不敢,也不知道自己錯在了哪里,就這麼可憐兮兮地看著他。
那漉漉的,泛著水的眼睛直看得紀言信心,輕輕地覆上去吮了一口:“一大早是誰讓我帶去頂樓吃大餐的?”
“……”戚年一臉的懵。
誰??什麼時候?
紀言信一看的表就知道已經忘得一干二凈,撐在側的右手落下來,不輕不重地了一下的肩膀,無力地嘆了口氣:“就知道你剛睡醒的話不能聽。”
話落,他站直,沿著肩膀落下來的手握住的放在自己的口:“扣好就可以出門了。”
驀然到他溫熱的溫,戚年“嗖”的一下,回手:“扣……扣紐扣?”
紀言信無聲地用眼神詢問:“哪里有問題嗎?”
戚年搖頭,巍巍出手的同時忍不住小聲嘀咕了一句:“你不怕我把你服了嗎?”
紀言信低頭側耳,只來得及聽到后小半句,低低笑了兩聲,抬手了一下滾燙的耳朵:“了試試。”
Advertisement
那輕輕挲的作緩慢得讓戚年幾乎能覺到他微涼的指腹,連頭也不敢抬,抿了抿,盡量忽略耳朵上越來越磨人的輕捻慢,老老實實地把他沒扣上的紐扣扣上。
可偏偏他時輕時重的力道,充滿了暗示。等戚年從下往上扣到最后第二顆時,他不知何時已經低下頭,那溫熱的呼吸就在的耳邊,格外清晰。
耳子的紅已經開始蔓延到臉頰,戚年飛快地抬頭看了他一眼,沒等和他對視又低下頭,瞄著他線條的鎖骨,默默地在心底輕聲念:“要冷靜,冷靜,冷靜……”
然后……
一只手扶上了的后頸,他低沉的聲音就在耳邊:“還沒好,發什麼呆?”
戚年一個哆嗦,往領上最后一顆紐扣睨了眼,抬手去住又致的金紐扣。還未等把領口拉,他已經低下頭來,沿著的額頭一路吻下來。
溫地一點一點吻下來,覆上的角前,含糊地嘀咕了一聲:“改簽吧,我們今晚就回去,好不好?”
——
一起吃過午飯,已經是下午的一點。
回Z市的機票改簽功,原本和周欣欣定在今晚的會議臨時改期,就下午,在蔓草的小會議室開。
昨晚發生的事,戚年自己也有些自顧不暇。等坐在了會議室里,聽周欣欣說起,才知道重之下,路清舞已經刪了所有的微博,可依舊拒不回應。
榮品文化今早迫于力,已經用微發表了申明。表示這件事榮品也是害者,現已辭退肖黎黎,并追究路清舞的違約行為,要求賠償。
除此之外,之前周欣欣在漫繪上整理歸納的“路清舞抄襲”,終于得到重視,被漫友翻出來一一審對。網上追究責任的聲音,鋪天蓋地。
Advertisement
而這一次會議的容,就是戚年要不要起訴。蔓草作為戚年的老東家,這一次自然是鼎力支持,追究路清舞的侵權行為。
戚年沉默了很久,久到周欣欣都以為要被圣母附決定原諒路清舞時,才清了清嗓子,一字一句道:“為什麼不?”
把握在手心里良久的手機推到周欣欣的面前,啞聲道:“路清舞給我發信息了。”
從一個小時前,間斷地一直在給發短信,從起初的不知悔改地威脅放狠話,到現在的低聲求饒,求放過……路清舞已經把的尊嚴徹底踩在了腳底下。
知道錯了又怎麼樣?總要有人對這四年來負責。
更何況,做得那些事,樁樁件件都犯了的底線,為什麼要去原諒這樣一個人?
周欣欣看完氣得都要歪了,格外慶幸戚年依舊保持著理智:“講真的,要是道個歉你就收手了,我真跟你絕。”
戚年默。
又不是傻,更何況,路清舞傷害了最的人。差一點……差一點就以為,要失去他了。
會議結束后,會議室只留了整理筆記的周欣欣和在等紀言信的戚年。
周欣欣整理著整理著,用筆帽杵著眉心問道:“你難道就不好奇你紀老師在這里面下了多功夫?”
戚年咬著紙杯,盯著共位置里越來越近的箭頭指標,心不在焉地回答了一句:“他沒說,就告訴我……”
話音未落,會議室的門被推開。
暖意未退的夕余里,紀言信姿拔地站在門口,朝勾了勾手指:“走,我們回家了。”
猜你喜歡
-
完結572 章

一吻成癮
那一夜,她大膽熱辣,纏綿過后,本以為兩人不會再有交集,卻在回國后再次重逢,而他的未婚妻,竟是自己同父異母的姐姐!…
126.6萬字8 60809 -
完結73 章

過分偏愛
京州圈人人皆知,季家二少,薄情淡漠,不近女色。年初剛過24歲生日,卻是個實打實的母胎單身。圈中的風言風語越傳越兇,最后荒唐到竟說季忱是個Gay。公司上市之際,媒體問及此事。對此,季忱淡淡一笑,目光掃過不遠處佯裝鎮定的明薇。“有喜歡的人,正等她回心轉意。”語氣中盡是寵溺與無奈。-Amor發布季度新款高定,明薇作為設計師上臺,女人一襲白裙,莞爾而笑。記者捕風捉影,“明小姐,外界皆知您與季總關系不一般,對此您有何看法?”明薇面不改色:“季總高不可攀,都是謠言罷了。”不曾想當晚明薇回到家,進門便被男人攬住腰肢控在懷里,清冽的氣息占據她所有感官,薄唇落到她嘴角輕吻。明薇抵住他的胸膛,“季忱我們還在吵架!”季忱置若未聞,彎下腰將人抱起——“乖一點兒,以后只給你攀。” -小劇場-總裁辦公室新來一位秘書,身段婀娜,身上有股誘人的香水味。明薇翹起眉梢笑:“季總,那姑娘穿了事后清晨的香水。”季忱:“所以?” “你自己體會。”當晚,季忱噴著同款男香出現在明薇房間門前,衣襟大敞鎖骨半遮半掩,勾人的味道縈繞在她鼻尖。明薇不自覺撇開視線:“……狐貍精。” 【高奢品牌公司總裁x又美又颯設計師】 一句話簡介:悶騷一時爽,追妻火葬場。
19.6萬字8 19912 -
完結207 章
壞男強吻:契約甜心
她失戀了,到酒吧買醉後出來,卻誤把一輛私家車當作了的士。死皮賴臉地賴上車後,仰著頭跟陌生男人索吻。並問他吻得是否銷魂。翌日醒來,一個女人將一張百萬支票遞給她,她冷笑著將支票撕成粉碎,“你誤會了!是我嫖的他!這裏是五萬!算是我嫖了你BOSS的嫖資吧!”
41.3萬字8 38579 -
完結485 章

感化暴戾大佬失敗后,我被誘婚了
桑家大小姐桑淺淺十八歲那年,對沈寒御一見鐘情。“沈寒御,我喜歡你。”“可我不喜歡你。”沈寒御無情開口,字字鏗鏘,“現在不會,以后也不會。”大小姐一怒之下,打算教訓沈寒御。卻發現沈寒御未來可能是個暴戾殘忍的大佬,還會害得桑家家破人亡?桑淺淺麻溜滾了:大佬她喜歡不起,還是“死遁”為上策。沈寒御曾對桑淺淺憎厭有加,她走后,他卻癡念近乎瘋魔。遠遁他鄉的桑淺淺過得逍遙自在。某日突然聽聞,商界大佬沈寒御瘋批般挖了她的墓地,四處找她。桑淺淺心中警鈴大作,收拾東西就要跑路。結果拉開門,沈大佬黑著臉站在門外,咬...
87.4萬字8.18 29488 -
完結897 章

蝕骨囚婚
追逐段寒成多年,方元霜飛蛾撲火,最後粉身碎骨。不僅落了個善妒殺人的罪名,還失去了眾星捧月的身份。遠去三年,她受盡苦楚,失去了仰望他的資格。-可當她與他人訂婚,即將步入婚姻殿堂,段寒成卻幡然醒悟。他動用手段,強行用戒指套牢她的半生,占據了丈夫的身份。他畫地為牢,他與她都是這場婚姻的囚徒。
119萬字8.18 15163 -
完結23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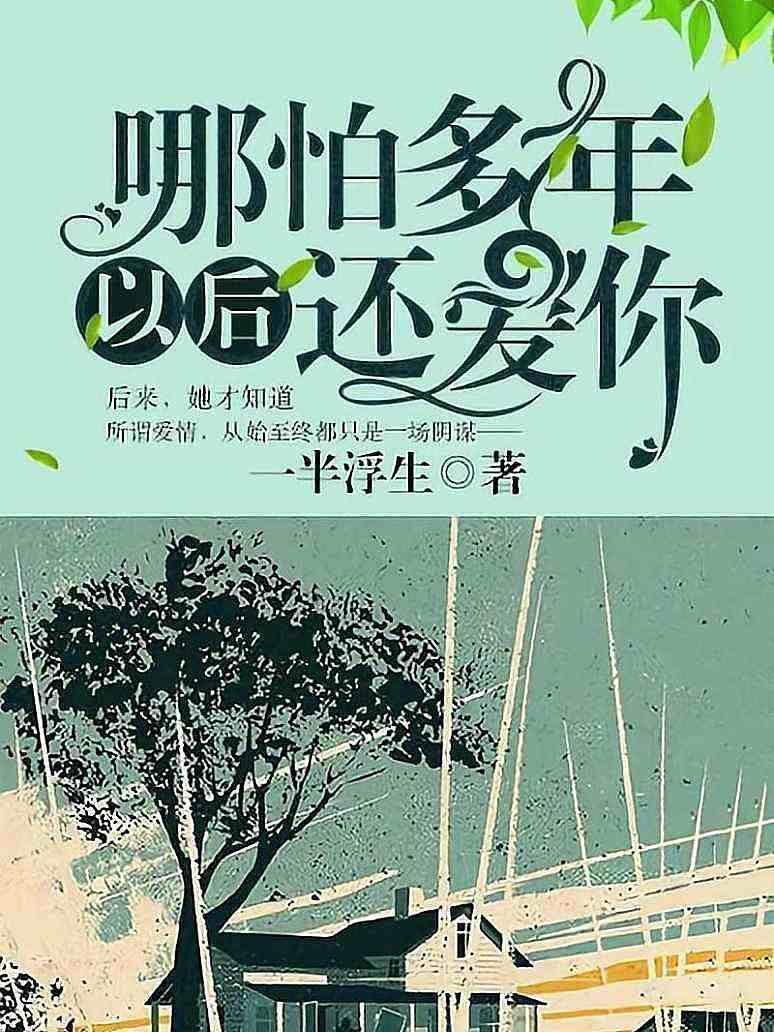
哪怕多年以后還愛你
“生意麼,和誰都是談。多少錢一次?”他點著煙漫不經心的問。 周合沒有抬頭,一本正經的說:“您救了我,我怎麼能讓您吃虧。” 他挑眉,興致盎然的看著她。 周合對上他的眼眸,誠懇的說:“以您這相貌,走哪兒都能飛上枝頭。我一窮二白,自然是不能玷污了您。” 她曾以為,他是照進她陰暗的人生里的陽光。直到最后,才知道,她所以為的愛情,從頭到尾,都只是一場陰謀。
107.8萬字8 356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