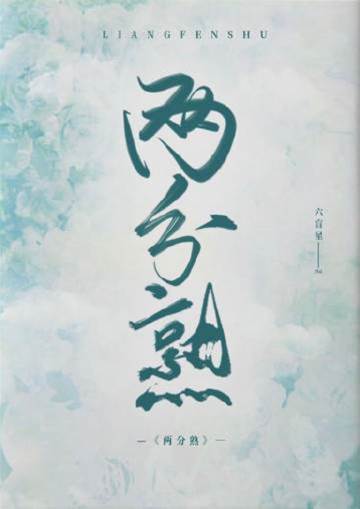《在冷漠的他懷裏撒個嬌》 第7章 你心疼我
安可走投無路,於是ue到了寂白,希幫忙解釋。
現在,寂白的微博量幾乎是呈次方數增長,無數網友詢問寂白,讓解釋一下吸的事,甚至還有幾個昏頭的網友厲聲質問,為什麽要和安可沆瀣一氣陷害自己的姐姐。
寂緋緋的微博數百萬,但並非所有人都在關心寂緋緋撕的事,年齡稍大的網友對此事不置一詞,激跳腳的都是比較容易被煽的年輕。
僅僅一時間,寂白的微博數量達到了四萬。
網友們都等待著寂白的回答。
不過要讓他們失了,寂白不會回應任何事。
一則安可曾經瘋狗咬人地針對過;二則,現在還未時過早。
重生回來,寂白明白了一個非常深刻的道理,你能出來的委屈,都不委屈,而是辯解;隻有別人覺到你的委屈,才是真的委屈。
所以不會再像上一世那樣去訴苦了。
寂緋緋心裏是有點害怕的,寂白的微博現在被很多發現了,非常擔心妹妹會出有損形象的話。
不過幸好,寂白的微博一片安靜,並沒有回應安可。
寂白的微博裏大多是積極好的容,譬如去閨家開趴,或者逛逛街喝茶之類雖然偶爾流出對輸的不願意,但是言辭並不激烈,也沒有寂緋緋的壞話,對沒不良影響。
寂緋緋安心了,和寂白僵持的關係也緩和了不,又開始虛偽地對噓寒問暖,關懷備至。
父母看到這樣的形,自然滿懷欣。
半個月後,安可的父母登門,親自向寂緋緋道歉,希能放自家兒一馬,現在安可整神神叨叨的,看了醫生可能出現抑鬱的傾向。
這一切全拜寂緋緋所賜,安可的父母對寂緋緋恨得咬牙切齒,但是為了自家兒能夠從這段噩夢中走出來,他們還是腆著臉登門,親自向寂緋緋道了歉。
Advertisement
寂緋緋接了長輩的道歉,出麵安躁的們,這件事是一個誤會,現在安可已經認識到錯誤了,希們不要再對進行人攻擊,讓這一切過去吧。
們罵了好幾,終於是罵不了,消停下來,安可也刪掉了@寂白的微博,這件事總算是告一段落了。
半個月後,安可回到了學校,原本開朗的格變得有些鬱。
相安無事到了九月下旬,謝隨和幾個哥們走出教學樓,路過重新翻修的自行車棚。
幾個沒長眼的大男孩一陣風似的跑過,帶翻了一排的自行車,嘩嘩啦啦的連鎖反應,驚得路人回頭觀。
謝隨了耳朵,偏頭便見了倒在地上的一輛白的車。
車是折疊式的,車被洗得幹幹淨淨,籠頭前還掛著清新的白籃子。
幾個黑恤大男孩對自己的無心之失渾然不覺,嬉笑打鬧著離開,不想謝隨突然側,擋住了他們前麵的路。
幾人防備地問:“你幹什麽?”
謝隨向那輛紅的自行車,冷峻的眉眼挑了挑,嗓音低沉而冰冷——
“扶起來。”
黑恤的男孩訕訕地:“你管太多了吧。”
謝隨微微側頭,活了一下脖頸,作略有些跋扈。
“不要讓我重複第二遍。”
黑恤男孩惹不起謝隨,心裏發怵得厲害,隻能服了,走到自行車棚邊,將四下裏絆倒的自行車一一地扶起來。
“這樣行了吧。”
謝隨給他讓開了道,語調平靜卻帶著不怒自威的味道——
“走路看著些。”
待那幾個男孩離開以後,叢喻舟溜達到自行車跟前,著下頜觀察了好一陣:“讓我用火眼金睛好好看看,這車是孩的?”
謝隨沒有理他,屋子從包裏出紙巾,了自行車坐墊上沾染的泥灰。
Advertisement
“不會吧!就這車車,還勞煩您老人家親自拭呢,給我得了。”
叢喻舟正要接過紙巾,謝隨推開他:“不用。”
叢喻舟眼角暈開了笑意,抱著手臂和兄弟們斜倚在邊上看熱鬧:“隨哥,這車籃子好像歪了。”
謝隨繞到前麵檢查,車籃子還真是歪歪斜斜地耷拉著。
這個容易,掰正就行了。
他手一掰,“哐”的一聲,車籃子他媽居然掉下來了!
謝隨看著手裏的車籃,又抬頭了幾個兄弟,角扯了扯。
叢喻舟也是一臉懵:“這隨哥不愧是拳王,好手勁兒啊。”
好巧不巧就在這時,寂白背著書包從教學樓出來,車棚邊停下腳步。
的車籃子還在謝隨的手裏。
“”
被那雙黑漆漆的鹿眼凝視著,不怕地不怕的謝隨,有那麽一瞬間,居然他媽的心虛了。
“謝隨,你為什麽要這樣做?”
寂白的嗓音略帶自然的沙啞,語氣如同的表一般,波瀾不驚。
不知道為什麽,謝隨很喜歡聽他的名字,謝隨,謝隨,調子很沉,但是帶著一種特別認真的質。
“我”
什麽都能丟,麵子不能丟。
謝隨當下便冷了臉,兇狠地:“這什麽破爛玩意兒,擋著老子的路了。”
他完,還把籃子擲了出去,籃子在地上滾了幾圈,滾到寂白的腳下,更加變形了。
叢喻舟角,艱難地咽了口唾沫。
大哥啊,追孩不是你這樣追的啊!
寂白眼睜睜看著車籃子滾到了腳邊,蹲下把它撿了起來,拍了拍灰塵和泥土,一言不發地走到車邊,嚐試著將它裝回車龍頭上。
謝隨見這不溫不火的模樣,有些耐不住子了:“你就不會跟老子生個氣試試?”
寂白老實地:“我怕你打我。”
Advertisement
“他媽你怎麽總覺得老子要打你。”
寂白抬起頭,漆黑的眸子掃向他:“你騎車撞過我。”
謝隨結上下滾了滾,良久,他視線側向一邊,憋了很久,也沒能憋出一句對不起。
謝隨何時跟人過對不起。
寂白見籃子實在是裝不上去了,隻能放棄,將籃子掛在車後座,反正學校外麵還有修理鋪。
寂白推著車要離開,經過謝隨邊的時候,謝隨突然手掌住了的肩膀。
襯的料子是雪紡的,很,也很單薄,他甚至過料到了肩帶的形狀。
豔高照的一,氣溫很暖,風很燥。
他發覺自己的掌心有些,詫異地看了看自己的手,口而出:“你怎麽這麽?”
話剛問出來,後一幫男孩立刻流出了意味深長的壞笑。
他問得有歧義了。
寂白的臉頰變得緋紅,的質和別的孩不一樣,縱然是在盛夏,別的孩都不會多汗。
偏偏,即便是在冬日裏,隻要氣溫稍高,都會出汗。
所以每都會洗澡,縱使如此,還是招架不住的“充盈”。
上一世,謝隨總會問,為什麽,為什麽你那麽?
寂白會屈辱地咬住牙,才不會告訴謝隨,熱起來的時候,真的很想
可是下i過傷的謝隨,偏偏不能。
寂白敏地往後退了兩步,因為車棚狹窄,又推著車,險些絆倒了。
謝隨連忙手攬住,這一攬,直接被謝隨兜進了懷裏,腦袋重重地砸在了他堅的上。
鼻息間,充盈著他的味道,那是一種淡淡的薄荷草的氣息,讓想起了躁騰騰的夏日。
他隻穿了一件單薄的恤,很燙,寂白覺到他充實的度
立刻掙開了他,防備地往後退了退。
Advertisement
謝隨看了看自己的手,更潤了,他後背脊梁骨竄起了一陣激靈。
的也太水了吧。
寂白以為他是嫌髒,紅了臉,咬著牙推車離開:“你別我了。”
謝隨著的背影,心髒都快跳炸了。
**
寂白心裏也暗罵謝隨,蠻橫不講理,不過仔細一想,他什麽時候講過理,從來都是這樣胡攪蠻纏。
將自行車推到了校外的修車鋪:“師傅,你看我這籃子,能裝回去嗎?”
師傅穿著黑漆漆的皮革圍走過來,接過寂白的車籃子:“你這都變形了,裝不了了,換一個吧,我這裏什麽樣的籃子都有,你選選。”
“不能修了嗎?”
“修不了,這都壞什麽樣了。”
“那新裝一個多錢啊。”
“五十的七十的,你想要好一點的也有,一百二。”
“這也太貴了吧。”
寂白家裏雖然不差這點錢,但是決定了要在二十三歲之前經濟獨立,所以平日裏不會花錢,零用錢生活費什麽的,全都攢著,能多一分是一分。
就在寂白糾結之時,男人走了過來,撿起了地上的鐵籃子,不由分便推起了寂白的自行車,離開。
“哎!”寂白追上去,按住車龍頭:“謝隨,你幹什麽!”
謝隨偏頭道:“我帶你去一個地方,能修。”
寂白半信半疑地跟著謝隨,走在他邊。
他個子高大,推著的白自行車,看上去不協調。
走了得有好幾公裏了吧,寂白實在忍不住,問道:“什麽地方能修呀?”
“哪那麽多廢話。”
寂白頓了頓,決定放棄,他不想就不會,晴不定,誰都不準他的心思。
沉默了幾分鍾,又想起另外一件事,忍不住問:“謝隨,你為什麽會送我止疼藥?”
“不知道。”
“哦,那謝謝。”
“閉。”
“……”
他就是這樣一個怪人,寂白已經放棄和他流了。
謝隨將自行車推上了長江大橋的人行步道,左側是奔流不息的車道,而右側是波濤洶湧的江麵。
江風很大,吹拂著寂白額前的劉海,招招搖搖,著的鼻尖,微,手了。
偏頭發現謝隨在看。手機端一秒記住筆\趣\閣→\B\iq\u\g\ev\\為您提供彩\說閱讀。
被抓包的謝隨立刻別過頭,故作漫不經心地平視前方。
寂白看到他左耳上的黑曜石耳釘切割了夕,刺眼灼目,很漂亮。
男孩戴耳釘很,但他不,他的氣質很,耳釘也能戴出他獨特的男人味。
“這都過江了,你到底帶我去哪裏啊。”
謝隨依舊不話,過了江之後,他將自行車停在了橋頭兩間鋪的汽修店。
寂白打量著店鋪,鋪子坐落在橋頭的十字路口邊,煙塵很大,不過位置還算不錯。
店鋪裏停了兩輛看上去非常酷炫的改裝超跑,有幾個工人正在車底忙碌著。
“隨來了。”
“嗯。”
謝隨門路地走進去,拿出了鑷子鐵一類的工,蹲下對著鐵籃子搗鼓了一陣,然後將籃子裝在自行車龍頭上,用鋼固定住,甚至還拿出了電焊槍,啪啪啪地打了火
寂白忐忑地問:“這樣行不行啊。”
謝隨完全沒有理會,將鐵籃子焊在了龍頭上。
“那人騙你。”他開口:“能修好,他騙你買新的。”
“哦。”
“以後車壞了,可以來找我。”他頓了頓,又補充道:“找別人會被坑。”
寂白不知道,謝隨還有這種手藝,隻知道他會改裝賽車,沒想到還能修自行車。
籃子被穩穩當當地裝在了車龍頭上。
“謝隨,這裏是你家開的啊?”寂白了這間汽修鋪,鋪子門麵還大,裏麵有不改裝車。
“不是。”謝隨淡淡道:“我在這裏打工,管住宿。”
“噢。”都差點忘了,謝隨出底層,很窮。
不知道為什麽,寂白心裏有點酸,其實一早就知道他很苦,但是知道歸知道,親眼看見卻又是另一種覺。
謝隨何等敏銳的心思,一眼便看出了腦子裏在想什麽。
他臉沉了沉:“看不起老子?”
寂白連連搖頭,不是的!
或許會看不起寂緋緋的虛偽,安可的囂張,甚至父母的無能和偏心,在這個世界上,唯一不會看不起,就是謝隨。
其實謝隨也是故意嚇唬的,他能覺到,寂白和別的孩不一樣,眸子裏著一溫暖與好,令他不自想要靠近。
“那我知道了。”
寂白連忙問:“你知道什麽了!”
年低著頭,角勾起一抹微笑:“你心疼我。”
猜你喜歡
-
完結1070 章

奉子成婚:古少,求離婚(又名:離婚時愛你)
新婚夜,他給她一紙協議,“孩子出生後,便離婚。” 可為什麼孩子出生後,彆說離婚,連離床都不能……
171萬字8 365384 -
完結46 章

你如星辰不可及
蘇清下意識的拿手摸了一下微隆的小腹,她還沒來得及站穩就被人甩在了衣櫃上。後腦勺的疼痛,讓她悶哼了—聲。
4.2萬字8 18622 -
完結7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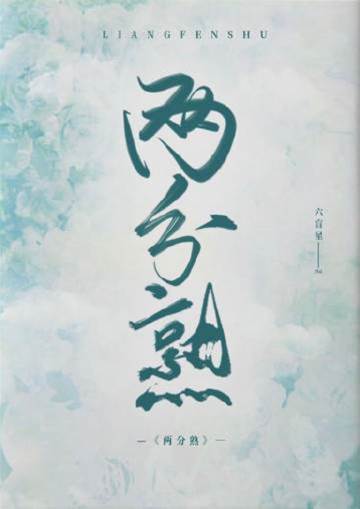
兩分熟
大學時,阮云喬一直覺得她和李硯只有兩分熟。學校里他是女粉萬千、拿獎無數的優秀學生,而她是風評奇差、天天跑劇組的浪蕩學渣。天差地別,毫無交集。那僅剩的兩分熟只在于——門一關、窗簾一拉,好學生像只惡犬要吞人的時候。…
25.3萬字8 6408 -
完結493 章
惡魔的寵愛
“以你的身材和技術,我認為隻值五毛錢,不過我沒零錢,不用找。”將一枚一塊的硬幣拍在床頭櫃上,喬錦挑釁地看著夜千塵。“好,很好!女人,很好!”夜千塵冷著臉,他夜千塵的第一次,竟然隻值五毛錢!再次見麵,他是高高在上的王,她是低到塵埃的花。一份價值兩億的契約,將她困在他身旁……
84.9萬字8 1497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