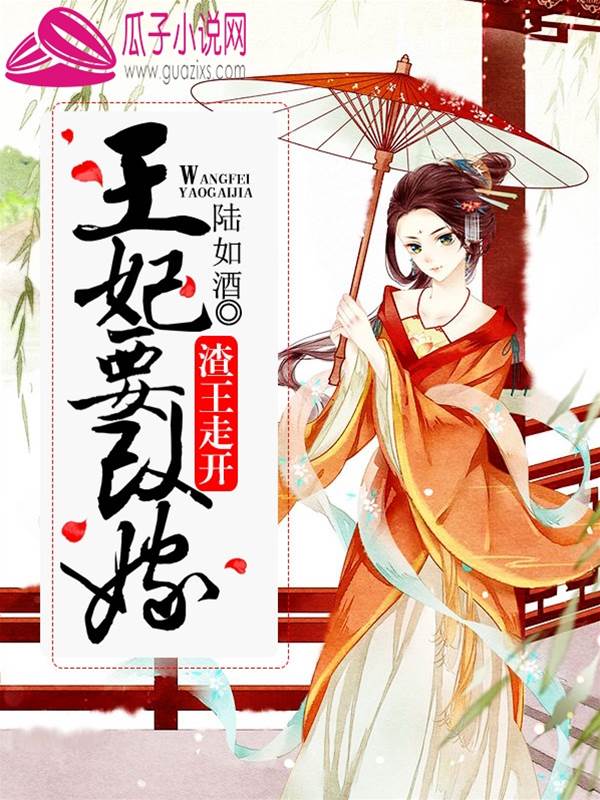《重生后成了權臣掌中珠》 第131章 畫眉
魏鸞覺得盛煜這兩日不大對勁。
倒沒像先前因周驪音而鬧別扭時那樣深夜不歸, 畢竟魏鸞懷著孕, 上回冒著夜里寒風去南朱閣找他,著實讓盛煜心疼了一把。打那之后,他但凡在府里,不管多晚都會回屋來睡,若戌時還被困書房,便會遣仆婦來送個消息, 讓魏鸞心安。
但他來屋里時, 卻頗盯。
對坐吃飯的時候, 魏鸞不經意間抬頭給他布菜,會恰好上盛煜落在臉頰的目;睡前坐著翻書時, 偶爾眼睛酸累了歇息, 會上盛煜泓邃的目, 若夜幕深濃,手里捧著的書卻只翻了兩三頁,顯然并未用心看書;便是連換梳妝,都能被他頗有興致地瞧著。
譬如此刻。
今日并無早朝,盛煜只需趕在辰時末前去衙署即可,不必急著出府。
朝初升, 灑滿庭院頭窗而。
魏鸞坐在妝臺前,任由抹春梳發。
的頭發保養得極好,上等綢緞似的,握在手里十分。澤養得黑亮,披散在肩時, 襯著姣白膩的,格外分明。眉眼尚未描畫,上也未涂口脂,發間耳畔更無珠釵裝飾,便是這樣素凈的臉,看著卻仍婉轉艷,愈有旖之態。
盛煜剛換好服,還沒戴冠帽,翹坐在旁邊圈椅里。
借著致銅鏡里的倒影,可以看到他在看。
不言不語,像是在賞玩人。
魏鸞以前從沒發現他還有這等興致。
遂拿指尖挑了口脂慢涂,道:“時辰已不算早,夫君還不出門嗎?聽說先前不朝臣進諫,怕夫君兼兩副重擔會忙不過來。若去衙署遲了,就不怕旁人將這揣測坐實?”
“無妨,晚點出門不遲。”盛煜淡聲。
Advertisement
魏鸞“唔”了聲,沒再管他,專心梳妝。
盛煜卻起走過來了,將手里端著的冠帽擱在妝臺上,修長的手指過來,狀若無意的撥弄珠盒里擺著的螺子黛,“這是畫眉用的?”
那只手慣于執筆握劍,裁斷生死,如今落在兒家梳妝的黛上,倒是新奇。
魏鸞含笑睇他,“夫君在別見過?”
故意咬重“別”二字,眼底不無揶揄,就差問是在哪位姑娘的繡閨妝臺了。
盛煜聽出揶揄,角微。
“玄鏡司門時,最先學的就是日用之。這些黛,哪個敷施妝好看我不清楚,但哪些胭脂黛里易摻毒,我卻一眼便知。像這種黛筆,若在毒里浸上足夠的時日,旁人瞧不出來,用久了卻能傷損,累及雙目,神不知鬼不覺。”
“咦!”魏鸞眼睫輕,“聽著怪嚇人的。”
盛煜逗得逞,指尖挑起螺黛比劃了下,“給你畫眉吧。”
“夫君會嗎?”
“試試。”盛煜淡聲。
魏鸞有點怕他畫毀了眉,要洗重來,不過難得這男人有閨中之興,也沒拒絕,只抹春先退開。盛煜遂拿腳尖勾個椅子坐著,稍加思索,抬手便畫。
的眉眼,他其實描摹過多遍。
在勾勒兩筆后便焚去的紙箋上,在他耐不住思念的深夜里,且魏鸞原就生了雙遠山含煙的秀眉,稍加潤便可。盛煜頭回上手,竟也畫得像模像樣,過后退開些許端詳,甚為滿意地頷首,低聲道:“很漂亮。在府里閑居,其實不必挽髻,披著好看。”
魏鸞笑著沒理他,只管攬鏡自照。
自打了曲園的夫人,就只敢在室里披散頭發,或是睡前拭,或是房事后地趴在盛煜上,由他擺弄挲。但凡出屋舍,總須挽髻。即便實在懶得梳,也會拿金環束著,免得仆婦看著不尊重。
Advertisement
盛煜藏春宮貪房事,當然覺得散發弱好看。
白日做夢的臭男人。
魏鸞心里輕哼,瞧著鏡中的眉,勉強湊合能看吧。也沒潑涼水,只道:“夫君倒是文全才,畫眉都能手到擒來。好了,時辰不早,快去衙署吧。”還要畫個漂亮的妝容去祖母那里呢。
盛煜屢屢被催,只好整冠出門。
繞過屏風出門檻,卻又忽然折回來,淡聲道:“你就沒什麼話同我說?”
魏鸞約莫猜得到他指什麼,卻抱著小火慢燉的心思,不太縱著他這病,便淡聲道:“有啊。夫君才剛加進祿,到衙署后可不能懶,早些置玩公事,晚間回來還能趕上吃飯。”說著話,還嫣然而笑。
“……”盛煜無言以對。
默然出了北朱閣,甩開長去衙署。
……
比起曲園里養胎的歲月安穩,朝堂上最近不甚太平。
臨近年關,各衙署忙著清掃羈押的差事,等著過年,誰知肅州西邊的白蘭國不安分,不時侵擾邊關,擄掠搶奪。肅州一帶由定國公鎮守,白蘭也是他手里的老對頭,先前奪回被占的城池時,鐵騎所向,曾令其聞風喪膽。
如今沒過幾年,卻又在邊疆滋事?
永穆帝瞧著定國公那幾封奏報,臉沉黑。
出京城往北,過了寬闊的隴州,便是條狹長的通道,自甘州起至肅州、沙州、庭州、安西,如走廊般綿延。比起南邊的山清水秀、溫富庶,這一帶多于塞外荒漠,不宜耕田農居。但這一帶對朝堂卻極為重要,因其不止能拒敵于隴州之外,還是商貿往來的要通道。
永穆帝父子養蓄銳、縱容章家,便是為收回這條通道。
數年前失地收復,重兵駐守,于走廊西側的白蘭國遭重創,早已俯首稱臣。
Advertisement
如今忽然滋事,恐怕是定國公生出異心,為保住手里的兵權,以戰養兵。畢竟白蘭雖曾俯首,到底民風彪悍,對肅州一帶的商道極為覬覦,若非朝廷重兵鎮守,怕是早就蠢蠢而。邊境廣袤,各主君皆有其職,為免再生,要對付白蘭,就只能用肅州都督麾下的兵。
而肅州的軍將……
章家百年基業,不止曾隨先帝征戰天下,當初也是鎮國公兄弟率兵收回失地,在北邊軍中威極高。先前永穆帝以周令淵的命為要挾,將庭州都督的權柄收回手里,換了心腹去鎮守,狠狠換了一番。
其中有些軍將是章孝恭的死忠部下,平白剪除師出無名,留在庭州又是個禍患,但凡攛掇出個兵變,邊塞重地,干系不小。永穆帝思來想去,便將那撥人調去了定國公麾下,一則對方甘與章氏為伍,能調得,免去麻煩;再則將這些刺頭盡數扔去肅州,回頭收拾起來,可一鍋端了。
謀劃里是如此,但須時日施展。
庭州的局勢尚未全然穩固,永穆帝沒打算太著急定國公,免得庭州肅州聯手生出□□。
如今白蘭生事,永穆帝亦不可能臨陣換將。
肅州都督的麾下多半是定國公的舊屬,如今又添了章孝恭的余孽,都是些刺頭,朝廷放誰過去都指揮不。那些三無不時的小擾,即使是定國公蓄意挑起來的,暫時也只能予定國公去解決。
永穆帝將這意思說與盛煜,問他如何看待。
盛煜的回答與皇帝的預料相近。
“先前太后在位,東宮未廢,庭州有些人還賊心不死,左右搖擺。章孝恭留下的麻煩,怕是得開春才能收拾盡,在此之前,不宜貿然用兵,免得邊塞生。定國公這是走投無路自掘墳墓,不過是想借白蘭牽制朝廷,茍延殘。秋后螞蚱而已,皇上不如放他多活一陣。”
Advertisement
“庭州那邊,開春即可?”
“最晚明年開春。”盛煜先前親自去庭州布置,且事關要,每每親自過問,十分篤定。
永穆帝頗滿意地頷首,“肅州的事若給你,如何置?”
“釜底薪。”盛煜淡聲。
這般打算,與永穆帝不謀而合。在皇位殫竭慮,萬鈞重的擔子在肩上,只能帝王咬牙扛著,將兩鬢都熬得斑白。如今盛煜漸棟梁,謀略手腕皆不遜能臣老將,永穆帝甚是欣,示意他繼續說。
盛煜遂肅容拱手。
“白蘭之所以為定國公所用,只是利益驅使。從奏報看,白蘭沒打算跟朝廷鬧得太僵,故只敢擾而不敢陳兵。等庭州安穩,皇上自可遣人出使白蘭,威與利兼而用之,據臣所知,那位國主也打算休養生息,定會休戈止戰。屆時皇上無需翻陳案舊賬,單憑通敵叛國一條,便可令定國公萬劫不復。既然師出有名,解決了外患,三路包抄,速戰速決即可。”
永穆帝聞言,忍不住笑了。
“朕也是這意思。既如此,這事開春了再議,如今讓戶部隨便撥些錢糧。折騰了整年,朕也該空歇歇。”他說著話,微微后仰,靠在椅背上。
只要不起邊患,三路大軍足以剿滅定國公在肅州的人馬。更何況,有隴州和庭州兩面夾擊,玄鏡司也可借機行事,挑起章氏舊屬,嘗試從里頭瓦解。
離兩代帝王苦心籌謀的事,只剩一箭之遙。
永穆帝闔眼,臉不知何時轉為平靜。
“肅州的商道是國之大計,往后不了要跟白蘭打道,開春后釜底薪的事,你與使臣一道去吧。使臣從朝中選派,你再尋個跟白蘭有過往的,從旁協助。”
朝堂與白蘭的往,除了雙方使臣,便是肅州的人馬。
——那邊開了互市,朝廷還會從白蘭買軍馬。
若要從肅州選人手……
盛煜想起個人,問道:“臣想帶魏知非前去,皇上意下如何?”
“他倒是可用之才,鄭王也曾夸過。”
這般贊許,自是答允了,盛煜領命,拱手告退而去。
……
出了麟德殿,外頭天朗氣清。
盛煜瞧著翹角飛檐,輕舒了口氣。
章孝溫既走到這地步,算是徹底將章氏當初從龍之功毀了個徹底。貪心不足,敗名裂,終是要自食惡果。屆時死敵既除……他忍不住看了眼玉霜殿的方向。
周令淵母子仍關在那里。
宮中爪牙盡除,曾得永穆帝忍辱負重的那個惡毒人,如今困于偏僻冷殿。為階下之囚,除了還有口飯吃,行連尋常農婦都不如。曾仗著軍權作威作福,等親眼看著百年基業毀于一旦,該是焚心挫骨之痛吧?
盛煜眸冷沉,拂袖離開。
先去了趟玄鏡司,再去中書那邊,誰知今日時相抱恙,未來衙署。偏巧有件事要定奪,須與中書令商議方可,盛煜既已任了中書侍郎之職,想著此事不宜拖延,且不知時相病如何,便得空時去了趟相府。
好在時相病得不重。
臘月里天冷風寒,各衙署忙著收尾,中書也不例外。時從道原就上了年紀,連日勞累,昨晚深夜回府時了風寒,今早便昏沉沉的沒能起。好在太醫及時去調理,兩副湯藥喝下去,神頭已好了些。
盛煜進去時,時相仰趟在榻上,背靠枕,腦袋上搭了浸的巾。
時虛白一閑居的白,正侍奉湯藥。
見他進屋,忙命人設座奉茶,待將湯藥喂完,自退出屋子,連同門扇也掩上。
剩下兩位中書的頭領議事。
等商議完畢,已是暮四合。
時虛白親自送盛煜出府。
冬日天晚,暮漠漠,府里的廚房已飄起炊煙。自打從鄧州回來后,兩個男人已許久不曾照面。便是在章太后的喪禮上,時虛白也以份低微自居,不曾到宮中面,更未去出殯送葬。如今并肩而行,一個玄威重,端穩冷,另一個白衫飄飄,似在世外。
那是迥然不同的氣度,各有千秋。
途徑時虛白的院子,盛煜忍不住瞥了眼。
他清晰記得,那座書房的高架上,擺滿了卷軸書畫,其中不知多幅有魏鸞的影子。時虛白早就過了弱冠之年,卻從未傳出婚娶的消息,在鄧州時,更是舍命相救——若當時沒有魏鸞在場,盛煜篤定時虛白不會蹚那渾水。
猜你喜歡
-
完結1450 章
替嫁棄妃覆天下
問女子的容顏能有多值錢?她是先帝親點的皇后,卻在顏容半毀時被一紙圣旨從后變妃。一旨雙嫁,絕色的妹妹代她入宮為后,而她遠嫁給那少年封王,權傾朝野,冷酷殘暴的雪親王……新婚夜,他說她的容顏只配呆在馬廄里,雖有王妃之名卻只能任人奚落…他中毒命在旦夕,她不顧一切救他,只為讓自己活有尊嚴……以妻子這名,行幕僚之實她伴......類小說,情節引人入勝,非常推薦。
353.4萬字8 121976 -
完結354 章
穿成侯府通房丫鬟后,我擺爛了
秋錦穿越了,穿成被送去當通房,而被拒絕打了回來的小丫鬟。 因長相貌美,算卦老先生說她命中帶福,老夫人將秋錦送給混世魔王嫡長孫小郎君當通房,希望旺旺嫡長孫
53.7萬字8 11161 -
完結301 章

昭鸞
虞昭是聞名于世的東楚第一美人,縱使兩國交戰數年,依舊美名遠播。她本有一樁人人稱羨的美滿姻緣,卻在大婚前被至親出賣,奉旨和親敵國,為宗族換來潑天榮華富貴。初聞消息時,虞昭慘白了面容,她要嫁的人是敵國太子蕭胤。對方龍章鳳姿、戰功赫赫,此前大敗東楚之戰便是由他領兵。新婚當晚,蕭胤以朝務忙碌為由,宿在書房一夜不見人影。虞昭等了許久便倦了,拉過赤錦喜被蓋在了身上。翌日,蕭胤終于見到虞昭的真容。他發覺自己在新婚夜丟下的太子妃,此刻一副睡飽了的模樣,不禁眼底微深。后來,蕭胤將她堵在墻角,試圖履行夫妻“義務”。他望見虞昭哭紅的眼,以及那紅艷的菱唇,既不忍心傷她,唯有放軟姿態,嗓音暗啞道:“孤哪兒不如你那個未婚夫了,你說說。”
46.2萬字8 12432 -
連載5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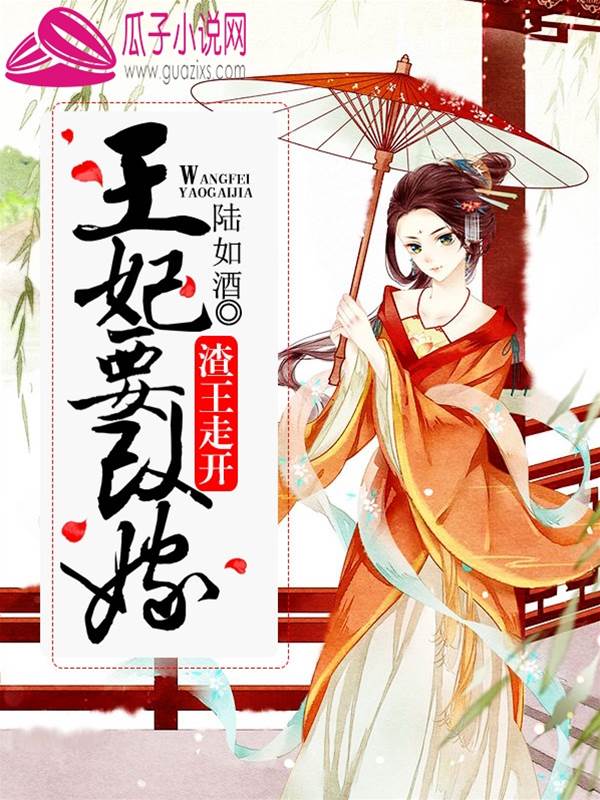
渣王走開:王妃要改嫁蘇妙妗季承翊
蘇妙,世界著名女總裁,好不容易擠出時間度個假,卻遭遇遊輪失事,一朝清醒成為了睿王府不受寵的傻王妃,頭破血流昏倒在地都沒有人管。世人皆知,相府嫡長女蘇妙妗,懦弱狹隘,除了一張臉,簡直是個毫無實處的廢物!蘇妙妗笑了:老娘天下最美!我有顏值我人性!“王妃,王爺今晚又宿在側妃那裏了!”“哦。”某人頭也不抬,清點著自己的小金庫。“王妃,您的庶妹聲稱懷了王爺的骨肉!”“知道了。”某人吹了吹新做的指甲,麵不改色。“王妃,王爺今晚宣您,已經往這邊過來啦!”“什麼!”某人大驚失色:“快,為我梳妝打扮,畫的越醜越好……”某王爺:……
99.7萬字8 1343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