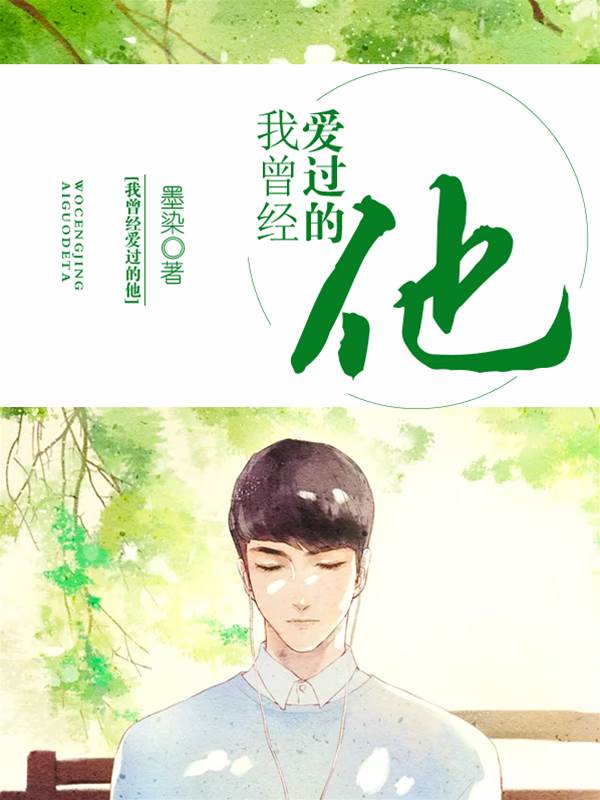《他站在時光深處》 第66章 他站在時光深處65
電話被掛斷, 應老爺子轉看向坐在他下首, 和他僅隔著一臂距離的溫景然:“都聽見了?”
年邁的聲音, 如寺廟鐘樓里的鐘聲, 聲厚重。
他的手邊,剛開始沸騰的水,在明茶壺里咕嚕咕嚕地冒著泡, 把整個夜渲染得格外匆忙。
溫景然提起茶壺,用熱水沖淋茶。
他這一手泡茶的技藝,也是師從應老爺子,從溫到倒茶, 無一步驟不。
他修長的手指在暖的燈下, 似泛著潤澤的瓷, 執杯的手指骨節彎曲的曲線流暢,像一件上好的藝品。
他取過青釉的茶壺置茶葉,低垂著的眉眼眨了眨,開口時, 聲線沙啞, 幾不句:“……聽見了。”
不是很清晰, 卻實實在在聽清楚了。
事還要從前幾天說起。
自從應老爺子有了給自家孫和得意學生拉郎配的念頭,就無比關注應如約的生活。
前段時間, 老爺子頻繁地從應如約的里聽到“沈長歌”這個名字時, 已預不好。
這種憂在有一次看到沈長歌把如約送回家時瞬間達到了制高點。
老爺子人老了沒耐心,那幾日,尋了個空就給溫景然去了個電話, 借著了解沈長歌的工作況以及為人世旁敲側擊地提醒溫景然——這個混小子對如約可不懷好意啊!
溫景然之所以能讓應老爺子如此喜歡,除了專業技能過關和商高低的關系也是不可分。
尤其應老爺子生怕他聽不懂自己的暗示,順手造的理由百出。什麼“那個沈醫生面相看著不善我很擔心”“神外科手強度這麼大腎都要憋壞了”等等,就沒有正經的……
應老爺子在應如約面前十足嚴肅刻板的爺爺形象,可在溫景然那另當別論。
Advertisement
應老爺子老來親自手漸,通常把機會都讓給學生,他從旁指導。
一臺手下來,說風涼話的時間比一本正經的時間多的多,通常有他在,手室里的畫風都是“小謝剛才把東西掉病人里面還是外面了?快幫他找找”“還不止?也行吧,你速度快點我覺得病人快撐不住了”或者“手上活這麼慢,磨蹭什麼呢?忙著往病人肋骨上刻到此一游啊”……
是以,溫景然回應的態度也很放松:“據我所知,如約應該和那位沈醫生只是朋友關系。”
老爺子說了半天,豈甘心被溫景然不痛不的一句話打發了,直言道:“說了半天,我就想問問你對如約有沒有別的心思。如果沒有,我就把這位沈醫生列考察名單,沒你什麼事了。”
老爺子對溫景然的拿很準確,一句話,溫景然悉數招認。
雖沒有全盤托出,但話里話外意思明確——這師生關系可以進一步升華加深下了。
這段私底下的會談因為不見,兩人皆默契地統一態度,只當沒有通過這次電話。
不料,還沒幾天……
聽溫景然說了大概,應老爺子吹拂著茶面的熱氣,一雙眼沉郁得眼瞳漆黑,辨不清喜怒:“這丫頭心結重,看著跟沒事人一樣,心卻薄得像紙片。不在一起也對,這子和誰都不能在一起。”
應老爺子對太過疏忽如約時的心理健康其實抱有很執念的歉疚。
“到現在也沒有去正視你是醫生的份,說到底,怕父母的婚姻會在上再重演。當這是過家家呢,還期待你會和別的醫生不一樣。做醫生這一行的,這一生都在做研究,治病人,一個電話就能去急診管你接電話之前是在哄朋友還是鬧離婚呢,必須得到。”
Advertisement
老爺子說著說著就真的怒起來:“我當年和結婚,第一個孩子流產時我外派學習,三個月后才回的家。生爸時,鄰市地震,說走就走,還沒聽到孩子哭,去了半個多月回來。要都這種子,也就沒什麼事了,這脾氣啊,我看都是像了那媽,當年也是……”
溫景然盯著青釉杯底那細碎的茶末,輕輕地晃了晃,再抬起眸時,雙眼沉靜地著他,輕聲打斷:“老師。”
應老爺子回視,鼻息重,猶有怒氣。
溫景然此時卻忍不住發笑。
“前”友的爺爺站在他這一邊,也不知他是不是這第一人。
越想越覺得逗趣,他到底沒忍住,只能借著喝茶的作遮掩住角的笑意。明明是苦到舌尖都發直的安山茶,他卻品出了一回甘。
他垂眸看著被搖散的茶末,再抬起頭時,凝視著燈下,正被時慢慢忽略的老人,語氣平靜道:“是我的錯,明知的癥結,卻沒能理。”
老爺子方才那些看著怒火中燒的話,怎麼可能是真的生如約的氣,他不過是擺出個姿態,在等溫景然表態,也是在替如約說話。
雖然晦,但這番良苦用心,溫景然如何會看不出來?
老爺子嘆了口氣,緒平靜下來,抿了口仍帶著燙意的安山,問他:“那你打算怎麼做?”
“先什麼也不做。”溫景然執起茶壺,往老爺子的茶盞中滿到八分,手腕一提,把茶壺放回桌墊上,低聲道:“現在想想,這種結果也未嘗不是好事。”
老爺子其實有些懷疑……
手臺上,他那些頭學生討論怎麼追生時,他這得意門生可從來不說話啊……這能有什麼好主意?
Advertisement
——
隔日。
如約掛了號,在診室外的休息椅上排隊候診。
溫景然是S市有名的胃腸外科醫生,又被列在專家欄里,他每次出門診的看診率都高得驚人。
應如約聽小邱念叨過,他的看診率是魏醫生的一倍。
今天親眼所見,才知道他連日常看門診都能這麼忙。
號的護士認識如約,從手里接過病歷單時驚訝地睜圓了眼,有些驚喜:“應醫生,你今天不上班啊?”
“請假了。”應如約攙著外婆,對笑了笑:“帶外婆來看診。”
護士“哦哦”了兩聲,示意們進去。
溫景然還在給上一位病人寫醫囑,余及,轉頭對向欣和外婆點頭示意,落筆寫下最后一個字,合上病歷單遞給病人,叮囑“注意飲食”后,站起,親自扶著外婆坐在了椅子上。
他知老太太的病,但昨天知道病的渠道僅憑一個電話。
直到此刻,看到了紙質的病理結果,他仔細地看過每一項指標以及首診醫生的醫囑,確認后,目在如約上一掃而過,看向向欣:“是T2N1MO進展期,腫瘤浸潤面積較小,幸好發現及時。先安排住院,的手方案等常規檢查做完后我再跟你們詳細說明下。”
向欣點頭笑道:“那好,麻煩你了。”
溫景然開好住院單夾在病歷單里遞給應如約,示意去護士站辦理院。
從進診室到現在,這還是溫景然唯一一次和眼神的流。
——
外婆順利的院等手排期,加上又有向欣全天照顧,一時有些無用武之地。隔日就回醫院,正常上班。
小邱昨天下班后特意和沈靈芝一起來病房看了老太太,早早得知如約今天會上班的消息,一大早就在科室里等著給送蘋果。
Advertisement
“我們醫院最近太衰了,我昨天剛給靈芝姐也送了蘋果,你趕收下,咱們都平平安安的。”話多,一刻不說話都忍不住,從抱怨應如約這兩天不在沒人可聊天到薛曉這件事的最新匯報,最后聊到溫景然:“我聽李護士說,昨晚溫醫生大半夜來了醫院,挨個看了病人的況直接在值班室睡下了。”
應如約捧著蘋果的手一僵,下意識地留意:“在值班室睡下的?”
“是啊,你說溫醫生又不值班,也沒手的……還這麼敬業。”小邱托腮,嘀咕著:“長得帥又有錢還這麼努力……”
沈靈芝笑了聲,回頭看了眼懷春的小邱,毫不留地打碎了的心事:“你就別想了,溫醫生心里有人了。”
小邱懶洋洋地瞥了一眼,意料之外地沒有像沈靈芝預想的那樣激到炸裂,格外平靜地點點頭:“我猜到了,Wuli溫醫生最近緒這麼晴不定的,真的值班室也就昨晚才住了一回,肯定是外面有人了。”
換了只手繼續托腮,眼神往應如約上斜了眼:“我還覺得那個人就是我邊的人……”
應如約被那幽怨的眼神一掃,渾不自在,心里更是猶如梗了一刺一般,一想起那個人就扎得疼。
拿著蘋果,揮揮手,轉就溜:“我先去手室準備手。”
——
下午臨近下班的點,不知道甄真真從哪知道如約外婆在S大附屬醫院住院的事,拎了一大袋的水果來探病。
應如約接到向欣電話時,懵了一會,正好已經沒事就在等下班,跟沈靈芝說了一聲就急匆匆趕去普外的病區。
甄真真一見來就數落:“這麼大事你都不告訴我,要不是溫……”
話說到這,戛然而止。
險些說,甄真真滿臉懊惱,摟著向欣的小臂撒:“阿姨你看如約,從小到大都是這個臭脾氣,有什麼事永遠自己埋心里。不錘一悶,屁都不放一個。”
甄真真和應如約朋友的時候,向欣還沒和應爸爸離婚,只不過那時候關系也不是很好,但對這個熱活潑的孩倒是印象很深。
“打小悶慣了。”向欣笑看了眼如約:“你可別跟見怪。”
甄真真不過是為了轉移話題,當下順著臺階就下了:“怎麼會見怪,我兩好得都快長一起了。”
嬉笑著,又是打趣又是講笑話的,把兩位長輩逗得合不攏。每每這個時候,就得意地朝如約拋去一個眼神,別提多驕傲了。
向欣不讓如約陪護,催著下班和甄真真去吃頓好的。
等兩人一離開,外婆看了眼正替倒茶的向欣,嘆了口氣:“如約要是有真真那孩子活得那麼明白就好了。”
向欣沒接話,拎著水瓶往外走:“我去打水。”
走出住院部,甄真真的腳步一頓,就停在臺階最上方不走了。
應如約下了臺階才發覺沒跟上:“怎麼了?”
甄真真臉上笑意淡去不,心里有些別扭,慢吞吞地走下臺階后,噘不滿道:“你說月底有事跟我說的,今天就是這個月的最后一天了,如果我不來,你是不是就忘記這件事了?”
應如約被一提才想起有這麼一回事,扶額,有些抱歉:“對不起,最近事太多太集……”
“原諒你。”甄真真挽過的手:“你想跟我說什麼呀?你外婆的事?”
“不是。”應如約停下來:“我那時候想告訴你我和溫景然在一起了。”頓了頓,趕在甄真真大之前,及時補上一句:“可是現在大概要跟你說,我們分開了。”
幾秒經歷人生起落的,震驚得抓住自己的短發,那用力程度恨不得把揪下幾縷來。
暴躁地在原地來回走了兩圈,等停下來時,一雙眼直勾勾地瞪住:“不管,你去追回來。”
猜你喜歡
-
完結1058 章
陆少无心恋荒唐
眾所周知,陸彥廷是江城一眾名媛心中的如意郎君,有錢有顏。為了嫁給陸彥廷,藍溪無所不用其極——設計偶遇、給他當秘書,甚至不惜一切給自己下藥。一夜縱情後,他將她抵在酒店的床鋪裡,咬牙:“就這麼想做陸太太?”她嫵媚地笑:“昨天晚上我們配合得很好,不是嗎?”陸彥廷娶了聲名狼藉的藍溪,一時間成了江城最大的新聞。婚後,他任由她利用自己的人脈資源奪回一切家產。人人都說,陸彥廷是被藍溪下了蠱。成功奪回家產的那天,藍溪看到他和前女友糾纏在雨中。她笑得體貼無比:“抱歉,陸太太的位置坐了這麼久,是時候該還給顧小姐了,我們離婚吧。”“你想得美。”他將她拽回到衣帽間,在墻麵鏡前狠狠折磨她。事後,他捏著她的下巴讓她看向鏡子裡的旖旎場景,“你的身體離得開我?嗯?”為了馴服她,他不惜將她囚禁在臥室裡,夜夜笙歌。直到那一刻,藍溪才發現,這個男人根本就是個披著衣冠的禽獸。
354.5萬字8 15561 -
完結19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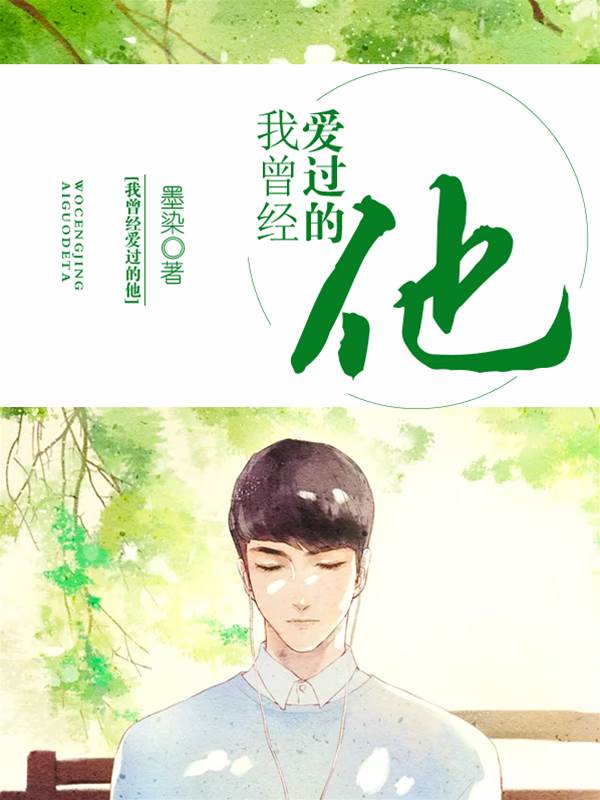
我曾經愛過的他
我為了躲避相親從飯局上溜走,以為可以躲過一劫,誰知竟然終究還是遇上我那所謂的未婚夫!可笑的是,所有人都知道真相,卻隻有我一個人被蒙在鼓裏。新婚之日我才發現他就是我的丈夫,被欺騙的感覺讓我痛苦,他卻說會永遠愛我......
33.5萬字8 1002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