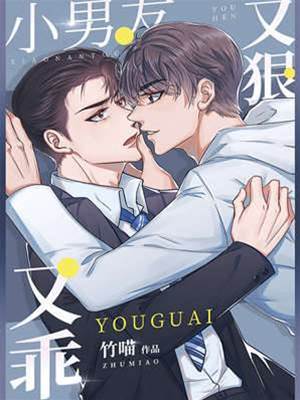《沖喜[重生]》 70
殷紅葉也曾暗中艷羨。
只是葉知禮已經娶妻,家里絕不可能讓給人做妾,而也不甘與人分一個男人,方才將年的心事封存在了心底。
后來王氏難產去世,只留下一個子。葉知禮續弦的消息傳出來,而家里又正在給看向合適的夫婿,才又了心思。
只是家里都顧忌葉知禮已經有了嫡長子而不同意,說再嫁過去,日后有了孩子,也得被一頭。
不甘心就此放棄,尋了國公府遣散的老仆打聽,方才打聽到了一些——那尋到的老仆告訴,老爺并不喜歡大爺,大爺出生后就只有個娘在照料。那老仆最后還附帶告訴了一個消息,說府里的老人私底下在傳大爺并不是已故的夫人所生,倒像是老爺養的外室所生。
只是那老仆也只是聽伺候的下人所說,并沒有什麼真憑實據。一番追問,也沒問出那外室況,只知道那外室和夫人先后有孕,以及外室最后拋下孩子,一走了之,再無蹤影。
老仆的話破綻百出,連自洽都做不到。但終于如愿嫁國公府后,卻在日積月累的相中,逐漸印證出了一些真相。
比如葉知禮對外與王氏琴瑟和鳴,但實則他對王氏并無太深的;再比如,葉知禮的書房里,藏著另一個人燒了一半的畫像。那剩下半張畫上,人容貌明艷,十分麗。
而葉云亭,不肖王氏,也不似葉知禮,卻唯獨與那畫上的人,像了五六分。
這些年自蛛馬跡中發現了諸多端倪,也越發篤定葉云亭便是那外室所生。葉知禮或許曾十分喜那外室,但不知什麼原因,兩人決裂了,那外室了無蹤影,只留下了一個出生不久孩子。又恰逢王氏難產,葉知禮便將這見不得的孩子,認在了故去的王氏名下。
Advertisement
剛發現這些事時,曾想去質問葉知禮,但沖過后,又冷靜下來。
那外室從未聽人提起過,葉知禮將人藏在國公府里,必定是不想為人知,若貿然去問,恐怕只是平白惹葉知禮不喜。況且知曉葉知禮并不是真心喜王氏,只覺高興。至于那個外室……葉知禮連他們之間的孩子都如此冷待,想必是將人恨到了骨子里。
是以這麼多年,只當做一無所知,從未破這層窗戶紙。
但這前提是葉云亭的存在不會威脅到葉妄的地位……殷紅葉垂眸,手指攥了帕子,勉強笑了笑:“哪有什麼是理所應當的?這大公子都嫁出去了,怎麼算也該是妄兒繼承才對。”
葉知禮看了一眼,角若有似無地勾了勾,嘆息道:“但他若非要,我也沒有辦法。”
說完,似安地拍了拍殷紅葉的手。
殷紅葉垂著眼,神不定。
***
葉云亭回了王府,卻發現李歧不在府中。正要去尋人問一問他的行蹤,卻不防越長鉤自屋頂上跳下來,落在了他側:“回來了?先生有事尋你說。”
——這幾日常裕安與越長鉤都在王府中小住。
聽說先生尋他,葉云亭腳步轉了個方向:“先生尋我?何事?”
越長鉤雙手抱懷,上沾了風雪:“我們要離開上京了。”
一聽他這話,葉云亭便明白了他的為未盡之語。
兩人進了客院,就見客房門窗敞開,屋,常裕安坐在一方小幾前,正在煮酒。
見兩人過來,便招了招手。
“先生。”葉云亭走過去,在他對面坐下。
“這些日子,你可想清楚了?”常裕安給他倒了一杯酒。
Advertisement
剛煮好的酒,散發著暖融的酒香。葉云亭端起酒杯,啜飲一口,暖融融的過頭,化了滾燙的辣。
他卻仿佛一無所覺,又一口將剩下的酒喝完。
常裕安觀他面:“你已經有了決斷。”
他頓了頓,還是忍不住勸說道:“我在上京逗留這些日子,上京暗流涌,朝堂不穩。不用多久,必生象。”
葉云亭垂下眸,神滿含歉意:“所以我才要留下來。”
朝堂暗流涌,幾方勢力博弈。李歧在局中,隨時都面臨危險,他怎麼能放得下他一走了之?
況且,他答應過他……會好好考慮。
第51章 沖喜第51天 都怪你
這句話說出口, 葉云亭先是怔然。
他以為自己多會糾結猶豫一番,可口而出的話,卻快得讓他措手不及。他一直以為自己還沒有最終做下決定。但其實在他不知道的時候, 他心中早已經有了決斷。只是他一直自欺欺人不愿意承認罷了。
他畏懼從未經歷的過,于是將自己包裹起來,止步不前。
但實際上他的心早就有了落點, 李歧之于他,不再只是同舟共濟的盟友。他的一舉一, 有意無意地牽著他的緒,不論他承不承認,這都是事實。
葉云亭微微抿了,一直混沌的思緒在這一瞬間變得通明晰。他穿過重重膽怯與猶疑,看到了藏在迷霧之后的真心。
——他放不下李歧, 或許也可以說, 他心悅他。
葉云亭笑了一下, 不知怎麼想起了李歧厚著臉皮歪纏的樣子。若是他知道自己的心思,恐怕會更加得寸進尺。
常裕安見他表變換,先是怔楞, 接著便是了然徹,到底嘆了一口氣, 知道自己是勸不了。
Advertisement
葉云亭是他看著長大的孩子, 他雖然脾溫和, 極與人起爭執,但實則是個很有主意的人。他認定的事,無可更改。
他索不再做無謂的勸說,遲疑一番后,才緩緩道:“你既然已經有了決斷, 我便不再相勸。”他自腰間出個不起眼的木牌給葉云亭:“我與長鉤這兩年都在南越落腳,你若是想尋我們,便來南越都城,帶上這牌子去月酒樓報我的名字即可。”
葉云亭接過,就見這牌子上沒有任何紋飾,只正中一個古樸的纂書“鳶”字。
他收起木牌,鄭重應允:“若有機會,必會去南越看先生與師兄。”又頓了頓,笑道:“若是以后北昭安定,先生與師兄也可回北昭看看我。”
南越雖暫時未與北昭起沖突,但以他如今的份,怕是不便明正大地去南越。
常裕安顯然也明白他的顧慮,點頭應下,道:“放心吧,我們有機會會回來。”
師徒三人喝了一場酒,權做送別。
等李歧歸來時,就見葉云亭裹著披風坐在廊下的人靠上,他眼神迷迷蒙蒙的,臉上有些紅。
“怎麼坐在這里?”李歧走近,先聞到了一酒香。他皺了皺眉,替他攏了攏披風兜帽,又用手背試了試他的臉頰,有些涼:“這麼忽然喝這麼多酒?”
自知酒量不好,葉云亭平日里很會喝酒。
“葉妄走了,先生和師兄也走了。”葉云亭拍開他的手,瞇起眼看著遠,似在喃喃自語,又似在對著李歧說:“他們都走了,我沒走。”
想起那沒來及去看的壯麗河山,他心里涌起一氣,仰頭瞪著李歧,說:“都怪你。”
Advertisement
若不是李歧一次又一次地歪纏,他怎麼會舍不得離開,留在了這他最想離開的上京城里。他憤憤瞪著李歧,眼神像看一個書生的妖,又重復了一遍:“都怪你。”
“?”
李歧暗暗嘶了一口氣,心想怎麼喝醉了竟如此不講道理?
但葉云亭一張雪白的臉泛著紅,眼睛霧氣朦朧,仰頭著他說“都怪你”時,仿佛他當真做了什麼滔天的錯事。
李歧嘖了一聲,心就了。只能順著他,溫聲哄:“是,都怪我,我錯了。”
葉云亭看著他,眼睛一眨一眨,半晌后了鼻子,著遠,輕聲說:“罷了,不怪你,是我自己愿意的。”
李歧心里一跳,目灼灼地追問:“愿意什麼?”
但是葉云亭卻不肯開口了。
他看了一會兒紛紛揚揚的雪景,就開始說困了,起搖搖晃晃地要回屋睡覺。
猜你喜歡
-
連載9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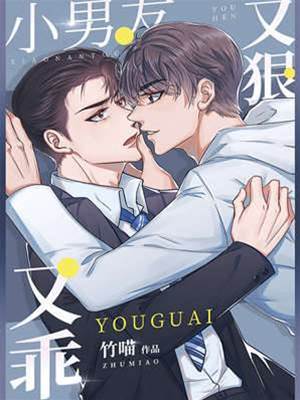
小男友又狠又乖
江別故第一次見到容錯,他坐在車裡,容錯在車外的垃圾桶旁邊翻找,十一月的天氣,那孩子腳上還是一雙破舊的涼鞋,單衣單褲,讓人看著心疼。 江別故給了他幾張紙幣,告訴他要好好上學,容錯似乎說了什麼,江別故沒有聽到,他是個聾子,心情不佳也懶得去看脣語。 第二次見到容錯是在流浪動物救助站,江別故本來想去領養一隻狗,卻看到了正在喂養流浪狗的容錯。 他看著自己,眼睛亮亮的,比那些等待被領養的流浪狗的眼神還要有所期待。 江別故問他:“這麼看著我,是想跟我走嗎?” “可以嗎?”容錯問的小心翼翼。 江別故這次看清了他的話,笑了下,覺得養個小孩兒可能要比養條狗更能排解寂寞,於是當真將他領了回去。 * 後來,人人都知道江別故的身邊有了個狼崽子,誰的話都不聽,什麼人也不認,眼裡心裡都只有一個江別故。 欺負他或許沒事兒,但誰要是說江別故一句不好,狼崽子都是會衝上去咬人的。 再後來,狼崽子有了心事,仗著江別故聽不到,在他看不見的地方悄悄說了很多心裡話,左右不過一句‘我喜歡你’。 後來的後來,在容錯又一次說出這句話的時候,江別故終於沒忍住嘆出一口氣: “我聽到了。” 聽力障礙但卻很有錢的溫文爾
56.5萬字8 6649 -
連載136 章
壯漢將軍生娃記
忠勇侯府的少將軍楊延亭把自己未婚夫婿給打了,還拐回家一個小倌兒。 不想這小倌兒堅持自己只是個陪有錢少爺玩的清白秀才。 後來沒想到兩人竟然被湊在了一塊,要當夫妻。 都說哥兒生子難,偏偏這將軍身體好,生了一個又一個! 設定:將軍是個膚色健康的哥兒,高大健壯,但是因為是哥兒又會有些不一樣的地方,比如寬肩腰細屁股大,再比如有個發情期,反正各種設定都加一點。 秀才不瘦弱了,俊朗一些的,會一些武功,是魂穿過去的。 孕期漲乳,生子產奶,後面流水,只一個穴兒。 肉文,俗爛劇情,1V1,雙潔。
32.9萬字8 16427 -
完結56 章
我就想離個婚[重生]
重生前,葉緋兢兢業業、勤勤懇懇,眼裡只有工作。 重生後,葉緋決定放飛自我。 去他媽的工作!去他媽的合約婚姻! 他再也不要過這種無1無靠,四海飄0的日子了! 離婚,必須離婚! 茶幾上,葉緋甩出一份離婚協議,美滋滋地掰著指頭數—— “最近有個小鮮肉,屁股翹腰窩深,一看就持久。” “還有一個鼻梁挺手指長,一定會玩花樣。” “哪個比較好呢?” 晏梟撩起眼皮,面無表情地看了他一眼。 後來, 葉緋腰酸腿軟的癱在床上,悔不當初地吐出一口煙圈:“失算了。” 呆呆子攻X騷浪受
16.5萬字8 636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