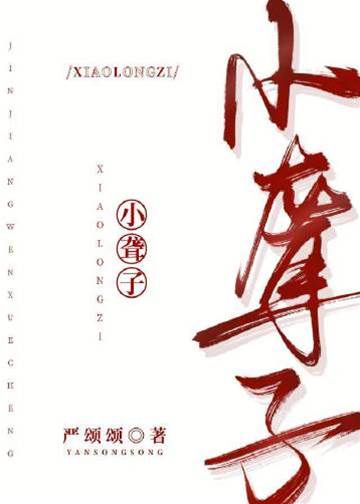《沖喜[重生]》 142
百姓們聽說不僅打了勝仗,西煌十萬人馬還全滅了,雖然他們尚且不懂西煌十萬兵馬全滅所代表的的意義,但卻無法阻止他們激喜悅。哪里還顧上房屋不房屋的,有年紀大些的,想起曾經在西煌馬蹄下的苦,都抹起眼淚來。
在姜述與朱烈的安排下,城外的百姓們分批有序地回了城中。
待百姓都離開了,李歧才下馬,大步走向祭臺。
那里,葉云亭與老王妃靜靜站著。
“母親。”李歧先向老王妃行了禮,接著目便看向葉云亭,兩人目無聲匯。
“我乏的厲害,就先回去休息了。”老王妃瞧著兩人的神,眼神慈,沒再夾在中間妨礙夫夫兩個,倚秋攙著自己,上了后頭的馬車。
李歧深深凝著干裂的青年,手掌上他的側臉,低聲道:“辛苦你了,累不累?”
“累。”葉云亭沒有逞強,擔憂一夜,他眼下影濃重,嗓音也有些干。
“我帶你回去。”李歧說完,掐著他的腰,將他抱上了馬。
葉云亭雖然瘦削,卻量高挑,并不算輕。但在他手上,卻好像輕飄飄沒什麼分量。
“你休息一會兒。”李歧讓他側坐馬上,將人按在自己口,用披風將他整個裹住。
眼前黑下來,葉云亭被披風整個罩住。單獨隔出來的狹小空間里,除了輕輕的呼吸聲,便只有李歧腔的跳聲。
一下一下,平穩而有力。
就好像他這個人一樣,如山岳巍峨,沉穩可靠,堅不可摧。
葉云亭深吸一口氣,鼻間盡是獨屬于他的氣息,他眼皮往下垂著,就在這樣的令人安心的氣息里,疲憊地睡著了。
Advertisement
李歧控制著速度,帶著他慢慢往回走。
落在后頭的朱烈瞧瞧孤零零落下的季廉,唉了一聲,一副“真可憐不過不要傷心習慣就好”的表對他說:“看來那馬車是給你準備了。”
——他們出城時帶了兩輛馬車,一輛是給老王妃的,還有一輛他原本以為是給王妃的,但現在看來,是給王妃的小書準備的。
季廉撓了撓頭,“哦”了一聲,收回目,趕上了馬車。
馬車速度可比李歧要快得多,從他邊經過時,季廉趴在車窗上探頭往外看,瞧見李歧垂著眼,神十分溫。
他放下簾子坐回去,心想也不枉爺昨天費了這麼大的勁兒。
李歧帶著人回都督府后院時,就見穿著甲胄的葉妄興沖沖的跑來,他臉上又添了兩道傷口,左臂用繃帶吊在前,走路還有點一瘸一拐,傷不,但都不算重。一張臟兮兮的臉上喜氣洋洋。
到了近前,他張口要人,卻被李歧一個作止住了。
“他睡著了,有什麼事,晚些再說。”
葉妄低低“哦”了一聲,把中的激興憋了回去,看著李歧將人抱進了屋里。
“到了嗎?”葉云亭睡得不沉,李歧將他放在床上時,他迷迷糊糊地睜開眼睛,咕噥著問了一句,手卻還抓著李歧的角沒放。
真粘人。
李歧瞧著那只抓著自己角的手如此想到。
“嗯,你繼續睡。我守著你。”
似乎這話他覺得安心,葉云亭含糊不清地“唔”了一聲,又睡了過去。
他太累了。
神繃了一夜,在見到了李歧后,便驟然松懈下來。
Advertisement
李歧就坐在榻邊守著他,等他睡了之后,方才掀起他的,檢查膝蓋上的傷勢。接人的路上,他聽姜述說,葉云亭為了當好表率,以示誠心,在祭臺前跪了整整一夜。
子卷上去,出膝蓋上目驚心的淤青來,再往下,整條小都有些浮腫,應當是跪久了所致。
葉云亭冷白,黑紫的淤青在他上就格外可怖,李歧輕輕了一下,就聽睡的人輕哼了一聲,他頓時不敢再,輕地將放了下來。
算了,先讓他睡個好覺。
*
等葉云亭一覺醒來,天已近黃昏。
李歧就坐在榻邊,側對著他正在看文書,修長的眉微微蹙,似乎不太愉快,但在察覺他的目后,轉過來,那不愉便盡數化作了溫。
“睡醒了?是想先沐浴還是先用飯?”
葉云亭定定看了他幾眼,準備起時,才發現自己手里還攥著他的角。他恍然明白了李歧為什麼坐在榻邊看文書。
“先……沐浴。”在外城吹了一整宿的寒風,如今他只想泡在熱水,將那種浸骨髓的寒意驅散。
“我讓人備好了熱水。”李歧聞言將他打橫抱起來,往浴房的方向走。
葉云亭一驚,雙臂卻下意識環住了他的脖頸,耳尖燒紅:“我可以自己去。”
“你還能走?”
聽他這麼一說,葉云亭才察覺了上傳來的脹痛,確實有些難,但也不至于不能走。
但……被抱去似乎也沒什麼。
他抿了抿,沒在出聲,任由李歧將他抱去了浴房。
李歧知道他的習慣,早就讓下人備好了熱水,抱著人過去,替他寬了裳,便將人放在浴桶里:“你泡一會兒,要加水就同我說。”
Advertisement
他守在不遠,目灼灼看著浴桶里的人,全然不覺得自己搶了下人加熱水的活兒有什麼不對。
葉云亭下浸水中,臉頰被水汽熏紅:“哦。”
“哦”完之后,發現他一甲未除,顯然是守著他還沒來及沐浴更,又猶豫道:“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
沒料到他說出這種勾人的話,李歧眼神掃過清澈的水面,瞧見水下約的玉,磨了磨后槽牙:“你傷了,今日暫且放過你。”說完似覺得不忿,又補充道:“日后再補回來。”
葉云亭:“……哦。”
他不說話了,他只是想單純讓李歧也一起泡個澡,但這人顯然腦子里都裝著不正經的事。
換了三桶熱水,泡了兩刻多鐘,葉云亭才覺得自己重新活了過來。
李歧用寬大的布巾給他干,再換上干凈的中,然后將他又抱回了臥房,塞進被窩里。
臥房的桌子上多了兩個瓷瓶,是李歧先前人送來的,拿過瓷瓶,坐在榻邊,讓他將出來藥:“上的淤青要開,這樣好得快些。會有些疼。”
“嗯,我能得住。”葉云亭整個人陷進的被褥里,只出半張臉來看著他,一條修長筆直的則擱在李歧上,卷起,腳趾有害地蜷著。
李歧沒忍住了他的圓潤腳趾頭,換來一個輕蹬,方才低笑一聲,將藥酒倒在掌心捂熱:“疼別忍著,我……盡量輕些。”
說完掌上控制著力道,小心替他將膝蓋上的淤青開。
待兩只都上完藥,李歧又替他按了一會兒小以及腳底的位,通經活絡,方才凈了手,問:“了麼?我讓人擺飯?”
Advertisement
“有點。”葉云亭誠實地點了點頭。
他坐在床上,只穿著寬松的中,發髻散開,隨意披散在肩頭,眉目秾麗,整個人瞧著慵懶又,看向他的眼神繾綣依賴。
李歧被看得心頭發,恨不得將人抱在上,端來飯碗一口口喂他吃。
葉云亭不知他心里所想,吃飯時只覺得,李歧看他的眼神,總是著怪異的……慈?
“……”他覺得自己大約是想多了。
第107章 沖喜第107天 (一更)
吃過晚飯, 李歧又以葉云亭上傷勢未好做借口,將他抱回了榻上。
被抱著走來走去,葉云亭覺得有些難為, 耳尖染了薄薄一層緋紅,眼底水瀲滟。他忍著赧道:“我自己能走。”
“但我想抱著你。”李歧用鼻尖蹭了蹭他的耳垂,著聲音低低道。
“……”他說的如此直白, 反倒是葉云亭不好意思起來,抿了抿, 沒再言語。
猜你喜歡
-
完結84 章

望春冰
他曾經嫁給一個男人,又被那個男人拋棄。 永治廿八年,裴耽一紙訴狀呈上天子御前,堅持與四皇子奉冰和離,割席斷義,永不相見。 名為和離,實同休棄。 半個月后,太子謀逆事發,奉冰身構大逆,下獄窮考,逾冬貶為庶人,流放牢州。 而他的前夫裴耽,卻從此青云直上,直至成為本朝最年輕的宰相。 逆案五年后,新帝召奉冰回京朝覲。 狀元宰相攻x落魄皇子受。年下。 逃避、折騰、誤會、磨合的離婚后文學。 愛在窮途末路時將他拋棄, 又在風煙俱凈處向他回眸。
16.1萬字8 5686 -
完結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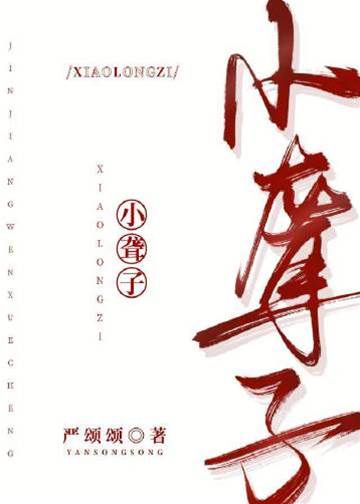
小聾子受決定擺爛任寵
憑一己之力把狗血虐文走成瑪麗蘇甜寵的霸總攻X聽不見就當沒發生活一天算一天小聾子受紀阮穿進一本古早狗血虐文里,成了和攻協議結婚被虐身虐心八百遍的小可憐受。他檢查了下自己——聽障,體弱多病,還無家可歸。很好,紀阮靠回病床,不舒服,躺會兒再說。一…
30萬字8.18 1787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