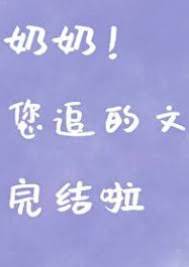《你說南境有星辰》 Chapter 11 神秘女友
歡越說越生氣,又不能大聲,控訴到最後,幾乎在用氣音說話了,衿羽眨眨眼,捂著直笑:“你都氣這樣了,還怕吵到他睡覺?”
“我這是善良。我媽之前更年期嚴重失眠,看著多可憐!彥偉說他是十幾年難得睡好覺了,也不曉得是做了什麽虧心事。”
“三三,其實也不怪他挑剔你,你看你這屋子,要不是咱倆好,我都不想抬腳進來,還有你的服,配得也太難看了。”見要反駁,衿羽直接捂住了的,“你自己說,同樣的屋子,別人願意待你狗窩,還是蘇教授房間舒服?”
對於這種答案顯而易見的問題,歡拒絕回答。
衿羽看著昨晚被歡在床頭的混運衫,直皺眉:“以前我還幫你把服都配好,選選款式,你到昔雲來了以後,完全在放飛自我,這樣的服你也穿得下去?”
“洗掉了嘛。”
“那就扔了呀!”
“多可惜,穿著還蠻舒服的。”
“你就是這樣,貪舒服,可好歹你也挑一下款式,別閉著眼睛拿到哪件算哪件。還有,那種熒綠、土玫紅我求求你別買了。”
“便宜嘛,一般斷碼剩的肯定不好。”
衿羽無奈地起了拳頭,作勢要打:“三三,你窮瘋了嗎?”
歡笑著一把抱住了閨的拳:“那可不!親親小羽,學校電路馬上整改好了,我這兒還缺兩套投影設備,要不你先認領一套?”
“你就知道敲詐勒索。”
衿羽狠狠地瞪了一眼,隻是於姑娘天生是張清純可人的小臉,瞪人都瞪得滴滴地,完全沒有殺傷力。
“沒辦法,邊就你最有錢呀。”
衿羽往牆那邊一指:“親的,真土豪在隔壁,你不找他?”
Advertisement
歡賊兮兮地著下:“他那裏我有大圖謀,嘿嘿,當然,剩下那套投影他也是逃不掉的。”
“三三,你有時候真是不要臉。”
歡“吧嗒”在好友臉上親了一大口:“你們可不就我不要臉嗎?走,反正都睡不著了,陪我跑步去。”
衿羽往被窩裏一:“不要,我頭疼。”
“走啦,跑一跑,保證神清氣爽。”
衿羽看套了件橙短袖,手又去取櫃最上頭的黃子,無奈地跳了下來,去在最底層的那條黑帶橙邊的長。
“三三,這明顯是一套。”
歡笑得直搖頭:“差不多,差不多的。”
“差很遠好嗎?”於衿羽拍著頭,恨鐵不鋼,“我不是讓你過得多致,但是讓自己和房間看上去清爽一點,總是件好事吧?”
看著好友語重心長的臉,歡不知怎麽,就想起蘇睿那天義正詞嚴地和說“你這樣好看多了”的樣子,想起他那雙漂亮如秋水星辰的眼,高高在上地說著“隻是為了避免視覺上的摧殘,覺得需要鼓勵你往正確方向改進”,歎口氣,幫衿羽抬起服出了配套的子。
歡越說越生氣,又不能大聲,控訴到最後,幾乎在用氣音說話了,衿羽眨眨眼,捂著直笑:“你都氣這樣了,還怕吵到他睡覺?”
“我這是善良。我媽之前更年期嚴重失眠,看著多可憐!彥偉說他是十幾年難得睡好覺了,也不曉得是做了什麽虧心事。”
“三三,其實也不怪他挑剔你,你看你這屋子,要不是咱倆好,我都不想抬腳進來,還有你的服,配得也太難看了。”見要反駁,衿羽直接捂住了的,“你自己說,同樣的屋子,別人願意待你狗窩,還是蘇教授房間舒服?”
Advertisement
對於這種答案顯而易見的問題,歡拒絕回答。
衿羽看著昨晚被歡在床頭的混運衫,直皺眉:“以前我還幫你把服都配好,選選款式,你到昔雲來了以後,完全在放飛自我,這樣的服你也穿得下去?”
“洗掉了嘛。”
“那就扔了呀!”
“多可惜,穿著還蠻舒服的。”
“你就是這樣,貪舒服,可好歹你也挑一下款式,別閉著眼睛拿到哪件算哪件。還有,那種熒綠、土玫紅我求求你別買了。”
“便宜嘛,一般斷碼剩的肯定不好。”
衿羽無奈地起了拳頭,作勢要打:“三三,你窮瘋了嗎?”
歡笑著一把抱住了閨的拳:“那可不!親親小羽,學校電路馬上整改好了,我這兒還缺兩套投影設備,要不你先認領一套?”
“你就知道敲詐勒索。”
衿羽狠狠地瞪了一眼,隻是於姑娘天生是張清純可人的小臉,瞪人都瞪得滴滴地,完全沒有殺傷力。
“沒辦法,邊就你最有錢呀。”
衿羽往牆那邊一指:“親的,真土豪在隔壁,你不找他?”
歡賊兮兮地著下:“他那裏我有大圖謀,嘿嘿,當然,剩下那套投影他也是逃不掉的。”
“三三,你有時候真是不要臉。”
歡“吧嗒”在好友臉上親了一大口:“你們可不就我不要臉嗎?走,反正都睡不著了,陪我跑步去。”
衿羽往被窩裏一:“不要,我頭疼。”
“走啦,跑一跑,保證神清氣爽。”
衿羽看套了件橙短袖,手又去取櫃最上頭的黃子,無奈地跳了下來,去在最底層的那條黑帶橙邊的長。
“三三,這明顯是一套。”
歡笑得直搖頭:“差不多,差不多的。”
Advertisement
“差很遠好嗎?”於衿羽拍著頭,恨鐵不鋼,“我不是讓你過得多致,但是讓自己和房間看上去清爽一點,總是件好事吧?”
看著好友語重心長的臉,歡不知怎麽,就想起蘇睿那天義正詞嚴地和說“你這樣好看多了”的樣子,想起他那雙漂亮如秋水星辰的眼,高高在上地說著“隻是為了避免視覺上的摧殘,覺得需要鼓勵你往正確方向改進”,歎口氣,幫衿羽抬起服出了配套的子。
“富二代真是一個德行。”
衿羽滿意地看穿上一套服,點點頭:“其實我也奇怪,蘇教授那麽高大上的人,怎麽會願意住在你這裏?”
歡把好友往前一拉,聲音又低三度:“你也奇怪,對吧?以前我以為是因為昔雲確實沒有好賓館,可就他來了以後這架勢,哪怕是買套房子自己歸置我都不奇怪,為什麽還會住在連廁所都要和我共用的七小裏呢?”
想起手機裏拍的那張傳真,充斥著大麻、法律等詞匯,歡不由分說,連拖帶拽把於衿羽拉出門跑步去了。
小鎮子早晨潤的空氣中有綠樹枝頭霜葉清香,當地最常見的三角梅攀爬出牆外芬芳吐豔,霧氣像迷離的紗,掩蓋了日之下這個與翡國接壤的邊陲小鎮的洶湧暗。貫通全鎮的主路上,新建的兩三層瓷磚小白樓與灰瓦木梁的舊屋錯著,不時有小三突突而過,早餐攤冒著蒸汽和食香味,昔雲此刻就像所有的老鎮子一樣,平靜、安詳,又充滿了煙火氣息。
“老師,早。”
“小老師,又出來跑步啦。”
“老師,來朋友了!”
歡作為城裏來的大學生,在七小已經待了三年,還幫著翻修重建小學,在鎮裏也算半個名人,兩人一路跑來一路招呼,還有個阿婆聽見衿羽咳嗽兩聲,不由分說塞了小袋“咳地佬”讓泡水喝,把衿羽得淚眼汪汪,拉著歡的手說回去就訂投影儀。
Advertisement
“早知道你這麽好收買,我就帶你去學生家家訪一圈,你會不會順便把孩子們冬天的被褥都包攬了?”
衿羽憤憤地橫了一眼,繼續低頭看著手機裏的圖片,神越看越嚴肅。
“三三,這份傳真是律師回複蘇睿的,照片裏的人涉嫌在境時攜帶大麻,蘇睿找律師朋友把保釋出來,這是傳真過來的保釋文件,”衿羽的眉頭越皺越深,“不過最後這裏對方有幾句私人留言,marijuanaisaclassC……大麻是C類毒品,youshouldhelphergetridofitintermsofyourpreviousexperience,三三,對方寫的是previousexperience,用你過去的經驗幫助戒除,難道蘇睿也吸過大麻?”
“不能吧……”
很難把蘇睿這樣的人和毒品,哪怕是毒相對算小的大麻聯係起來,何況彥偉作為緝毒警,應該不會把老底給一個有過吸食毒品史的人吧!
歡眉頭鎖。
萬一彥偉不知呢?
“KaleyEvelina,Kaley,應該是,以前是個有名氣的模特呢,上過MDC榜單的。”
衿羽把手機裏搜到的大圖拿給歡看,棕發碧眼的姑娘看起來和黑白照片裏的人廓有七像,還有一顆同在右眉邊的痣,隻是搜到的海報上,上了妝的Kaley看起來更為魅,是不折不扣的尤。
衿羽接過手機繼續查,越看越覺得不得了:“三三,這個KaleyEvelina是個癮君子呀,被拍到在家開嗨趴,還因為疑似吸毒吸high了鬧事,被取消了幾個代言。一定是!看,這條新聞說有一個往數年的富二代男友,在大學當理教授的,唉,照片拍這麽糊,也看不出來是不是蘇教授。”
歡把衿羽的手機搶了過來,新聞配圖拍得極其模糊,隻能看到Kaley醉醺醺自酒吧出來,半癱著掛在一個瘦高個男人的手臂上。
“五看不清楚,但服款式和係像算命的會穿的,所以他朋友吸食大麻,他至有大麻吸食史。”
歡常常掛著笑意的角抿出了嚴厲的弧度,衿羽小心地看了一眼好友,見神中除了驚訝失,倒沒什麽失落之類的緒,暗自放下心來,吐了一口大氣,這才相信,三三每次聽見調侃就奓並不是。
歡眉頭一挑,倒調侃上衿羽:“怎麽?你很失的樣子?”
“我本來覺得像蘇睿這種人,有有才有品有錢,簡直是偶像劇裏量定做的男主角,在你隔壁住了這麽久……”
“所以我就該五迷三道,暈乎得連他惡劣的本質都忽略掉?先不論他可能過大麻,兩個人在一起什麽最重要?三觀得合呀!我和算命的完全沒在一個國度,怎麽異相吸?再說了,我家雖然不是啥大富大貴,也足食把我寶貝一樣養大,何苦去攀高門大戶?”
“那倒也是。”
“如果他真的過大麻,我隻能直接請他走了。”
歡想起傳真最後的話,整張臉都冷了下來。衿羽很在好友臉上看到這樣堅決的冷漠,著手指躊躇著不知該怎麽接話。
正巧兩人一路慢跑,到了河邊,隔河相,斜對麵是一排極為簡陋的棚屋,有些甚至四麵牆都隻是用篾條、油紙布糊裱出來的,風。沒有電,就地取水,幾個得瘦骨嶙峋的孩子坐在盆子裏,用自製的漁線在釣魚,掃過歡和衿羽的目也是空的,連求意識都沒有。
“看看那裏,你覺得如果蘇睿吸過大麻,我怎麽和他相?”
與裏薩湖的棚屋相仿,此地停留的多是翡國流落而來的難民,以及當地因為吸毒、病痛流離失所的特困戶。即使是這樣,這裏依然是吸毒的重災區,甚至有些舉家都是癮君子,包括幾歲的孩子在,還有部分是HIV病毒攜帶者。所以鎮上的孩子都從小被家人警告,不能落單跑到河邊,更不能靠近棚屋。
衿羽對棚屋的印象也很深刻:“我上次過來給學校送東西,你和彥偉也特意代了,不讓我往這邊來。”
“別說你,那個時候校長連我都不讓來。不過,我去年帶的那個班,有兩個學生就是棚屋區的,小豆子家更是棚屋這邊難得家中有兩個壯勞力的家庭,隻是豆媽和都重病,導致家中不敷出。”想起機靈的小豆子,歡苦笑著說,“豆爸懂一點簡單醫,有時候他那裏還能‘買小包’,棚屋的人不會得罪他罩的人。而且我給這邊的人送過幾次救急藥,現在算是數能確保在棚屋出平安的人。就算是這樣,豆子爸爸也讓我盡量別過去,夜裏更是止去。”
猜你喜歡
-
完結260 章

小可愛你挺野啊
第一次和江澈見麵,男人彎著一雙好看的眼,伸手摸摸她的頭,笑著叫她小喬艾。他天生笑眼,氣質溫雅中帶著些許清冷,給人感覺禮貌親切卻又有幾分疏離。喬艾正是叛逆期的時候,個性還不服管教,但為了恰飯,她在江澈麵前裝得乖巧又懂事。時間一久,跟江澈混熟,喬艾的人設日漸崩塌……她在少女時喜歡上一個男人,長大後,使出渾身解數撩他,撩完消失的無影無蹤。多年後再遇見,男人紅著眼將她圈進臂彎裡,依舊彎著眼睛,似是在笑,嗓音低沉繾綣:“你還挺能野啊?再野,腿都給你打斷。”
44.2萬字8 20042 -
連載2076 章

撿個首富回家寵
送外賣途中,孟靜薇隨手救了一人,沒承想這人竟然是瀾城首富擎牧野。
237.7萬字8 208041 -
完結213 章
生崽痛哭:豪門老男人低聲輕哄
【年齡差11歲+霸總+孤女+甜寵+無底線的疼愛+越寵越作的小可愛】 外界傳言,華都第一豪門世家蘇墨卿喜歡男人,只因他三十歲不曾有過一段感情,連身邊的助理秘書都是男的。 直到某天蘇墨卿堂而皇之的抱著一個女孩來到了公司。從此以后,蘇墨卿墮落凡塵。可以蹲下為她穿鞋,可以抱著她喂她吃飯,就連睡覺也要給她催眠曲。 白遲遲在酒吧誤喝了一杯酒,稀里糊涂找了個順眼的男人一夜春宵。 一個月以后—— 醫生:你懷孕了。 白遲遲:風太大,你說什麼沒有聽見。 醫生:你懷孕了! 蘇墨卿損友發現最近好友怎麼都叫不出家門了,他們氣勢洶洶的找上門質問。 “蘇墨卿,你丫的躲家里干嘛呢?” 老男人蘇墨卿一手拿著切好的蘋果,一手拿著甜滋滋的車厘子追在白遲遲身后大喊,“祖宗!別跑,小心孩子!” 【19歲孩子氣濃郁的白遲遲×30歲爹系老公蘇墨卿】 注意事項:1.女主生完孩子會回去讀書。 2.不合理的安排為劇情服務。 3.絕對不虐,女主哭一聲,讓霸總出來打作者一頓。 4.無底線的寵愛,女主要什麼給什麼。 5.男主一見鐘情,感情加速發展。 無腦甜文,不甜砍我!
39.3萬字8 14199 -
完結18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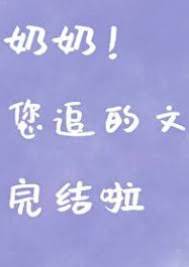
南風知我意
清遠公安裴西洲,警校畢業履歷光鮮,禁慾系禍害臉,追求者衆卻無一近的了身,白瞎了那顏值。 某天裴西洲受傷醫院就醫,醫生是個女孩,緊張兮兮問他:“你沒事吧?” 衆人心道又一個被美色迷了眼的,這點傷貼創可貼就行吧? “有事,”裴西洲睫毛低垂,語氣認真,“很疼。” “那怎樣纔會好一些?” 裴西洲冷冷淡淡看着她,片刻後低聲道:“抱。” - 緊接着,衆人發現輕傷不下火線的裴西洲變乖了—— 頭疼發熱知道去輸液:南風醫生,我感冒了。 受傷流血知道看醫生:南風醫生,我受傷了。 直到同事撞見裴西洲把南風醫生禁錮在懷裏,語氣很兇:“那個人是誰?不準和他說話!” 女孩踮起腳尖親他側臉:“知道啦!你不要吃醋!” 裴西洲耳根瞬間紅透,落荒而逃。 ——破案了。 ——還挺純情。 - 後來,裴西洲受傷生死一線,南風問他疼嗎。 裴西洲笑着伸手擋住她眼睛不讓她看:“不疼。” 南風瞬間紅了眼:“騙人!” 卻聽見他嘆氣,清冷聲線盡是無奈:“見不得你哭。”
36.3萬字8.18 15565 -
完結510 章

改嫁總統后,假千金成團寵了!
【真假千金+團寵+閃婚+萌寶】大婚當天,許栩沒等來新郎,卻等來了未婚夫霍允哲和許雅茹的曖昧視頻。 她滿腹委屈,給遲遲未來婚禮現場的養父母打電話。 養父母卻說:“感情這事兒不能強求,允哲真正喜歡的是雅茹婚禮,趁還沒開始,取消還來得及。” 直到這刻,許栩才知道,得知她和許雅茹是被抱錯的時候,養父母和霍允哲就早已經做好了抉擇! 不甘成為笑話,她不顧流言蜚語,毅然現場征婚。 所有人都以為她臨時找的老公只是個普通工薪族。 就連養父母都嘲諷她嫁的老公是廢物 卻不想海市各方大佬第二天紛紛帶著稀世珍寶登門拜訪! “海市市長,恭賀總統新婚!送吉祥龍鳳玉佩一對!” “海市民政局局長,恭賀總統新婚,送錦緞鴛鴦如意枕一對!” “海市商務部部長,恭賀總統新婚,送古董梅瓶一對!”
59.8萬字8 3582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