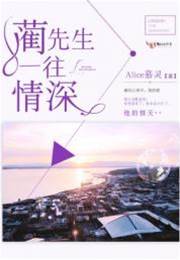《女校》 第一百一十二章 初吻
“法斗,也像你。”
“它哪兒像我,它像只小豬,它像你,死纏爛打的樣兒。”
“那你養,養著就知道了。”
他在那兒說。
一貓一狗,一一憨,這家里瞬間就熱鬧了,所以說可的小生命真的有治愈效果,前段時間拂不去的霾消了,眼前也一片亮堂,滿腦子都是這兩個小家伙,另一個白盒子里放的是貓糧狗糧,貓窩狗窩,還有各式各樣的小玩小零食,這興趣大得不得了,回頭表揚:“今年的禮我超級滿意。”
之后,事就多了。
研究這兩個小家伙吃什麼喝什麼就可以花掉半天的時間,還有名字,靳譯肯堅持布偶貓的名字里得有個“七”,于是五分鐘之就給起了,小法斗“悟空”,布偶貓“七戒”,靳譯肯得知時這倆已經認名字滿地跑了,他沒話說,龍七樂呵,還問他:“龍二和悟空同時掉水里你救誰?”
“七戒。”
“七戒又沒掉水里。”
“我怕它濺著水沫子。”他說。
偏頗的心真是很明顯,他甚至還留出了另一個手臂文位置給長大后的七戒。
而隨著氣溫悶熱,知了聲越來越燥,今年的盛夏就這麼悄無聲息地來了,大學暑假的第一個月仍在家里躺,很久沒過這樣不用工作不用滿天飛的日子,把之前該看的電影和表演專業類的書都看了,還加回了之前的班群,開始清算自己落下的課程,順便眼眼這些跟自己同班了一年卻連面都沒見過幾次的同學。
班長是一個葛因濘,長相非常清冷掛的孩子。
看群員頭像的時候就注意到了,膠片照,很立的五,黑發,冷白,眼神寡,一看就是難追那一掛,而且越看越眼,不止是在校見過,好像,想半天,在腦子里洗牌,終于想起來上半年有一部口碑過得去的懷舊青春劇,在里頭擔了二的角。
Advertisement
所以也是一邊上課一邊拍戲的半出道年輕藝人。
倒不太像是做班長那塊料。
正看著,手機“叮”一聲響,老坪的信息來了,提醒記得試Fire&Gun送來的禮服,《冷蟬》的最后一場宣傳就在一周后。
虧了悟空和七戒,這幾天的神特別好,被阿姨的湯養得氣紅潤,而且龍梓儀是老年人作息,每天不到十點睡覺,六點就拉晨練,過了連續半個月不熬夜不喝酒不煙的日子后,到出席宣傳的那天,的活照在全網了。
實時熱搜第一。
也有Fire&Gun一半的功勞,老坪說這品牌簡直把當親兒寵,送來的是還沒展出的超季禮服,高級又叛逆的淡橘抹配大開叉白,小腹,長卷發高扎起,真鉆頸鏈,滿滿的夏日風與超模,值又上一個高峰,那些時尚號博主都轉瘋了。
當晚還有一個實時熱度高的話題,是關于和臧習浦的全場零流。
真沒什麼可聊的,臧習浦在上停留的眼神再多,也完全不接,總看著導演,或主持人,或席下觀眾,所以臧習浦從始至終也沒往拋什麼話茬,活臨結束時,他還提早退場了。
鄔嘉葵由于忙著拍邵導的戲,沒出席這最后一波宣傳。
所以班衛又撲了個空。
他開著他那超跑來的,專門在后臺等到活結束,特別沒勁,說本來不是發了活通告嗎,龍七在更室換服,隔著門回他:“你到現在還只能靠方通告來追的行程?看不出來啊,你追人這麼遜的?”
“這不是早跟你說過鄔嘉葵難追。”說完,還補殺一句,“能像你嗎,竇浚云都能把你約出去。”
Advertisement
門咔一聲開,換完了灰T與牛仔,松著腦后扎得特別的高馬尾,淡淡回:“可不是,竇浚云都能把我約出去,你當初追我時,一杯茶我都不愿意喝你的。”
班衛子一,這就想起自個兒以前也被迷得要死要活過,搖頭嘖一聲,像回憶黑歷史一樣,龍七把摘下的皮筋往他那兒扔,捋長發,他抬頭扯話題:“你是不是要開學了?”
“還有一周。”
“你那校區也在昭華館那塊兒對吧。”
“想干嘛?”
“今晚去那兒喝酒唄。”
“不喝,”往手上涂水,“校區有什麼好去的,我最近戒酒。”
“我去,你們這種戲劇學院的晚間活最有意思了,開學前一周那附近的小酒吧熱鬧得,”班衛抬著,刷著手機,“得去得去,反正靳譯肯也沒管著你,找個清吧,你喝茶我喝酒。”
還是沖著戲劇學院漂亮大學生去的。
桌上的手機有幾條未讀信息,龍梓儀發來的,說和盧子牧要過一下二人生活,讓識相點晚一點回來,悟空和七戒都已經喂了。
這媽當得還真是直接且不害臊,嘆一口氣,回班衛:“你明明是想找免費代駕,自個兒喝大酒舒坦了,讓我把你連人帶車送回去。”
“唉,兄弟一場。”
班衛往手臂上送一肘,白眼。
最終還是去了。
熱鬧是真熱鬧,就算是清吧,來來往往的男也很多,而且班衛挑的這家恰好有一伙學生在舉行學前派對,各個都很的樣子,湊在一起舉杯盞的,著風格各異,妝發致有個,應該都是戲劇學院的沒跑了,戴了個得很低的棒球帽,環著臂,跟在班衛的后,坐到清吧靠角落的一張圓桌邊。
Advertisement
班衛也著帽子,他的人氣在大學生間可比要火得多,昭華館一條街上十間酒吧有九間都放他的音樂,班衛做音樂是真牛,就連現在臺上那支樂隊也正唱一首班衛今年的新單。
主唱是個男生。
玩得也嗨,穿著背心與黑破,肩頸上已經布滿了汗,一手握立式麥克風,一手舉著喝到一半的啤酒瓶,帥,唱起歌來居然比班衛的原唱還帶,臺下半數生瘋了一樣跟著他唱,班衛也跟著音樂的節奏抖,龍七說:“你要那個長相,鐵定比現在紅。”
“唱得是好,”班衛說,“但我比他帥多了。”
嗤笑。
“這能比得過肯肯?”班衛又說。
“你別拉戰友,我一句都沒扯他。”
但班衛打趣歸打趣,一點兒都不恃才傲,人家唱得好他是認的,原本是來看姑娘的,這會兒愿意為了這樂隊多坐一會兒,他又點了酒,繼續叨他追鄔嘉葵那事兒,龍七聽得耳朵都快磨出繭了,這時候,那主唱興致正高,舉著的半瓶酒突然往場一灑,原本還跟班衛打皮子,眼角邊突然一涼,被潑到了。
班衛翹著腳大笑,摘帽子,拿紙巾。
順著笑聲,臺上那主唱男生看過來,正唱完一曲,氣吁吁的,拿著隊員遞過來的水喝,又用巾了滿是汗的臉,看這兒兩三秒后,他別頭到調音師那兒說話。
原本切好的一首搖滾曲前奏暫停,四五秒準備后,切一首式鄉村樂。
吧燈流轉,曲調懷舊,風格變化那麼大,像特意點給某人聽的,把棒球帽戴上,班衛的酒來了,他正講到第四次邀鄔嘉葵看自己演唱會被拒的事,右手手肘搭著椅背,左手在空中習慣地比劃來比劃去。
Advertisement
那主唱站在白下,抵著立式麥克風,踩著點進節奏。
……
Every
time
we
have
to
say
goodbye
(每當我們不得不再見之時)
I'm
counting
down
until
we
say
hello
(我就已經為下一次重逢開始了倒計時)
Every
touch
is
like
the
strongest
drug
(每一次都像是最猛烈的一劑強藥)
don't
know
how
much
longer
can
go
(不知道我們這份我還可以延續多久)
……
怪好聽的。
在被班衛言語轟炸的同時,像臺上看一眼,而那一眼,偏偏對上主唱灼灼盯著的視線。
……
never
had
something
that
can't
walk
away
from
(從未有這樣一份愫讓我難以放手)
But,
girl,
my
self-control's
so
paralyzed
(我的自制力已為你潰敗
難自控)
When
it
comes
to
you,
no,
ain't
got
no
patience
(每當我慢慢靠近
我已經迫不及待)
There's
something
'bout
you
girl
just
can't
fight
(關于你的一切都讓我如此難以抗拒)
……
本來以為是恰巧。
但這主唱一直不收視線,歌詞里的強烈,唱得也強烈,一直盯著這兒,濃厚而狂熱,像是認識許久的老朋友,或是剛剛經歷過一場纏綿的舊人,奇了怪,久而久之,班衛也隨的視線看過去。
立刻就笑:“你認識他?”
“不認識。”
“他盯著你呢。”
“他盯著你,不是我。”
班衛抖著下,跟著節奏聽歌,不過五秒又忍不住說:“眼神這麼強烈,這是認出你,要泡你。”
“扯。”
班衛靠著椅背坐一會兒后,從兜里掏手機。
“你干嘛?”
“發給肯肯,讓他知道你在國這行多好。”
“你神經病啊。”拿著菜單往班衛上拍一下,班衛嬉皮笑臉躲閃,與此同時,曲子進高部分,這男生唱得彎腰。
You're
like
that
cigarette
(你正是香煙的癮)
That
shot
of
100
proof
(或一杯五十度的烈酒)
No
matter
how
much
get
(無論我得到了多)
I'm
always
craving
(都還是更多)
That
feeling
when
we
kiss
(彼此親吻的那種奇妙覺)
The
way
your
body
moves
(互相纏綿繾綣的那副模樣)
No
matter
how
much
get
(無論我已經得到了多)
I'm
always
craving
you
(都還是著你)
Craving
you
(著你)
……
唱得那麼,又是那麼懷舊的曲風,讓人忍不住就回想起一些青的長經歷,但這些經歷被靳譯肯占據得滿滿當當,滿腦子都是他的眼睛和他笑起來的角,還有他喝酒的結和夾煙的手指,他吊兒郎當抬著二郎盯著時的眼眉,他批改得一片通紅的理試卷,以及他每一次從后進時,在耳邊的低語話。
完了,才兩個月,已經從神上想那混蛋,發展為生理上想那混蛋,心口燥燥的。
這會兒,主唱松開麥克風下臺,朝這個方向來。
班衛吹一聲哨,龍七煩他,白他一眼。
“沖你來的。”他打包票。
而就在班衛這句話落的同時,那男主唱已經非常不給面兒地越過他們這一桌,出著汗的手臂與龍七的肩膀輕輕相,,他俯到后頭一桌,直接親上那一桌其中一個孩兒。
這瞬間,音樂還沒停,吧氣氛極其高昂,那一桌的生也笑著著鼓掌,其中一姑娘嗓音高亮:“直接嫁吧!葛因濘!”
……
葛因濘。
名字耳,龍七湊熱鬧回頭看,一熱吻剛結束,那主唱直起,寵地生耳后的長發,縱使現場再火熱,那生眼里也只是淡淡欣悅,微直起,在他耳邊從容地說話,旁邊一嗓門大的生繼續打趣:“哎喲這私底下約什麼呢!”
看周圍人的反應也都悉兩人的關系,那看來就是熱中的,龍七往班衛那兒撇頭:“你剛才讓我很尷尬。”
班衛斜斜坐著,態度一點兒不變:“那首歌十句里至有八句是唱給你聽的,我看得出來,你別不信。”
話落,嗓門高亮的生又蹦來一句:“這不龍七嗎?”
突然被cue,不湊熱鬧了,轉回子,那生接著看見邊的人,尖就跟殺豬一樣:“班衛!!”
周圍桌的人陸陸續續看過來,有點大,看時間不早,跟班衛商量準備走,起時,大部分人都認出和班衛了,氣氛重新熱鬧起來,班衛到后面干脆摘帽子,場瞬間發出一陣歡呼尖,向他舉酒杯,他舉著棒球帽喊一句:“大家繼續玩!這場我請!”
歡呼雀躍的鼓掌好聲與手機閃燈下,環著臂,在班衛的護送下走出清吧。
“剛才那姑娘葛因濘是吧?”前腳剛出,他就問。
“看上人家了?這可是有男朋友的。”
“不是,”倆人往停車場的方向走,班衛手兜,“你不知道?是邵國桉的外甥。”
步子稍微緩了一下。
邵國桉,邵導,臧習浦曾經引薦見的人,京圈說話的主兒,奚靜的后臺。
“嘉葵最近不是在拍邵導那片子嗎,這姑娘在里頭也有角兒,戲份不多,我上回探班見過,實打實的關系戶。”
到停車場了,一聲解鎖,龍七開主駕駛車門:“那你專門告訴我這,是什麼意思?”
“也就讓你知道一下,圈里的人際關系說到底就那樣,也不是說要維護,就是別有矛盾。”
“那沒后臺的人,我就能鬧矛盾了?”
“哎,這不怕你格太沖嗎。”
關門,發車,龍七回:“知道了,謝謝你,但我也不是不講道理的人,誰對我好我就對誰好,說不定我還喜歡。”
班衛聳肩。
到家了。
送班衛花了一個小時,這會兒十二點整,想著也夠晚的了,用鑰匙開門,門剛開一個兒,悟空已經搖著尾在兒里頭探頭,可死了,而客廳的燈開著,亮堂堂的,將悟空抱起,關完門,轉頭就看見在餐桌邊上坐著的盧子牧。
……
的手被皮帶圈著,反綁在椅背上。
“……”當下心就一聲口,上問,“你們玩這麼浮夸?”
而盧子牧本來半睡半醒,聽見靜轉頭,馬上氣若游出聲:“哎七七,你回來了,趕,你趕給我喂幾口。”
桌上有一桌燒好的飯菜,一筷沒,都涼了,七戒正窩在盧子牧的棉拖鞋旁,龍七有點警覺,蹲把七戒也抱起來,兩手各抱一個:“家里進賊了?”
“不是,”盧子牧馬上搖頭,“先別說,你快給我喂幾口,我沒勁兒說話。”
桌沿邊上放著盧子牧的手機。
“我媽呢?”
“在房間里。”
“那我先給你松綁唄。”
“別,還在氣頭上,晚點兒更炸,你喂我就。”
“我媽綁的你?”
“嗯,對。”
“氣什麼?”把一貓一狗放回地板,往桌上拿筷子,問。
盧子牧嘆口氣:“出版社主編約我吃飯聊書,我跟人多聊了幾句。”
“就這啊?”
盧子牧撇點頭,龍七又問:“我媽控制這麼強的?”
再次撇,把頭點得很重,怨氣真的很重,而一勺子湯剛要喂到邊,臥室的門咔一聲巨響,嚇了一大跳,手抖,湯到盧子牧脖子里,龍梓儀的腦袋探出來:“龍七!敢!”
七戒都炸了,喵嗚一聲,竄上沙發,龍梓儀接著說:“進來!給你收拾開學的行李呢,搭理,讓著!”
門砰一聲關。
但龍七沒聽。
作快,迅速把湯倒飯里,盧子牧也配合著趕張,喂兩口后,龍梓儀的火山嗓又發:“龍七!!!!還想不想去上學了!”
放碗,拍盧子牧兩下肩膀后,朝臥室趕。
猜你喜歡
-
連載1164 章
穿到跟殘疾大佬離婚前
遲清洛穿進一本狗血小說,成了商界殘疾大佬作天作地的小嬌妻。小嬌妻驕縱任性,飛揚跋扈,還紅杏出牆。遲清洛穿來當天,原主正因為爬了娛樂圈太子爺的床上了熱搜。大佬丈夫終於同意跟她離婚。遲清洛:“老公我愛你,之前跟你提離婚是我一時糊塗。”輪椅上的大佬眸色深沉:“你糊塗了很多次。”不不,從今開始,她要改邪歸正,渣女回頭金不換。可是漸漸的大佬好像變得不一樣了,對她說抱就抱,說親就親。嗯?大佬不是淡薄情愛,隻把她當擺設的麼?遲清洛眨眨眼:“好像有哪裡不對。”大佬將小嬌妻圈入懷中,指腹摩擦著她的唇珠,聲音嘶啞:“哪裡不對?”
104.7萬字8 56328 -
完結845 章

寵婚入骨
許家多年前送去鄉下養病的女兒許呦呦回來了,回來履行與林家的婚約婚禮前夕新郎逃婚去國外找他的白月光,眾人:哇哦……【吃瓜表情】許呦呦:哦豁。下一秒,白皙細軟的小手攥住男人的衣袖,甜糯糯的語調:“墨先生,您可以娶我嗎?”……墨深白商業巨擘清心寡欲,神秘低調,在波雲詭譎的商場叱吒十年,無一家報刊雜誌敢刊登他的一張照片,也沒有一個異性能讓他多看一眼。所有人都說墨深白娶許呦呦一定是協議婚姻,一年後絕對離婚。許呦呦津津有味的吃著自己的瓜,只是吃著吃著就發現好像不對勁啊。逛街購物不需要買單,吃飯不用點餐,不管走到哪里大家熱情跟她打招呼:墨太太好。後來墨深白的白月光回來了,前未婚夫深情表白:“呦呦,只有我是真的愛你,回我身邊,我不嫌棄你。”許呦呦還沒來得及回答被男人霸道的攬入懷中,低音性感撩人:“寶貝,你沒告訴他,這裡有了我們愛的結晶。”溫熱的大掌貼在她平坦的小腹上。許呦呦紅了臉,渣男紅了眼……【無腦瑪麗蘇先婚後愛文|專注虐男二】
142.9萬字8.18 230570 -
完結110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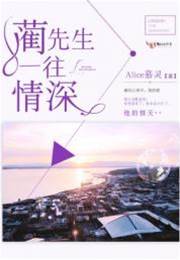
藺先生一往情深
曾有記者舉著話筒追問C市首富藺先生:“您在商界成就無數,時至今日,若論最感欣慰的,是什麼?” 被眾人簇擁,清俊尊貴的男子頓步,平日冷冽的眸難得微染溫色,回答:“失而複得。” - 人人都說她死了,藺先生心裡有一個名字,彆人不能提。 他走她走過的路,吃她喜歡吃的食物,人前風光無限,內心晦暗成疾。 情天眉眼寂淡:有些愛死了,就永遠不在了。 他眼眸卻儘是溫然笑意:沒關係,沒關係。 她的心再冷,他捂暖。 世人隻知商場中藺先生殺伐決斷手法冷酷,卻從不知,他能將一個人寵到那樣的地步。 - 但後來 人來人往的步行街頭,商賈首富藺先生仿若失魂之人,攔著過往行人一遍遍問—— “你們有冇有看到我的情天……” 他的情天,他的晴天。 · ·寵文·
138.8萬字8 78510 -
完結855 章

報告總裁,你老婆又跑了
黑暗中,他鉗住她的下巴,“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 她自輕自賤“知道名字又如何?你只要一分不少的把錢打到我卡上就行了。” 本以為拿到錢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當一切沒有發生。 誰知那古怪男人從此卻陰魂不散的纏住了她。
167.7萬字8 38184 -
連載176 章

軍婚撩人:首長大人請深吻
她代替姐姐嫁給了那個據說身有隱疾的年輕軍長。他的寵,他的溫柔霸道,讓她毫無抵抗的臣服。卻原來爾婚我詐,不過是一段遠的要命的愛情。幾年後,她攜子歸來,撩撥的他欲火焚身。他反身把她壓在辦公桌上,“老婆,按照一夜七次的頻率來算,你已經欠我很多了,要不咱們還是先還債吧!”
30.5萬字8 2624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