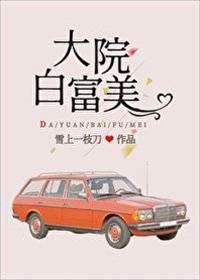《請你留在我身邊》 第6章 不丟人
徐西貝請迎晨吃飯,看樣子已經從被劈的影里走了出來。
“晨兒你今天敞開了吃,吃完咱們再去K歌,宵夜什麼的我都安排好了。”
“饒了我吧,”迎晨翻著菜單,說:“我脖上的傷可經不起折騰。”
徐西貝嘆了口氣,真心實意地道歉:“對不起啊晨兒,上回因為我的沖,連累到你了。”
天臺那一幕驚險猶在,說不后怕是假的。
迎晨現在還有脾氣,怪責:“知道就好,我差點冤死鬼了。”
徐西貝不好意思地撓了撓鼻尖,“多吃點,我請客。”
迎晨加了盤紅燜豬手,評價:“這地方裝修還不錯,老板有點品位。”
“當然得有品位,價格死貴。”
“心疼了?”
“請你吃飯就不心疼。”
迎晨樂了,起,“我去趟洗手間。”
——
同是這家餐廳。
“哥,這是什麼做的?”林德一臉興,指著墻上的掛飾,“是水晶麼?好亮!”
“玻璃拋,技含量不高。”
“那這個呢?這筆字我咋一個都不認識。”林德的頭往左歪往右歪,費勁地認。
“草書,寫的是沁園春。”厲坤拍拍他,“行了別看了,走吧,去吃飯。”
林德踟躕在原地,“要不,厲哥,咱換地方吧。”他掃了一圈這里,眼神猶豫膽怯。
厲坤看出了他的遲疑,平靜道:“好不容易放天假,帶你出來轉轉,沒事,不貴。”
林德來自農村,真正的窮鄉僻壤,能走出大山的孩子都不容易,部隊工資不高,他每個月還得往家里寄,平時休假也不出去玩。
厲坤表面不說什麼,但有機會就帶他出來見見世面。
“想吃什麼自己點。”
厲坤閑散地靠著椅背,一只手搭著背沿,出的手指長而勻。他咬了煙在里,顧忌是公共場合,所以只過過干癮,并未點燃。
Advertisement
“哥,能吃嗎?”林德盯著菜單上的大鵝眼冒。
厲坤笑道:“能,點兩只。”
“得嘞!”
林德點完菜,“好了!”
那笑容,比天花板上的水晶燈還亮堂。
“我看看。”厲坤過目了一遍,又加了兩個點心,對服務員說:“謝謝。”
林德手掌,坐得筆直端正,眼睛看看窗簾,又瞄瞄碗筷,再掃掃別桌。
厲坤覺得好笑,假裝嚴肅,“咳咳!”
“嗯嗯!”林德連忙目不斜視,坐得比剛才更直了。
堅持了十幾秒,他說:“報告!申請上廁所!”
厲坤摘了煙,點下,“批準。”
林德大白牙一,溜得飛快。
這店新開張,上座率極高,加之地兒大,林德繞了半天都沒找到洗手間。問了個服務員,對方忙著上菜,隨便一指:“在那邊。”
于是林德就懵懂地往“那邊”走。走過一段走廊,這邊全是包廂,一個挨一個。
林德經過一間,突然從里頭傳出一道聲音——
“站住。”
這聲音有點,但林德瞬間沒記起來,他轉過頭。
“誒嘿,還真是這位兵哥哥啊。”那人起,從席間走近,臉被酒水養得紅上頰,他著林德,眼睛在笑,笑里著壞。
林德認出來了。
寶馬車的主人。
就上回在路口查車,不配合執法大吵大鬧的那一位。
“東子,有人啊?”又湊過來一個,這個腳步踉蹌,明顯喝大發了,定睛一瞧,“噢喲!人民子弟兵同志。”
他怪氣地撒開嗓子,學樣:“敬禮敬禮。”
林德背脊正,不理睬,正要走。
“慢著。”傅東住。
林德頓足,側目,“干嘛?”
包廂里一桌的人,個個紈绔,酒瓶堆了一地兒,都是看笑話的。
Advertisement
傅東眼神微變,佯裝憂慮:“解放軍同志,我得跟你匯報一下,咱這包廂里有個黑東西——喏,就在那。”
他手隨便一指,沒等林德看清,子就攔住,“會不會是炸彈?”
林德:“……”
傅東:“你是特警,幫忙看看。”
這個份讓林德下意識地立正。
傅東生意人,人,察言觀厲害的很,眼皮一挑,把路讓出,“來來來,專業人士排除一下,咱們也好放心,再說了,這是公共場合,萬一有個什麼,也不太好對吧?”
林德心里不安,但腦瓜子比不上他們。人被懵懂地帶進了籠子。
既然進來了,林德覺得,檢查一遍也沒什麼。
于是,他走過去,哪怕穿著便裝,背脊也永遠直。
但就在他走向窗戶的過程里,傅東使了個眼——
靠邊的一個人拿著瓶白酒突然起,扯開座椅站了出來。因為太快,林德閃避不及,了個正著。
那人哎呀一,同時手心一松,就聽“稀里嘩啦”一陣刺耳。
酒瓶掉落在地,淌了個干凈。
林德懵了。
“哎呦我天!這酒老貴了!”對方佯裝心痛,指著林德:“怎麼回事啊,走路也不看著點!”
林德實誠,有話就說:“是你自己撞上來的。”
“嗨?你這人咋這樣啊?摔爛就摔爛唄,但你這樣污蔑人就不對了啊。”對方嘁了一聲,嫌棄:“還是軍人呢。”
林德聽到最后一句,像是被忤了逆鱗的魚,聲音陡大:“我沒有!”
“行了行了。”傅東出來“打圓場”,“多大點兒事啊,不就一瓶五糧,照價賠償不就得了。”
那人配合極好:“啊!20年五糧,還沒開蓋,給你打個折。”
Advertisement
林德一聽那五千塊的數字,人已經徹底懵掉了。
——
迎晨補了會妝,才從洗手間出來。
悠閑地原路返回,偶爾看看墻上的一些別致掛飾。
“壞了東西賠錢,這可是天經地義,小兄弟,你說,是不是這個理?”
經過走廊,右邊的包間有人說話,語氣不善。
迎晨不興趣,正準備走。
“我沒有撞他!”
這聲音?
迎晨眉心淺皺,放停腳步。
“我知道了,你這是記恨我上回查你車!”
迎晨輕推門。
林德瘦高的影在這窄窄的門里憤怒得直抖。
傅東撕破了臉:“酒就是你砸壞的,怎麼?沒錢?啊!”
他倒滿三大杯白酒,酒瓶一扣,“把它們給我喝嘍,讓你走。”
在座紈绔公子哥哄笑。
“喲?橫眼看我?不喝就賠錢!”傅東威脅,險的很:“不然我就去你們部隊舉報,在場的全是證人,看你怎麼辦。”
“是麼?證人?”清脆的聲,格格不地闖了進來。
眾人回頭,迎晨雙手閑散地環搭在前,要笑不笑的樣子,頗有冰山人的氣質。
傅東皺眉:“你誰啊?”
迎晨走過來,攔在林德前,毫不怯地看著傅東,“一瓶酒,犯得著這樣?”
“喲,幫手啊。”傅東笑得像個無賴,雙肩一聳:“犯不著犯不著,可他賴賬啊。”
“有說不賠嗎?”迎晨聲音冷了幾度。
傅東識貨,這的一看就是有點底子的人。
于是故意道:“談錢傷和氣,酒桌朋友。把這杯酒干了,咱們就當是個誤會。”
“誤會?”迎晨突然笑出了聲,鄙夷之意盡顯。
笑夠了,走過去。
“姐。”林德拉住。
“沒事。”迎晨撥開手,轉看著傅東,拿起那杯滿當的白酒。“是不是喝三杯這事就算完?”
Advertisement
底氣太足,凌厲明艷,傅東竟一時舌頭打卷。
“行。”
迎晨舉杯仰頭,兩口干干脆脆,幾秒之間杯子就見了底。
全場傻眼。
“姐!”林德大聲。
迎晨心跳不,甚至角都沒有半點殘酒,笑:“這兒臟東西太多,喝點酒散散味。”
傅東臉一變。
迎晨沒暫停,第二杯又了。
“哎呀,這兒不僅臟,味道還難聞,酒能殺毒,別把自己惡心壞了。”
迎晨端著空杯,對傅東搖了搖,“你們聞見了嗎?不好聞吧?”
這些人臉如豬肝,個個不吱聲。
“第三杯。”迎晨面不改,看向林德正了語氣:“喲,還哭了?”
林德眼圈通紅,倔強地撐著不肯落淚。
迎晨收了笑,陡然嚴厲:“不許哭!有槍炮聲的地方你都去過,上過戰場挨過子彈,別的垃圾能比嗎?!”
把最后一杯酒喝完,杯子一丟,拉開包掏出一疊錢。
迎晨把這把錢重重甩到傅東臉上,趾高氣揚,再沒給他半點面子:“你算個什麼東西?也就這五千塊錢的出息!”
傅東徹底懵了,臉被扇得火辣辣。
迎晨出生將門,骨子里承襲了一傲勁,唬住這幫人綽綽有余。
聲音嘹亮:“林德,走!”
——
出了走廊,林德再也忍不住,眼眶通紅地泣了兩聲。
“姐,謝謝你幫我,我真的沒有砸壞他們的酒,是他們……”
迎晨不耐煩地打斷,手虛在半空,“扶我。”
那三杯酒的量不,喝的急,這會勁頭上來,人犯了暈。
“姐,姐你慢點。”林德的手剛搭上肩膀,就被一道力氣撇開——
“給我。”
林德懵了半秒,驚聲:“厲哥!”
厲坤沉臉抿,作魯地把迎晨搶了過來,架住的肩膀往上一提,自己卻下意識地離遠遠。
厲坤表不耐,仿佛在說:這他媽什麼況?
他在餐桌上等了半天,菜都上齊還沒見林德來,電話也打不通,于是就出來找。結果到了這麼一個活祖宗。
而酒量不錯,只是腳底有些晃,其實人沒事的迎晨,一看是厲坤,頓時見機行事,徹底變了骨醉鬼,整個人都靠了過去。
的有意無意地蹭著厲坤。
厲坤明顯僵。
迎晨勾起角,眼睛一閉,干脆來了個徹底醉死。
厲坤鐵臂發,剛想推開。
“哥,晨姐剛才幫了我。”
林德適時開口,斷斷續續地講了剛才的經歷。
“……晨姐幫我解圍,喝了三杯白酒才變這樣的。”
講完。
厲坤一怔。
懷里的人拱了拱,手還住他的心口。
很熱,在跳。
厲坤用最大定力,才讓自己表現得不那麼發抖。
迎晨閉著眼,心在笑。
真好啊,他沒有推開自己了。
鬧了這一出,飯也別想吃了。林德那是哭著求著,讓厲坤把迎晨送回去。如果說,以前還是良好印象,那麼經歷這一次,可以說是生死之了。
厲坤被他鬧得心煩,“我送!你他媽別嘮叨了!”
林德頓時一口大白牙,兩腳一并,敬禮:“謝謝隊長!”
夏末,夜風爽利。
厲坤開了半邊車窗過風,副駕駛上迎晨歪頭斜腦,還在“犯迷糊”。
犯迷糊就是為了等下車的這一刻,能明正大地黏在厲坤上。
嘟囔語,不放過任何一秒和他親接的機會。借著酒醉,把自己完全吊在厲坤脖上。
迎晨摟他的脖子,臉頰往男人的肩窩蹭。酒味兒混著上的香水味,生生調和了一劑溫曖昧。
厲坤渾僵。
“唔……頭好暈。”迎晨為求表演真,語氣都是糯糯的。
借酒壯了膽,人往上挪了些,似有似無地住了厲坤脖子上的皮。
一剎那的溫熱如電流過境。
厲坤手握拳,心猿意馬了幾秒,他恢復鎮定,說:
“松手。”
沒靜。
“我讓你松手。”
沒聽見。
“別后悔。”
不后悔。
下一秒,厲坤語氣平靜,告訴:“我肩膀上有只蝗蟲。”
迎晨懵了片刻,反應過來后——
“啊啊啊!!”
人跟詐尸似的瞬間滿復活,方向辨認清晰,助跑速度過,從厲坤上跳下來,尖跑遠。
等意識到自己出馬腳時,已經晚了。
厲坤雙手搭在腰上,閑散懶洋,好整以暇地著。
迎晨心里一落,糟糕,中計!
厲坤無神無,后是漫天黑夜。
迎晨表垮臺,這回是真頭暈,蹲在地上,仰著頭可憐。
對視之間,安靜得只有飛蟲偶爾竄過。
迎晨眸子水潤,喝了酒的緣故,臉也紅一片。微張,沖厲坤眨了眨眼。
厲坤看了許久,終于邁步走近。
迎晨頭仰得更高,跟個犯了錯的小孩兒一樣。
厲坤蹲下來,從齒間出五個字,低低道:“長能耐了,嗯?”
猜你喜歡
-
完結21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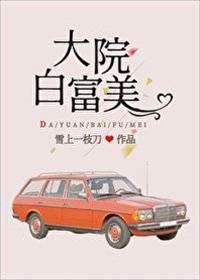
七零大院白富美
別名:大院白富美 肖姍是真正的天之驕女。 爸爸是少將,媽媽是院長,大哥是法官,二哥是醫生,姐姐是科學家。 可惜,任性的她在婚姻上吃了虧,還不止一次。 二十二歲時,她嫁給了識于少時的初戀,可惜對方是個不折不扣的渣男,兩年后離婚。 但她并沒為此氣餒,覺得結婚這事兒,一次就美滿的也不太多。 二十六歲再婚,一年後離婚。 三十二歲三婚,閃婚閃離。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集齊了極品婆婆,極品小姑子,極品公公之後,她終於遇上了最適合的人。 三十五歲肖姍四婚,嫁給了最後一任丈夫趙明山,二人一見鍾情,琴瑟和鳴,恩愛一秀就是幾十年。 重生後,她麻溜的繞過一,二,三任前夫,直接走到趙明山的面前,用熱辣辣的目光看著他, “哎,你什麼時候娶我啊?” 趙明山一愣,肩上的貨箱差點砸到腳了。
97萬字8 12440 -
完結673 章

你是我的情深似海
【重生+虐渣打臉】顏安洛把陸霆昊放在心尖上十年,卻到死都沒有得到過他的心。重活一世,她表示什麼狗男人,通通給姐滾遠點。她只想暴富!一份離婚協議甩過去。“離婚吧,我要回家繼承家業了!”某人卻紅了眼,一把撕了離婚協議。“要離婚,除非我死!”
120.3萬字8 126233 -
連載352 章

豪門後媽在娃綜爆紅了
【1V1,雙潔】 楚虞穿書了,成了豪門後媽帶娃綜藝文裡的惡毒後媽。 女主是善良賢惠,將繼子視如己出的好後媽,而女配則是打罵繼子,虐待繼子的惡毒後媽。 兩人一同參加了帶娃綜藝,女配成爲女主的對照組,被全網diss,最後的下場悽慘。 楚虞穿來後,直接躺平擺爛! 是無限黑卡不香?還是逛街買買買不香? 還有那個便宜繼子,軟萌可愛的,擼起來手感那叫一個好。 於是…… 楚虞憑藉著自己的“自身魅力”,成了娃綜裡的一股清流。 #新式帶娃#、#羨慕楚虞#、#我那生活不能自理的後媽#…… 楚虞成功靠躺平擺爛爆紅全網! ————
65.3萬字8 16103 -
連載1426 章

離婚后,夫人她走上人生巔峰
結婚三年後,傅臣璽的白月光回國,舒漾也收到了深愛三年男人的離婚協議書。 民政局門口,傅臣璽對着白月光深情告白:三年了,我從來沒碰過她,我只愛你舒漾徹底心死,只當三年感情餵了狗,轉身重拾舊業,賺錢走向人生巔峯人們這才知道,被拋棄的傅太太人美有錢,真人類高質量女性三個月後的深夜,傅臣璽紅着眼給她打了電話:“漾漾,我後悔了……”電話只傳來女人帶着倦意的嘟噥:“容煜,誰啊……”某個抱得美人歸的男人笑着掛斷電話,親了親懷裏的人:“沒誰,搞傳銷的。”
248.5萬字8 9554 -
完結221 章

溺養嬌臠
[高門矜貴子弟vs江南清冷美人] 老干部x小嬌妻;[女主絕色,先弱后強+男主忠犬,跌下神壇卑微求愛][真人講書可同步聽] 遇見她,他開始學著愛。成熟濃烈的愛,治愈她的創傷,溫暖她的一生。 南城“白月光”虞晚晚,被養父母送給神秘大佬謝廳南,成了他的掌心嬌寵。 人人都覺得虞晚晚早晚被厭棄,她自己也明白,早晚要離開。 *** 金字塔尖的謝廳南,從不相信誰能把他拿捏。 或許,他以為,那個嬌滴滴的小雀兒,翅膀早斷了。 *** 在謝廳南和第一名媛訂婚的當日,懷了孕的虞晚晚,一個人,開車到了無人區,徹底消失了…… 訂婚儀式進行時,衣冠楚楚的男人接了個電話,眾目睽睽下,扔掉訂婚戒指,慌亂離開…… *** 莊嚴寶地,青燈如豆,容顏傾世的女子遠離紅塵…… 有人藏地探險,遇到一神明般矜貴出塵的男子,遙望一地,三步一叩首,虔誠焚香。 像極了失蹤已久的謝廳南。 他說:“小夫人鬧情緒呢。我會拜到她回心轉意,帶她回家……” *** 排雷:1.年齡差10。遇到女主后男德歸位,化身忠犬。 2.副cp:老干部vs女明星;高門少爺vs名門千金 3·非典型追妻火葬場:男主不渣,標準忠犬,不是戀愛腦。 4。現實流,很現
37.6萬字8 368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