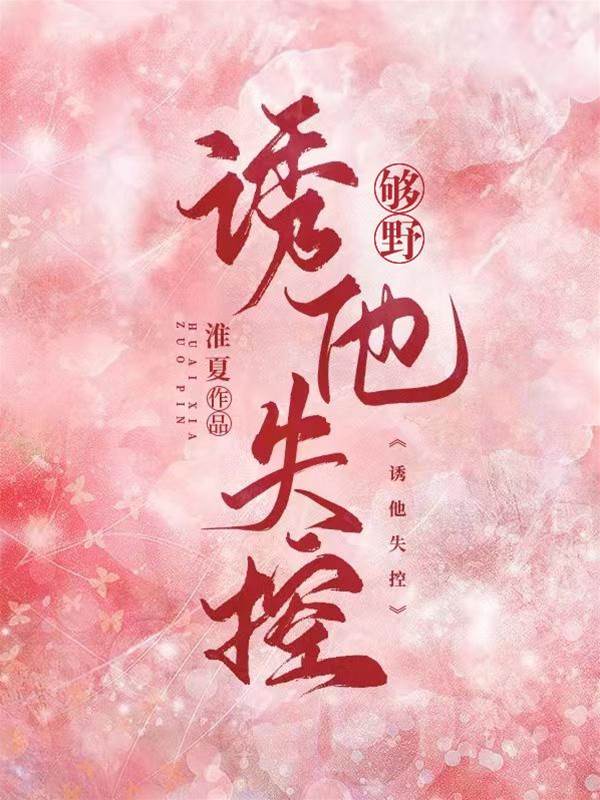《蜂蜜口味的故事》 第8章 要表白【一更】
兩個人面對面站在車邊吹著冷風。
“提醒你了有沙塵暴。”大概因為戈壁灘旁這呼嘯的風,陸初的聲線聽起來更低沉了些。
“是啊,所以我特意看了天氣預報。”只是天氣預報——
陸初發出了聲“嗯”,似乎并沒有在意的回答。他轉了,抬手指揮剛跳下車的特戰隊員把李姐一家帶到最后面的車上去。
因為總是奇怪地面,他果然覺得麻煩了,晏回溫沮喪地想。
于是,還是小小地補充了一下:“可天氣預報說,明天有沙塵暴……不是,已經今天了,是今天才有沙塵暴。”
陸初偏頭一指;“上車。”
晏回溫接著舉手把上,趕點頭追去李姐后。結果剛松了口氣,特戰隊員一按車門把手,最后面那輛車的車門唰地開。
李姐一家三口先坐進去,加上原本在里面的隊員,剛剛好沒有了的位置。
幾雙眼睛同時看向,晏回溫揮手跟大家打過招呼后,大腦才非常緩慢地繞過幾了個彎,然后轉頭十分小心謹慎地問陸初:“那麼……我坐哪兒合適?”
隔得遠,風又大,瞇眼也沒分辨出陸初的臉,就見他好像跟他自己那輛車里的人擺了擺手,又代了句什麼,最后對招招手。
晏回溫一路小跑過去,跑得直氣,扶著他的車,這是一輛作戰指揮車。
“方便嗎?”問。
陸初好像在趕時間,敲敲車門讓趕上車,如果不上的話:“小姑娘,后面還有一輛裝彈藥的車可以坐。”
晏回溫睜大眼睛投降,扭頭就手腳并用地爬上了這輛底盤略高的車。陸初砰一下上車門,震得脊背一直,接著他徑直繞去了另一邊的副駕駛室,示意隊員開車。
Advertisement
隊員一腳油門踩下去,晏回溫連忙摳座椅,要飛了嗎?
這輛指揮車里,除了電臺和各種觀察儀,還坐著另外3個隊員,都是中尉軍。
最前面離陸初最近的人筆直靠坐著,他正背對晏回溫,低頭笑著看手里的,青梅竹馬的朋友給他拍的異國風。
在哪兒跟朋友求婚比較好呢?林在言愉快地琢磨著。
后面,晏回溫好不容易坐穩,林在言正好收起東西,回頭跟熱地打了個招呼。這一聲招呼,驚得晏回溫差點沒訝出聲。
他是上次跟陸初在一起的人。
他手里的東西……咦,好漂亮的孩,他摟著的肩膀……
等等!
所以說,這個隊員有朋友。
那麼相親那天,就絕對誤會了!晏回溫趕低下頭去,有些懊惱地摳著手指。
在接下來的幾分鐘里,不斷自我檢討:就是,一開始……就特別喜歡陸初,本來都好命地去跟他相親了,但相親之后誰知出了點小意外,開始犯小愚蠢,后來的面就都搞砸了。
所以,回去跟他表白吧?
……
打完招呼的林在言看著晏回溫彩的表,又去打量陸初,發覺隊長正研究一張地圖出神,毫沒有理會后面的意思。
這倆人搞什麼啊?
他笑瞇瞇對著晏回溫;“嫂子。”
“嗯……”在完善自己計劃的晏回溫鬼使神差地接了話。震驚兩秒之后,清醒過來了,什麼?!剛才干了什麼?
陸初的視線從地圖上收回來,回頭掃了他們一眼。
這一眼,非常嚴肅。
“我不是故意的……我也不知道,不知道怎麼回事……”晏回溫驚慌失措地試圖解釋,“對不起……”
“你被占便宜了。”沒想到陸初出聲打斷。
Advertisement
“……”
沒有啊,覺得是自己賺了才對。
不過這樣一來,犯錯誤的晏回溫都沒敢再直視陸初板起來的臉,只瞄過去,他今天好像沒太有緒說話?
靠在椅背上的陸初又在腦海里過了一遍新隊員的各項數據,他不太滿意地闔上眼睛。
從這次新兵冬訓的結果上來看,雖然隔壁三中隊略差一些,要被上頭“發配”出去勞。但一想到自己手底下同樣是不省心的——
陸初活了一下脖頸,他也準備打個報告上去,兩隊一起“發配”出去算了。
地點的話,他回去跟三中隊長商量。
林在言顯然沒有意識到他的隊長在計劃什麼,就見剛才自己挑起的風頭過去了,回頭笑呵呵地繼續問晏回溫:“聽說你是漫畫家?”
看一眼陸初,點點頭。
“畫的是什麼啊?是那種很象的靈魂嗎?”他還是好奇。
“那倒不是。”晏回溫想了想,手從小背包里很快出一張草稿,遞給他看,“這是兩只狗,它們是書里的主人公……其實簡單點說,就是旅途的一些小悟。”
林在言掙扎了一番:“這是狗?”明明就是兩條,兩只手,西裝革履和穿小子的……片刻,他放棄滿腦子搜刮措辭來描述這兩位主人公了。
于是,林在言話到邊另外拐了個彎,開起玩笑來:“是不是畫的你跟隊長啊?不過我們隊長可是最喜歡穿迷彩服的哦!”
這回,晏回溫學乖了,立馬搖頭否定:“啊,不是,絕對不是。”
林在言呵呵一笑:“別張啊。”
被破心思的:……
陸初剛好在這時抬起了頭,眼睛漫不經心轉到了這張畫上。他的目頓了頓,又挪到晏回溫那張白里的臉上去了。
Advertisement
經過對比,他發現,都是孩子氣的屬。
正要轉回去,他的視線里,晏回溫的那雙眼睛在小小的期待著……然后,陸初就用下指了指畫,說出了目前腦海里唯一能尋思出的評價:“配不錯,很暖和。”
晏回溫睜著大眼睛,想說什麼都給忘了。
就看見他靠回椅背,拿起地圖,沉思。這才回神,小聲地,試探說:“如果你覺得好看,我也可以另外畫穿迷彩服的給你啊。”
“……”
終于,斜后方忍不住發出一聲輕笑,那笑聲溫潤平靜:“那你會攝影嗎?我看見你有整套的攝影材。”
咦?這人這麼溫和,他也是特戰隊員嗎?晏回溫轉頭面對過去,正張口答。
沒想到林在言一拍那人肩膀搶先給介紹道:“江洲,我生死搭檔,人超級溫。對了,他想學攝影是給未婚妻拍照。”
“你好。”江洲微笑。
晏回溫趕接話:“啊你好你好。”
“能把你這些材的型號告訴我嗎?”江洲仍微笑問。
“當然可以的,你等一下啊。”點著下,接著就要從背包里找紙,型號很長,材很多,得寫下來才行。
但江洲笑笑說不用,他用食指敲了敲額角。晏回溫頓悟,記這些對于他們來說太簡單了,不需要“用筆記”這種多此一舉的行為。
認真回憶,一字一句慢慢報出一大串字母跟數字。
“在哪可以買齊?”江洲從小在南邊長大,也是進了特戰隊才正式落腳北方。除了外出任務,他離開特戰基地的次數一只手就可以數過來。
晏回溫更認真想了想,給他挑了最大那家材城的地址。
江洲記下來,接著,他比較可憐地問前面;“隊長,放我假吧。”不過他的臉太溫了,可憐的效果不大。
Advertisement
“沒假。”陸初忙得眼睛都不抬,干凈利落地拋給他倆字。
“隊長!”江洲再請求,“要給未婚妻拍照呢。”
“別隊長。”陸初回頭,“什麼都沒用。”市里馬上要開大會,這假就算他給批,上面支隊長也批不了。
晏回溫的目在兩個人上來回飄過兩次,覺得陸初這個隊長當得實在太招恨,太不容易了。
權衡了一下,然后跟他們隔著兩個座椅,在一邊小聲:“不然……我幫你去買,買完了給你送進去,這樣行嗎?”
江洲雙手合十,萬分激。
突然。
前面的陸初頓了頓,打量了一下因為太輕,都坐不太穩的晏回溫:“我們開車都比較快,趕時間,你……”
老實說,晏回溫快要被甩吐了。
著陸初連忙擺手:“啊沒事,你們開,我能坐。”
……
一路狂飆,終于,他們在規定時間趕到了這個市的武警總隊。
陸初推開車門,跳下車時問晏回溫:“酒店在哪兒?”他招呼了個隊員過來,拋給他另外一串車鑰匙,讓他送去。
晏回溫自己訂下的酒店已經過期了,還沒有預定新的,于是先搖了搖頭。
正想說先預定,手機都點開了。沒想到陸初過來,一只手拎起的小箱子先一步走了出去:“算了,就隔壁武警招待所吧。”
晏回溫摘下羽絨服的大帽子,抬頭一看。眼前就是招待所低調的大招牌,簡直離他暫時落腳的這個總隊太近了。
一陣歡天喜地,雙手背到后面,按著后背的小背包立馬追上去。兩個人上了臺階,進了招待所,只不過,陸初并沒有空招待,他放下東西就直接走了。
安靜的房間里,晏回溫坐在窗戶前訂機票。
一抬眼,忽然驚喜發現,從這個角度往外時,剛好能看見總隊里的大場。場中央停著幾架帥氣的直升飛機,猜想,這是送陸初他們回去的。
晏回溫托腮看了會兒后,搬來工開始畫畫,畫的是想表白的一些東西。
后來,每天都在忙這件事。
等大作完,晏回溫將所有畫紙都擺在慵懶的下,傻乎乎笑了好久,然后把它們裝做了冊。這時都已經過了正月,一連張好幾天,終于臉,歡快地找陸初表白去了。
作者有話要說: 一更,二更馬上來~
別忘了吱吱——再翻看~
猜你喜歡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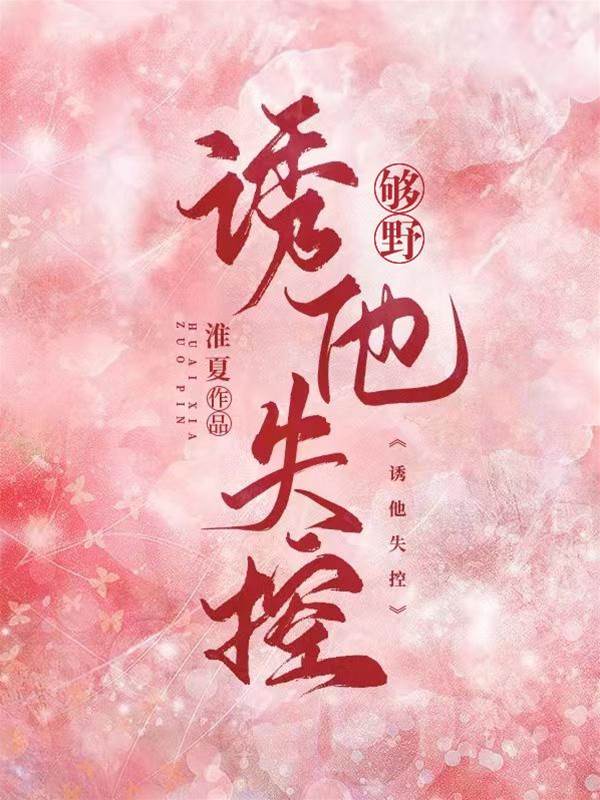
夠野,誘他失控
(雙潔 先婚後愛 雙京圈 甜寵丨律師x旗袍美人)圍脖:是淮夏呀(溫喬番外更新中)京圈太子爺楚雋,薄情矜貴,寡欲清冷。京圈大小姐薑晚寧,人間尤物,明豔張揚,驕縱紈絝。互為死對頭的兩人,突然閃婚,眾人大跌眼鏡。-婚後,楚雋發來消息:“在幹嘛?”薑晚寧:“怎麼啦?親愛的,在家,準備睡覺了,你呢?”楚雋:“我在你左後方的卡座,過來跟老子碰一杯。”眾人了然,表麵夫妻,各玩各的。太子爺的追求者們翹首等著兩人離婚,卻隻等到神明一樣的男人為愛瘋批。薑晚寧要離婚,楚雋咬著煙頭,語氣森然:“薑晚寧,你要是情願,我們就是雙向奔赴。”“你要是不情願,我不介意強取豪奪。”#男主假破產
19.5萬字8 15071 -
完結125 章

難以招架,裴總每天都想強取豪奪
【1V1 雙潔 強取豪奪 強製愛 男主白切黑 天生壞種 追妻火葬場】裴晏之是裴家的繼承人,容貌優越,家世極好,外表溫潤如玉,光風霽月,實則偽善涼薄,是個不折不扣的壞種。他從小就感受不到所謂的感情,不會哭不會笑,就連這條命都是拽斷了一母同胞哥哥的臍帶才留下來。裴家人都說他是沒有感情的瘋子,因此把人送到道觀養了十多年。直到他18歲那年斬獲大獎無數,才被裴家人歡天喜地接回來。都以為他會改邪歸正,殊不知,惡魔最會偽裝。*江予棠自幼性格木訥,沉默寡言,是放在人群裏一眼看不到的存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當了裴晏之的私人醫生。都說裴晏之性格溫柔,教養極好。江予棠對此深信不疑。直到兩人交往過程中,他步步緊逼,讓人退無可退。江予棠含淚提了分手。可招惹了惡魔,哪有全身而退的道理。往日裏溫潤如玉的男人像是被惡魔附體,對她緊追不舍,把人壓在牆上,語氣又壞又惡劣,“你要和我分手?換個男朋友……”後來的後來,男人抓著她的手,小心翼翼貼在臉上,嗓音裏滿是祈求,“棠棠今天能不能親一下?”從此以後,上位者為愛強取豪奪,搖尾乞憐。【沉默寡言醫學天才女主X表麵溫潤如玉實則陰暗瘋批偽善涼薄男主】
22.6萬字8.18 17507 -
完結377 章

怪他人設太迷人
九年前,他們勝似親密無間的姐弟;兩年前,他們是如膠似漆的戀人;現在,他們是背負恨意的冤家。陳玨怎麼也沒想到,少年時期那個陽光明媚的陳又時,如今為了得到她用盡了卑劣手段。“姐姐,你還跑嗎?
68.5萬字8 673 -
完結229 章

一見鐘情,傅少為她折腰
北城豪門世家傅辰笙權勢滔天霸總*京大外語學院大三女學生沈漓 直至遇見沈漓,傅辰笙纔開始心生悸動,高嶺之花就此跌下神壇。 (主線就是很甜的甜寵) ——— “夭夭別動。” “阿笙~,我疼。” 傅辰笙將她緊緊抱住,“對不起,夭夭,還是傷到了你。” “我受傷了嗎?” 她剛纔翻身覺得**是有些疼痛。 “嗯,乖寶有些撕裂,我已經給你上過藥了。” “上藥?你?阿笙?” 沈漓有些難以置信,她愣住,沉默半晌。 “你怎麼給我上的藥?” 傅辰笙平淡的訴說着事實…… 他溫朗一笑,將她的小腦袋按進懷裏,溫柔的摸了摸她的後腦勺。 “我哪裏沒看過。”
36萬字8.18 9489 -
連載559 章

被趕出家門,葉小姐靠醫術嘎嘎亂殺
被趕出家門,她搖身一變成為首富千金。弟弟冷眼,媽媽偏心,妹妹陷害? 不足為懼,且看她如何憑借逆天醫術征服所有人! 她畢生夢想就是做個好醫生,治病救人。 誰知一不小心成了高考狀元,醫學大咖們爭奪的頂級人才。 隨手救下的老人竟是大佬的奶奶,自此之后,大佬追著報恩。 葉錦沫不勝其煩:“我們已經退婚了,離我遠一點!” 季少委屈:“老婆,我重新追你好不好?” 要問季少最后悔的事,莫過于連面都沒見就和親親老婆退婚。
96.1萬字8 1858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