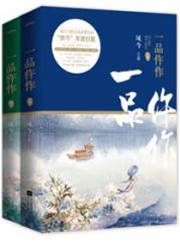《閨中記》 第39章
詩云: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里不知是客,一晌貪歡。
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話說云鬟為避開程曉晴,在外閑游之時,忽地來了一場急雨,因心念一事,便急匆匆冒雨跑回書房里來。
誰知才進了房門,抬頭之時,卻驚見一人坐在對面,雖年弱,然卻已有別樣氣勢,這抬眸一瞥間,額角的發被風輕輕一,晃過那不笑的微涼眸子,直看的人的心也忍不住有一寒意陡然掠過。
此刻門外仍是雨聲喧囂,嘩啦啦地一片,仿佛傾倒天河一般。
云鬟雖站在門,卻仍猶如人在雨中,通冰涼,而滿心滿耳都是吵雜慌的雨聲。
猝不及防間,兩個人目相對,趙六盯了片刻,忽地一笑道:“你是怎麼了?難道也沒有把傘不?跟著你的丫頭呢?如何也不理你?淋的這落湯似的可憐模樣兒……”他說著,便站起來,走到云鬟跟前兒,上上下下打量。
云鬟轉頭看他:“……六爺,怎麼在這兒呢?”
趙六見頭發嗒嗒地,小小地發髻像是被雨打歪了的菡萏,也隨著向著旁邊地傾斜,發卻在臉上,卻越發顯得眉眼清晰,雙眸更是清清若許,只可憐的,發跟裳上都滴著水,加上人小,越發惹人憐惜了。
趙六手過去,便握住云鬟裳一角,竟輕輕用力一擰,雨水隨著作,嘩啦流了一地。
云鬟尚未反應過來,見他如此作,整個人有些呆了,趙六已經圍著轉了一圈兒,嘖嘖了兩聲,從懷中掏出一塊汗斤,不由分說又向臉上。
云鬟忙后退一步,皺眉看他。
Advertisement
趙六“噗”地一笑:“我有事打外頭過,忽然見來了雨,便進來避一避,怎麼,你不喜六爺過來?”
云鬟道:“如何在這書房?”因見屋并無別人,心中自然疑,陳叔不至于隨意把人請來此,縱然請來,也該有個陪侍才是……
果然趙六說道:“你那陳管家讓我在廳上等候,我不耐煩,就隨意進來瞧瞧看……無意就來到這兒,這是你的書房?你小小個人兒,只認得兩個字倒也罷了,難道當真已經博覽群書了不?”
云鬟聽他說著,心頭刺刺撓撓地,忽然一念意,想到先前惦記的那事,便顧不得理會趙六,只忙跑到書桌邊兒上。
卻見筆架之后,挨著窗邊兒,整齊地放著一疊書,此刻風裹著雨,自檐下侵襲過來,上頭的一本書的書皮已經沾了幾滴雨點,微微潤了。
云鬟忙翻了一翻,卻見底下擱著本青書的書,倒是并沒沾著雨,略松了口氣,才要出來,忽然回頭看向趙六,卻見趙六果然正在背后著,雙眼著一說不出的奇怪之。
云鬟便撒手不去那書,只踮起腳尖,想把窗戶掩上,因一只手還吊著,量又矮,竟十分吃力,手指勾了勾,也不到窗扇。
趙六在后見探頭踮腳的,這般不易,不由失笑。
他竟走到跟前兒,于后探臂出去,輕易將兩扇窗戶掩了起來,因低頭,卻見云鬟在他前兒,似被他攏住了一般,正有些意外而驚恐地瞪著他,兩只眼睛便極圓的。
趙六便垂眸道:“做什麼?好沒禮貌,也不謝六爺一聲兒?”拍拍手,自顧自轉,目向桌上的書,便又問:“這些莫非都是你看過的?讓六爺瞧瞧都有什麼……”說著,便手要去擺弄。
Advertisement
云鬟忙抬手,竟推到趙六腰間,因仰頭看著他,說道:“六爺,你擅自闖到別人書房,已經是不妥當了,如何還要翻別人的東西?是何道理?”
趙六見雖是淋淋地,可卻這般義正詞嚴,竟忍不住又笑起來,把手上原先給雨的汗斤兜頭蓋下,便遮住了云鬟的頭臉。
云鬟只瞧見他莫名一笑,然后眼前發黑,一呆之下,忙舉手把那汗斤子扯下來,只鼻端嗅到一異樣氣息——必是被他帶在上或者用過之故,云鬟一愣,繼而怒道:“你做什麼?”
趙六見小臉猛然漲得通紅,便笑道:“你急急的回來是為了什麼,總不是因為聽說六爺來了,所以忙著回來見我……寧肯淋雨麼?”
先前他不期然闖進的書房,又拿汗斤子“手腳”,又來關窗把攔在里頭……如今又要翻自己的書,且帕子蓋臉這樣無禮,云鬟又驚又怒,又聽了這樣嘔心的話,越發氣急敗壞,當下便把那汗斤用力扔向他上:“趙六爺該走了!這兒不是你該呆的地方。”
趙六舉手將帕子兜住,竟在手中,忽然若有所思說道:“小丫頭,你為何……總敵視六爺一般?”
此刻因窗戶關上,室越發暗,他的臉暗暗淡淡地在地影子里,勾起云鬟各心病,起初因驚怒加,忘了別的,如今才想起來,當下也不回答,只疾步走到門口,大聲道:“來人,來人!”
然而此刻雨大,聲音傳雨中,卻又被鋪天蓋地的雨水了下去,云鬟了兩聲,不見人來。
后,趙六著的背影,忽然無奈地嘆了聲,說道:“六爺好歹也算是救過你命的,何至于一見到就這般,跟避貓鼠似的?”
Advertisement
云鬟只不去理會,目一,卻見廊下,是珠兒跟程曉晴兩個一前一后出來。
云鬟莫名松了口氣,而那兩個丫頭正說笑著,程曉晴先看見在此,當下對珠兒說了一句什麼,兩個人才忙斂了笑,飛快地來到此。
云鬟見曉晴手中拖著一個茶盤,里頭是一盞茶,便喝道:“你們都去哪里了?如何也沒有個人在這兒看著,若是給些閑雜人等進來胡鬧……可如何是好?”
珠兒跟程曉晴面面相覷,見疾言厲,都不知是怎麼了,珠兒怯生生道:“是陳叔吩咐說……小六爺來了,讓我們好生招呼,不可怠慢……”
此刻趙六已經走到門口,云鬟見他靠近,忙又退開一步,冷冷覷他。
趙六同目一對便道:“人兒不大,脾氣倒是不小,還會指桑罵槐呢?——你這地方難道有稀世的寶貝不?當六爺稀罕在麼?六爺這會兒就走,用不著你這小丫頭來揮三喝四!以后都再也不來了!”
趙六說著,便翻了個白眼,邁步出門。
此刻珠兒跟程曉晴正站在門口,曉晴正端著托盤,聽趙六怒,又見他出來,因惴惴地喚了聲:“六爺……”
趙六看也不看,只喝道:“滾!”竟自一拂手,只聽得“嘩啦”一聲。
珠兒跟程曉晴雙雙驚呼起來,原來是趙六這一揮間,竟把那托盤打翻了,茶盞在程曉晴上一,旋即落在地上,跌得碎。
可趙六視若無睹,冷哼一聲,頭也不回地竟走了!
珠兒嚇了一跳,忙握住程曉晴的手:“你怎麼樣,燙傷了不曾?”
程曉晴搖頭,云鬟大為意外之余,幾乎氣怔,趙六如此囂張,果然是“江山易改稟難移”,跟趙黼如出一轍,邁步出來,待要說兩句什麼,然而他已經去了。
Advertisement
云鬟只搖搖頭,心中道:“果然是他!這不如意便不管不顧發作起來的子……”咬了咬,磨了磨牙,卻終究不曾出口。
云鬟轉頭,見程曉晴跟珠兒站在一,都有些不知所措,云鬟便看曉晴:“可燙傷了?”
曉晴忙搖頭:“姑娘放心,好端端的。”
云鬟見半邊子被茶水了,便道:“你如何卻來送茶呢?”
曉晴十分不安,小聲說道:“我因無事,便陪著珠兒姐姐走一趟……不想竟怒了六爺……姑娘,我可是給你惹事了?”
云鬟皺眉:“不必理會此人。”又珠兒帶曉晴下去收拾。
此后,云鬟喚了陳叔來,問起今日之事,果然如趙六所說,他乃是來避雨的,當時偏云鬟為避開程曉晴躲到了偏院,故而珠兒等都沒找見。
云鬟聽了便道:“此人份雖然特殊,然而我們是安分守己的人家,跟他們軍中更是井水不犯河水,陳叔你大可不必如斯敬畏他們,他以后不來則罷,若還是來,萬萬不能由得他四走,也只以禮招呼罷了,很不必過于厚待。”
陳叔忐忑地答應了,白日趙六來時,陳叔的確是“如臨大敵”,因他知道這年份是極不同的,又是軍中的人,上回因王典之事又且看過他的手段,故而敬畏有加,果然如云鬟所說,半點兒也不敢怠慢如今聽了云鬟這般說,陳叔心想:“雖我們安分守己,但行伍出,做的人,若真的有些不良之意,我們又如何應付?且這小六爺看著也不像是壞的,手段又高,本也可算個靠山,只可惜小主子跟六爺脾氣不對,唉,只盼以后這位神來我們莊上,兩下相安就是了。”
不多時,程曉晴便來告辭,云鬟只讓珠兒送。
這一場雨到了晚間才淅淅瀝瀝停了,空氣里的燠熱倒是散了些。
夜間,云鬟洗漱了,正安寢,珠兒因拿了一雙繡花鞋出來,便對云鬟道:“姑娘你看,這繡的可好不好?”
云鬟接了過來,見淺綠的緞子鞋面上,繡的是鵝黃的報春花,小花簇簇,針線致的很,著實惹人喜歡。
云鬟翻來覆去看了會子,看這尺寸是給自個兒的,便道:“是你做的?只有些太鮮艷了。”
珠兒笑道:“我的針線哪里有這樣好?是曉晴做的,這也并不鮮艷,知道姑娘的心,知道你不喜歡那些大紅大綠的,特特給你選的呢。”
云鬟白日雖聽聞兩人說起,卻只以為是納了鞋底子,不料竟是如此……因慢慢放下,道:“倒是有心了。”
珠兒笑道:“的確是能干,要不怎麼那胡家這般喜歡呢?我瞧氣比先前來咱們莊的時候都好多了……”
云鬟點了點頭,不置可否,只珠兒把鞋收起來。
珠兒將鞋放進柜子里,見云鬟對燈出神,正出去,云鬟忽地問道:“白日我不在的時候,趙六爺來,可知道他在書房呆了多早晚兒?”
珠兒想了想,道:“也并沒多久,陳叔我去廳中送茶的時候,因不見了人,我便一路找去,那時候六爺還在廊下,并沒進書房呢……他還好言好語地跟我說話呢。”
云鬟轉頭看:“說什麼了?”
珠兒笑道:“也并沒別的,只問我這莊子多大,平日可還安靜等話,又問我們跟著姑娘多久了……”
云鬟不做聲,眼前卻想起趙六在書房那一場晴不定,以及他臨去掀翻茶盤……
珠兒見不言語,便又道:“我說了林嬤嬤是跟著京來的,我跟陳叔是在謝家跟著夫人的,他又問曉晴姐姐……”
云鬟正出神,聞言方回頭:“問?”
珠兒以為不喜,本正要停下,見問起來,才大膽道:“多半是見我沒提曉晴姐姐,故而六爺問是不是也是謝家跟著的,我就說曉晴姐姐是前兒日子才來的,就是在那賊人過來行兇的前一天……然后就沒話了。”
云鬟微皺眉頭,最終卻只一揮手:“你去睡罷。”
又過了兩日,云鬟的手已漸漸能放下來,因拘束了幾日,林嬤嬤自覺有些不過意,正又趕上七月十三鄜州城大集,當下一大早兒,便小廝備車,帶著云鬟進城玩耍。
沿街逛了會子,見那些琳瑯滿目的雜貨,林嬤嬤自是喜不自,又跟珠兒買了好些用著用不著之,兩個人都是歡歡喜喜。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