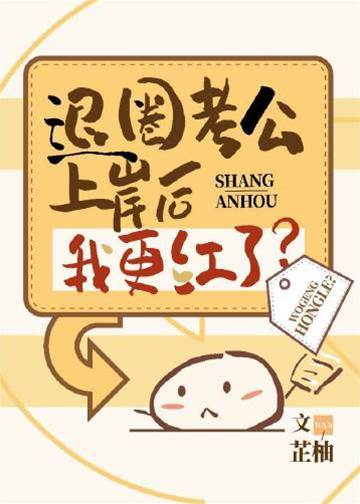《一路高升》 第六十八章 與女特工一席談
進了昆明城,大家要去的地方不在一個方向,有的要立刻回部隊,有的還想再玩一陣子,於是乎就各自找合適的公共汽車坐車走了。
上次背珍珍的黑鍋的時候,吳放歌曾經在昆明玩兒過好幾天,現在也實在沒什麼去,但是又暫時還不想回去,於是就在大街上瞎逛,一直逛到中午,才找了家小店要了份抄洱吃。原本洱味道不錯,可是臨近一家服裝店總是在那兒哼哼唧唧放遲志強的“囚歌”,真是越聽越生氣。其實要按20年後的觀念,小遲那點事兒真的不算啥,確實有點冤,可是一想到邊那些戰友年紀輕輕二十郎當什麼還沒就非死即殘,再聽著他們抱怨‘菜裡沒有一滴油’,心裡就覺得彆扭,這心裡一別扭了,原本味道不錯的洱也似乎變了味道。
正和隔壁的錄音機鬱悶吶,門口又來客人。
“老闆,來碗米線。”是個客,一口地道的雲南文山口音。
吳放歌下意識地一擡頭,一下子愣住了。那人著個大肚子,說也有五六個月了,材瘦小,面目清秀,眼神亮,神形疲憊,這……這不是過幾次手的那個越南特工嘛?
那個特工同時也認出了吳放歌,也愣住了,兩人就這麼對視著。
吳放歌腦袋裡面的:這傢伙怎麼在這兒出現了?這裡是昆明,又不是河,在這兒幹什麼?有沒有同夥兒?難道也要學我們來個深敵後?可我們也沒深這麼多啊,他小越南就行?
特工也瞪著吳放歌看,雙手平放在桌子上,看那架勢只要吳放歌一就準備逃之夭夭。
吳放歌一看這樣兒,心裡稍安,這種表現如果不是敵的話,那就是真的沒有同伴,或者同伴不在附近。
Advertisement
正在兩**眼瞪小眼互看的時候,服務員端了米線過來,那特工深知人是鐵飯是鋼的道理,雖然眼睛盯著吳放歌,卻拿了筷子,一口一口不不慢的吃,吳放歌也隨之有一筷子沒一筷子的挑面前盤子裡的洱,這麼一來,隔壁小店裡的囚歌就變得無關要了。
特工吃完了米線,算完帳後就走了,吳放歌也趕結賬,然後跟在後面。兩人一前一後間隔也就只有七八步,雖然時快時慢,卻總保持著這個距離,就這麼足足走了半個多小時,特工看來實在是累了,就在工人文化宮廣場上找了空長凳坐下了,吳放歌略想了一下,也走過去挨著坐下了。
特工突然笑了一下說:“你老跟著我幹嘛?追孩子不是這樣的。”
吳放歌說:“跟著你是因爲我們都是軍人,而且是敵對方的。而且我再變態也不會追一個大肚子的。”
特工被吳放歌毫不客氣地這句話說的臉不好看,於是說:“那你幹嘛不抓我?我現在孤立無援,你要手,我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兒。”
吳放歌說:“周圍老百姓太多,我怕殃及池魚。這場戰爭已經死了很多的人了,最好別再有不必要的殺戮了。”
特工輕輕著自己的肚子說:“我都這樣兒了,還能給誰造威脅?”
吳放歌微微一笑:“第一次見面你就對我說你懷孕了,結果第二次還不是提著槍把我攆的滿山跑?所以呀,誰知道你那裡頭不是個大炸彈?”
特工也笑著說:“你猜對了,我這確實是個炸彈,只不過除了我以外,不會給其他人造任何麻煩。”
當特工說自己的肚子確實是個炸彈的時候,還真把吳放歌嚇了一跳,可說到後面又讓他有了些許的慨:“你們吶也真是,居然讓孕婦執行那麼危險的任務……還有你老實說,你這次潛到昆明來幹什麼?”
Advertisement
特工聽罷,嘆了一口氣,幽幽地說:“我要是說了,你信不信?”
吳放歌說:“信不信你都得說,這是給你的機會,也是給我的。”
特工說:“我這次不如侵你們國家,是逃亡。”
吳放歌笑了:“你開什麼玩笑,要不你直接投降吧,我接你的投降,而且你現在這個樣子,也能得到比較好的醫療。”
特工說:“投降後的日子當然比我現在東躲西藏的好嘍,可是戰俘一換我還不是得被送回去?那可就得直接進監獄了。”
吳放歌說:“說說原因吧。”
“因爲就要和平了。”特工說。
關於即將到來的和平,吳放歌是知道的,現在距離北京亞運會不過兩三個月時間,到時候,越南北方軍區司令員武元甲就要坐在貴賓席上看開幕式了,可這和眼前的特工逃往有什麼關係。
特工似乎看穿了吳放歌的想法,就解釋說:“其實我在國……這麼說吧,我父親……職位高的……”
吳放歌笑道:“呦呵,沒看出來你還是**子弟嘛。”
特工一攤手說:“那有什麼用?本來想立點軍功回去就轉職,卻遇到你這個剋星,兩次都落荒而逃……”
吳放歌說:“如果不打仗,我們也許能爲朋友,可是戰爭讓我們沒有選擇,撇開什麼祖國啊,正義什麼的不說,當時我不和你打,我就只有死路一條,爲了保命,我也得和你打。”
特工說:“是啊,我又何嘗不是如此?開始的時候只是想立功,後來就只是想活命了。”
吳放歌又問:“對了,你還沒說,你怎麼又逃往了呢?你父親不是高嗎?”
Advertisement
特工皺眉說:“你別提了,他要不是高我還不至於逃往呢。”說完停頓了一下又說:“他是堅定的主戰派……這次失勢被捕了,還牽連了家人……總之是政治鬥爭的結果,你們不是也有類似的事兒嗎”
吳放歌低頭不語,特工等了半晌還沒聽到他說話,就問:“怎麼?你不相信我?”
吳放歌被這麼一問才說:“不是相信不相信的問題,我只是覺得爲一個不能左右自己命運的士兵真是可悲。歷史將被人銘記,可一個個的犧牲士兵卻爲了一個籠統的數字。你今後打算怎麼辦?”
特工此時心裡才落下一塊石頭,看來這個冤家士兵是不會逮捕或者告發自己了。可雖然鬆了一口氣,但是對未來還是一片茫然,於是又長出了一口氣:“不知道啊,先找個地方把孩子生下來吧,以後……或許去四川吧,聽說那兒是天府之國,要活下來應該沒問題吧。”
吳放歌站了起來,故作輕鬆地拍打著子說:“那好吧,祝你好運,我也該回去了。”
特工依舊坐著,只是仰頭說:“臨走前能不能再幫我一個忙?”
吳放歌擺手說:“你要借錢可不行,我那樣就了資敵了。”
特工笑著說:“你現在罪名也不小了,你放心吧,錢我還有點,只是求你做點別的。”
吳放歌嘆道:“冤孽啊,你說吧,別說我做不到的。”
特工著自己的肚子說:“人的幸福之一就是在懷孕的時候讓丈夫傾聽的胎音,可是……這孩子的父親沒能逃出來……所以……”
吳放歌搖頭說:“不行,我不是孩子的父親。我不能這麼做。”
Advertisement
特工說:“不是因爲這是個越南孩子?”
吳放歌說:“不是,我只是覺得我沒這個權利。”
特工嫣然一笑,說:“算了,這要求確實有點過份,你走吧,我想再坐一會兒。”
吳放歌說了聲:“對不起。”然後扭頭就走,一口氣走出了二三十米才停住腳步,不知怎麼的,他忽然覺得心口作痛,他的腦子裡兩種聲音在激烈的鋒,一個說:你不能把一個弱的孕婦一個人就這麼丟在那兒。另一個說:放歌,現在不是是不是敵人的問題,你幫就等於在害自己。
吳放歌覺得自己的腦袋就要裂開了,再回頭時,看見那個特工正費力地試圖從椅子上站起來,他實在按捺不住了,轉喊了一聲:等一下!然後快步跑回到椅子前,特工等著大眼睛看著他。雖然只有短短二三十米的距離,可吳放歌居然的厲害。
“怎麼?你還是要抓我嗎?”特工說“請不要傷害我的孩子。”
“不……有件事,可能是我現在唯一能爲你做的。”吳放歌說著,單規了下來,然後把自己的耳朵到了隆起的腹部。
“咚……咚……咚……”那就是一個新生命的心跳嗎?雖然有著重生前的人生經驗,這種會卻還是第一回。
特工把手放在吳放歌的頭上,著他的頭髮,淚水卻止不住的流下。在這一瞬間,這對在戰場上的冤家對手爲了彼此生命的依靠,他們不再是敵手,只是普通的男人和人。
古往今來,不知道有多素不相識的士兵,爲彼此國家的利益而相互廝殺著,他們本的意志被政治家的意志所代替,他們不由己,有時候只是爲了能活下去而殺戮,當戰火熄滅,硝煙散盡,倖存士兵們拖著傷殘的軀返回家園的同時,政治家們喝著一樣的紅酒重新分配所謂的國家利益,把酒言歡,大談國家之間的友誼,而士兵則被人忘,這就是他們的宿命。
這一天吳放歌很晚纔回到療養院,沒人知道他一下午都去了哪裡。
猜你喜歡
-
完結875 章

大訟師
杜九言穿越佔了大便宜,不但白得了個兒子,還多了個夫君。夫君太渣,和她搶兒子。她大訟師的名頭不是白得的。「王爺!」杜九言一臉冷漠,「想要兒子,咱們公堂見!」大周第一奇案:名滿天下的大訟師要和位高權重的王爺對簿公堂,爭奪兒子撫養權。三司會審,從無敗績的大訟師不出意料,贏的漂亮。不但得了重奪兒子的撫養權,還附贈王爺的使用權。「出去!」看著某個賴在家中不走的人,杜九言怒,「我不養吃閑飯的。」於是,精兵護崗金山填屋民宅變王府!「出去!」看著某個躺在她床上的人,杜九言大怒,「我不需要暖床。」兒子小劇場:「這位王爺,按照大周律法,麻煩你先在這份文書上簽字。」某位王爺黑臉,咬牙道:「遺囑?」「我娘說了,你女人太多,誰知道還有幾個兒子。空口無憑不作數,白字黑字才可靠。」小劇場:「抬頭三尺有神明,杜九言你顛倒黑白污衊我,一定會受天打雷劈。」被告嚴智怒不可遏。「天打雷劈前,我也要弄死你。」杜九言摔下驚堂木,喝道:「按大周律例,兩罪並罰,即判斬立決!」被告嚴智氣絕而亡。坐堂劉縣令:「……」
223.9萬字8 51694 -
完結8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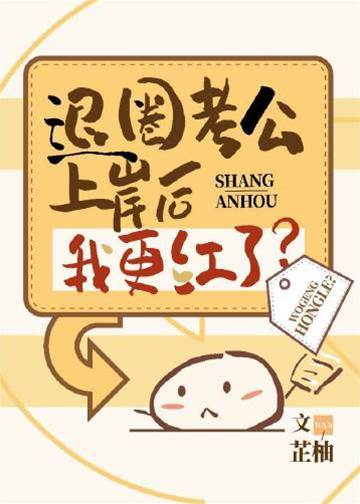
穿成炮灰我退圈上岸了
別名:全網黑后我退圈上岸了 時寧穿書了,穿成和影后女主搶男主的炮灰女配。但凡是炮灰,下場必定凄慘,想到書中人人喊打,出門被扔雞蛋的結局,時寧不由搖頭,退圈,退圈,必須退圈。此時原身父母發來最后通牒,退圈回家考公,成功的話獎勵車房以及恢復零花錢。時寧:還有這種好事?不就…
44.4萬字8 9032 -
連載332 章

機娘紀元:我的機娘都是世界級
機娘紀元:我的機娘都是世界級小說簡介:【單女+主角團】【機娘】【養成】【比賽】【溫馨】【熱血】【不好看吃屎】機娘紀元,這是個機娘能夠幻化成賽車的世界。機娘——外
65.3萬字8.18 25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