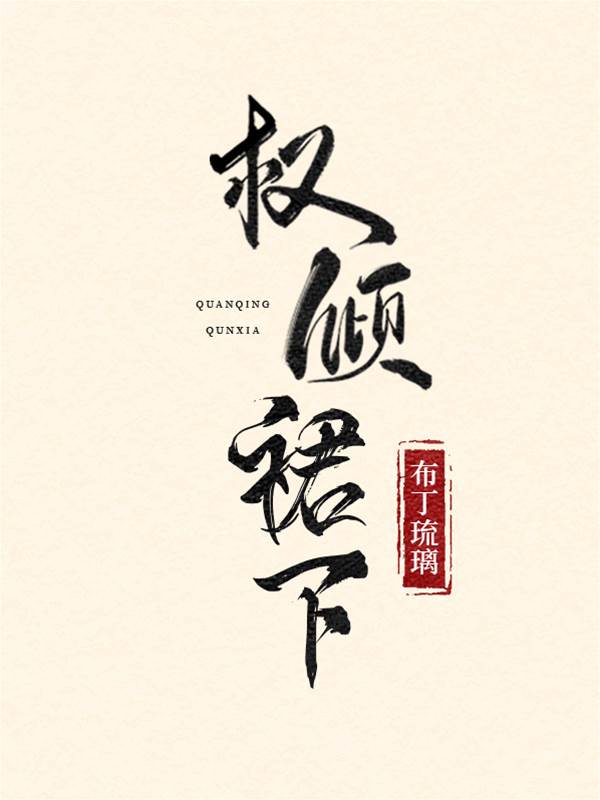《穿到大佬黑化前》 第102章
它回來,重新附到兒上,重新再給這個家帶來不幸。
時暮踱步湊近,蹲下,雙手捧起時媽媽的臉,們有三分相似,時暮看到了眼中的自己,沉,平靜,眼里有紅閃爍。
“你說我是邪,那我讓你見識一下,什麼是邪……”
張,起了黎族最惡毒的招魂咒,剎那萬歸寂,天乍寒,時媽媽和時蓉冷得直打哆嗦,們相擁,子躲在墻角,就在此時,時蓉覺有人在耳邊吹了個涼氣。
慢慢扭頭,一張漆黑猙獰的臉龐近在咫尺,無眼,黑大口占據全臉三分之二,他張,腔深竟有一張嬰兒的臉,正沖咯咯笑著。
時蓉尖一聲,驚恐無助的到了時媽媽懷里。
地獄惡鬼隨著招魂咒接二連三從腳下爬出,它們向時蓉和時媽近,每深吸一口氣,們的壽命就會解一分,且會遭非人的待和苦楚。
“時暮,我是你母親,你怎麼能這樣對我?!!”時媽媽被錮在墻壁之間,臉上已有部分皮變黑,瞪著眼,像是要將時暮撕碎。
時暮閉著眼,誦不停。
時蓉掙扎著爬到時暮腳邊,拉扯著的苦苦哀求,“我錯了,時暮我錯了,求求你讓它們走,讓這些東西離開,我好疼……嗚,我真的好疼……”是真的怕了,那些東西在不斷發出刺耳的,吵得腦袋都要炸了,覺得自己的靈魂和正在被這些惡靈拉扯,疼,四肢再疼,五臟六腑再疼,疼到難以思考,更恐怖的還是它們的面容,丑陋,扭曲,散發著難聞的惡臭。
時暮停下,睜眼,冷冷生生匍匐在下不斷哭泣的時蓉,的眼神掃過時蓉的臉,時蓉的,最后停在上,笑了,眸中竟帶著勾魂的魅:
Advertisement
“你傷我兩次,都在上,是嗎?”
時蓉再哭,沒有回答。
時蓉彎腰看,修長指尖挑起的下,強迫直視著自己的雙眸,說:“我一直以為你只是個被大人慣壞的孩子,所以我包容,忍讓,就算你把我推下樓梯我都認為你只是沖不懂事。可是今天,我發現你壞了,你的人壞了,你的心爛了,你讓我厭惡無比。”
拉著時暮,哭的肝腸寸斷:“時暮,是媽媽……媽媽讓我做的,求求你……放過我,嗚……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下一秒,在時媽媽凄厲的慘聲中,兩只惡鬼竟狠狠擰斷了時蓉的一條,時蓉張開瞪大眼,兩行清淚順著眼角落,都沒來得及,就陷了深沉的黑暗之中。
時蓉暈死過去了,是疼暈的,也是嚇暈的。
時暮踢開時蓉的手,后退兩步,垂眸斂目,“以彼之道還施彼,我斷你一條,很公平。”
“不不不不,蓉蓉……蓉蓉。”滿狼狽的時媽爬到時蓉上,看著臉蒼白,只剩下一條的時蓉,抱著再也忍不住痛哭出聲。
時暮拉過傅云深,“我們走吧。”沒有再看們一眼。
“嗯。”傅云深攬過時暮,攙扶著向外走去。
著兩人背影,時媽媽被淚水浸染過的雙眸迸發出濃濃的銳,目閃爍,看到他腰間流出的巫毒娃娃,時媽媽咬咬,連滾帶爬到傅云深后,趁其不備竟直接奪了過來。
傅云深瞳眸一,扭頭看去。
時媽媽摘下發叉,握著,笑的險:“時暮,燒死你外婆的那把火是我點的,我殺那邪一次,就能殺第二次。”說罷,狠狠把發叉刺到了娃娃膛。
Advertisement
只聽娃娃發出凄切慘,源源不斷從娃娃口滲,巫毒娃娃猩紅一片,笑著,得意洋洋。
時暮捂住口倒在傅云深懷里,能到纏藤蠱溫暖的藤蔓將心臟包裹,也能到纏藤到攻擊時的痛苦,甚至能聽到它的息和魅蠱不安的跳聲。
[哥們兒你沒死了吧?]
[喂,纏藤?]
[格老子的,你不會真死了吧?]
魅蠱再,一聲比一聲急促。
它毫不猶豫的,把自己曾吞噬下去的力量源源不斷輸送到纏藤上,時暮到魅蠱的力量越來越小,心臟的跳聲也越來越大,同時,傷口開始修復,愈合。
這是纏藤,把魅蠱給它的力量再給了,這麼一來,時暮本的力量已經大過了這兩條蠱。
著那細的溫暖,時暮眼眶驟然紅了,明明只是兩條蟲子,甚至都不知道它們是什麼樣子,卻讓切到了被保護的覺。
[孫孫,仙人你個鏟鏟,莫挨老子,離老子遠點。]纏藤說話了,雖然替時暮承了巫毒娃娃的致命一擊,但還活著。
魅蠱沒吱聲,又把力量往纏藤上送了點,小小聲:[老子給你的,不準給外人。]語氣有些別扭。
外人時暮:[……]搶了它們的蠱力還真是對不起了。
“時暮?”頭頂,傅云深視線灼灼,帶著擔憂。
沖傅云深懷里出來,仰頭,毫不猶豫的親上了他的。
傅云深一愣,有些手足無措,“你……”
“我沒事。”時暮笑的很燦爛。
的確沒事,臉上的傷口沒了,眼睛更亮了,也不知是不是傅云深錯覺,總覺得……時暮變的更好看了,是的,好看,甩開了年,骨子里散發出了兒家的。
Advertisement
看著還好端端和傅云深聊天的時暮,披頭散發的時媽媽有些接不能,眼神放空,手上發叉更加兇狠的刺著那娃娃,被這麼一陣瘋狂猛后,娃娃很快變得破破爛爛。
突然,時媽媽像是被驚雷劈到天靈一樣,全都彈不得,眼神閃爍,里呢喃:“時、時黎?小黎,我的小黎……”大哭著繞過時蓉,跌跌撞撞向樓下跑去。
剛才的天變已經讓賓客全部離開,跌跌撞撞來到二樓,索出鑰匙開門,手很抖,半天都對不準鑰匙孔,正當絕之時,時暮奪過鑰匙開了門。
屋窗簾閉,漆黑一片。
床上被褥凌,滿是跡。
時暮往前幾步,時黎倒在上,捂著口眉眼痛苦。
他死了,上有著和時暮一模一樣的傷痕,可惜的是……沒有兩條蠱為他抵擋最后的致命攻擊。
時暮總算明白,為什麼在時蓉第一次刺心臟時還能站起來,和時黎雙生,從母胎出來時只差了十幾秒,巫毒娃娃上寫的是的名字和月份,遭傷害的是和時黎。
時黎先天弱,重病纏,注定難遭此劫。
時媽媽跌坐在地,在這黯淡無的房間里,在倒地的時黎面前,同時倒塌的還有的期。
辛辛苦苦培養的兒子死了,疼的小兒殘疾了,的心沒了,未來……也沒了。
到底報復的是誰?是時暮,是魅蠱,是的母親?
或者,是母親再報復?
時媽媽眼神游離,已然陷到了瘋魔的狀態。
寂靜無聲之中,時暮看到那白纖細的年出現了窗前,他看了腳下的尸一眼,最后又向獨自呢喃的母親,神平靜,無怨無憎。
Advertisement
最后,目定定落到時暮臉上,輕輕說;“帶我離開。”
時暮睫輕,推了推旁的傅云深。
他皺眉,上前把時黎抱了起來。
時黎面無表:“你能不要公主抱嗎?”
“屁話真多。”傅云深嘟囔一句后,把時黎的尸抗在了肩上,只聽哐當一聲,時黎的腳丫子重重磕在了床腳。
“……”看著就疼。
時黎有些不滿:“你能溫點嗎?”
傅云深眼角余冷冷瞥過,他瞬間收聲,繞過傅云深到了時暮旁。
對于突然做鬼,時黎沒什麼太大的波,只是傅云深讓他有些不爽,上那勁兒讓他格外不舒服,時黎余瞥向時暮,眸又暗了暗。
傅云深扛著時黎尸下樓,大廳作一團,一些昂貴的花瓶和用品都不見了蹤影,估計是那些親戚趁捎走的。
時黎的視線認認真真略過房間的每一個角落,他很差,這房子是三年前為了給自己養病,不顧爸爸反對強行讓他買下的,老實說時黎不喜歡這樣的大房子,空間越大,越顯得心寂寥。
傅云深撥打了急救電話,就算時蓉可惡也不能死了,那會對他們造嚴重影響,至于時黎尸,不如給專業的理,一切解決完后,傅云深拉著時暮就要離開。
時黎長睫輕,著急跟上,可在迎上頭頂那灼熱的時,他瞬間退回到了房子。
時暮扭頭看著,站在影的時黎表深邃,眼神之中帶著濃濃的不安與忐忑。
心中微,掙開了傅云深手,重回屋子打了把傘出來,時黎雙手兜,不神跟了過來。
傅云深擰眉,冷聲問:“你要帶著他?”今天過后,他對這家人的非常不好,就算時黎沒做什麼,傅云深也覺得討厭。
時暮咬了咬下,停下腳步和傅云深說:“你先回去吧。”
“嗯?”
“我想和時黎說點事。”
猜你喜歡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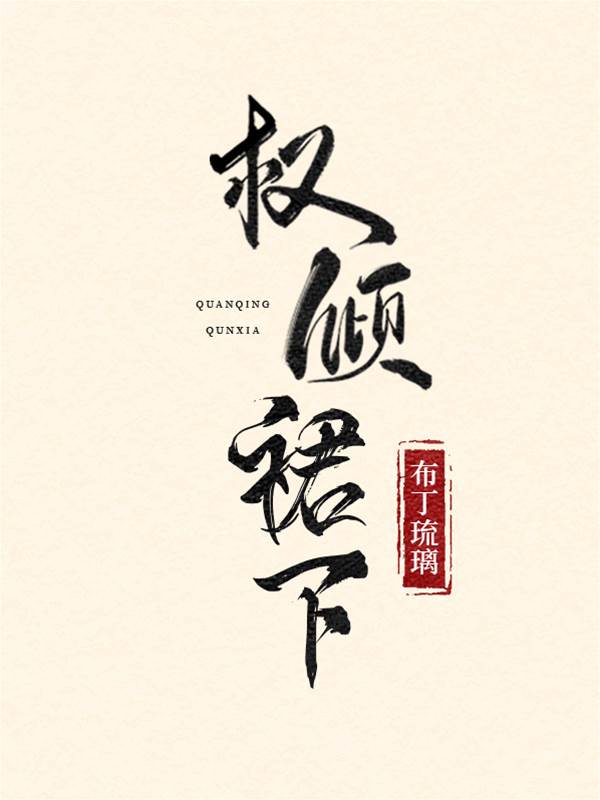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091 -
完結97 章

平陽公主
新科放榜后,群臣大宴于曲江庭,慶賀盛事。 游宴上,皇帝指著新科狀元,對愛女平陽公主道, “此子可堪配吾兒。” 平陽公主抬頭,一口清酒噴出來。 這不就是三年前被她始亂終棄的面首沈孝嗎! 三日后,新科狀元沈孝一道奏疏,聲色俱厲彈劾平陽公主三大罪——不知廉恥、囤積錢糧、暗蓄私兵。 平陽公主: 我只是要了你的清白, 你他媽這是要我的命啊!
31萬字8 10548 -
完結98 章

偏執寵愛
1 軍隊裡大家都知道,他們的陸隊長背上有一處誇張濃烈的紋身。 像一幅畫,用最濃重的色彩與最明媚的筆觸畫下一枝櫻桃藤蔓。 有援疆女醫生偷偷問他:「這處紋身是否是紀念一個人?」 陸舟神色寡淡,撚滅了煙:「沒有。」 我的愛沉重、自私、黑暗、絕望,而我愛你。 「我多想把你關在不見天日的房間,多想把你心臟上屬於別人的部分都一點一點挖出來,多想糾纏不清,多想一次次佔有你,想聽到你的哭喊,看到你的恐懼,看到你的屈服。 ——陸舟日記 2 沈亦歡長大後還記得16歲那年軍訓,毒辣的太陽,冰鎮的西瓜,和那個格外清純的男生。 人人都說陸舟高冷,疏離,自持禁欲,從來沒見到他對哪個女生笑過 後來大家都聽說那個全校有名的沈亦歡在追陸舟,可陸舟始終對她愛搭不理。 只有沈亦歡知道 那天晚自習學校斷電,大家歡呼著放學時,她被拉進一個黑僻的樓道。 陸舟抵著她,喘著氣,難以自控地吻她唇。
32.1萬字8 954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