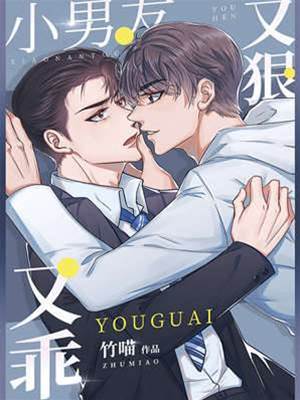《我靠美顏穩住天下》 第99章
悉萬丹的頭顱,是顧元白第二次近距離看到的死人頭顱。
很巧,這兩顆頭顱都是薛遠送到他面前的,一是為邀功,二是為讓顧元白泄憤。邀功的那個頭顱是王土山的寨主,而這個,不得了,是契丹八部的首領之一。
當初荊湖南的反叛軍被回京城斬首示眾的時候,因為徐雄元從始到終都是顧元白掌中的一條線,是個徹底的手下敗將,顧元白沒有想去看他砍頭的興致,因此滿打滿算,他也就見過這兩顆死人頭了。
但顧元白卻很是鎮定。
他是打心底的鎮定,顧元白也沒有想過他能夠這麼坦然,甚至坦然到跟一個死人的頭顱駁回他生前的話。
派人將悉萬丹的頭顱拿去理之后,顧元白問:“沒有其他東西了嗎?”
通報的人道:“驛站還送了一樣東西過來,是薛將軍給送來的。”
說著,他從懷中掏出了一個手帕,雙手舉過頭頂,恭敬送到顧元白的面前。
顧元白看了這個手帕好一會兒,才手去拿起,緩緩展開。
但手帕之上卻是什麼都沒有,空茫茫地一片。顧元白眉頭蹙起,以為是用了什麼方,“端水來。”
在宮侍端水來的時候,他走到殿前,將手帕舉起對著空中烈日,這時才勉勉強強地發現,手帕正中央的部分,有一點細小的沉。
像是混了風沙的水干后的痕跡,若不仔細那就完全看不出來。
“這能是什麼?”顧元白沉思。
通報的人這才記了起來,“圣上,手帕當中還帶著一張紙條。”
他找了找,將紙條遞給了圣上。顧元白接過一看,就見上方寫著:
——北疆的第一片雪花,你的了。
北疆的風雪如鵝飛舞。
在薛遠寫信的時候,有旁人探過頭一看,哈哈大笑道:“薛九遙,應當是北疆的風雪如鴨飛舞。”
Advertisement
此話一出,眾人大笑不已。
營帳外頭的風呼呼地吹著,吹得帳篷颯颯作響。得要石塊著,才能不使風雪吹進來。
薛遠面對這些人的笑話,面不改地沾墨,繼續往下寫著字。
旁人笑話完了他,繼續閑聊著,過了一會兒,有人問:“薛九遙天寫的這些信到底是給誰寫的?”
眾人都說不知道,等有人想要問薛遠的時候,薛遠已經拉開了簾子,獨自跑到外頭沒人的地方繼續寫著信了。
外頭的風雪直接打到了臉上,全靠著上的棉護著熱氣。薛遠強壯,穿著冬后更是渾冒著熱氣,大雪還沒落在他的上,就已經被他上的熱氣給融化的沒了。
薛遠將墨放在一塊石頭上,把紙墊在手上繼續寫,速度變快。沒有辦法,外頭太冷,要是不快點寫,要麼墨結冰,要麼筆結冰。
這都是給顧元白寫的信。
薛遠先前也寫,在奔襲到京城的那一日前給顧元白寄過了許多信,但顧元白就是小沒良心的,他就是不會。從京城回來之后,明知道對方不回,但薛遠還是寫的更為頻繁了。
不知道為何,從京城回來之后,薛遠更想顧元白了。
很奇怪,先前的思念還能被下去,為雜草瘋長。但現在的思念好像找到了竅門,它們知道什麼地方是薛遠的,是薛遠捂不住的地方,于是生長再生長。
比先前的更為猛烈,更為無法制。乃至現在在風雪里去寫著信,薛遠也只覺得心頭火熱,甚至帶上了些焦灼。燙得肝火難,皮燎泡。
風雪同樣打在這張信紙上,但了那點點沉暗反倒有了不一般的意味。薛遠把信收起,揣在懷里抬頭看著天。
Advertisement
呼吸間出來的熱氣往上飛去,他想了一會顧元白,想了一會他也白得如雪、冷得如雪的指尖,想他的脖頸、臉龐和。
好幾次想起來都萬分后悔,那時怎麼沒想起來多親他一口呢?怎麼沒想起來在他脖子上吸出幾個印子呢?
拿個的東西回來惦念,就算是再裝一袋洗澡水,去喝一口顧元白上下的水……怎麼著都比現在這樣干想著強。
帶過來的白玉杯早就沒了顧元白的味道,手帕之上也只剩下龍紋了,薛遠深深嘆口氣,回了營帳。
在外巡查一番的薛老將軍也回來了,極為納悶地看了他一眼,“大冬天,你火氣怎麼這麼大。”
“不知道,”薛遠起眼皮看了他一眼,了,又想,想顧元白想到大冬天都能有這麼大的火氣,可惜,要是這疼是顧元白給咬疼的就好了,他嘆氣,“薛將軍,趕進去,都在等著你。”
父子倆走進軍營,擺在眾位將領中間的是一個沙盤,上方已好不同的旗幟,那是北疆其余游牧民族的地盤。
“來商量商量年后的作戰,”薛老將軍道,“哈哈哈哈,等咱們商量完這最后的作戰,接下來就能準備過年的事了!今年必定是個好年,這最后的關頭,還需要大家伙兒再堅持堅持了。”
眾位將領神采奕奕,齊聲道:“是!”開始熱火朝天地商談了起來。
時間一邁了冬,白天亮著的時候就變得越來越短了起來。不止北疆如此,京城也是如此,且京城的冬季,也就比北疆好上那麼一手指的功夫。
圣上在十二月中旬時,特地出來巡視了一番京城百姓的生活。褚衛也在邊,一行人深看了看,回程的時候,顧元白的臉上就加了些笑意。
Advertisement
在他們一同前往鄉間的路上,盯著褚衛的人便走了一個回了薛府,將這件事告訴了薛二公子。
“圣上和褚衛同游?”薛二公子猛得撐著床面坐了起來,“那你們還不趕快找機會理掉褚衛!薛遠那狗脾氣你們不知道嗎?要是他代的事沒辦好,是你死還是我死?”
小廝道:“是您死。”
薛二公子被嚇得抖了一下,“知道還不趕快手?”
“二公子,不是我們不手,”小廝道,“是我們發現,還有另一伙人盯上了褚衛。”
薛二公子好奇:“誰?”
小廝搖了搖頭:“不知道。但他們今日從一早就跟在了褚衛后,如今褚衛就同圣上在一起,他們要是手的話,怕是這些人都要命不保了。”
“好好好!”薛二公子喜道,“那你們就別做什麼了,就讓那群跟著褚衛的人去替我們手。”
小廝恭敬:“是。”
這些跟著褚衛的人正是西夏皇子派過來的人。
西夏皇子是想暗中教訓褚衛一番,他覺得既然他喜歡褚衛,那也不會做得太過分,就是派人將褚衛綁來,讓褚衛被他辱辱,等他出完氣了,這人就可以放了。到時候大恒皇帝就算要查,也得講究證據不是?
西夏皇子派過來的人并不知道顧元白的份,他們一邊提防著顧元白和褚衛后的一眾侍衛,一邊相互傳遞著消息:“這麼多的人,現在不好下手。”
“但他們在京城里頭也不好下手,”領頭的人急得滿頭大汗,“城里有巡邏的人,也就在鄉間有機會了。”
“你看走在最前頭的那個公子哥,一看就知道不好,手無縛之力,”屬下道,“前頭正好有一山坡,我們埋伏在那里,一批人去擄褚衛,一批人去擄這個公子哥,把這個人帶上正好能拿他威脅那些侍衛們,讓那些人不敢上前。”
Advertisement
領頭人點頭,去頭上的汗:“就這麼辦了,”
顧元白和褚衛緩步走著,有說有笑。正當他們走到一山坡時,旁邊突然有人大聲著沖了出來,手里拿著大刀,兇猛異常,轉眼之間,十數人就從兩側朝著二人沖來。
后侍衛們立刻拔出刀上前,褚衛神一變,當即護在了圣上面前,“圣上,快走!”
說話之間,這些早已埋伏在這的辭客已經沖到了面前,褚衛不閃不躲,正當他準備大義赴死之時,只聽耳側有幾聲破空之音響起,前最先奔來的刺客已經一聲慘,捂跪倒在地。
褚衛一怔,轉一看,圣上面容無比冷靜,正拿著一個小巧無比的弩弓,對著面前的辭客連連著短箭。他當真是鎮定極了,握著弓弩抬起手臂,在這個刺客中箭之后又平穩地轉向了下一個人。
不過眨眼之間,侍衛們已經沖上前去與這些人開始爭斗,只聽沒過幾聲的兵戈撞之聲,這些刺客已經被侍衛們著跪了下來。
顧元白將工程部給他特制的弩弓收起,見到褚衛眨也不眨地盯著他看,冷面上勾起一個溫和笑意:“褚卿,嚇著了?”
褚衛倏地覺得腔之心臟跳,他了手,面上瞬息之間飛上了薄紅,如玉潔的額上,甚至轉瞬之間出了細的一層薄汗。
顧元白安地拍了拍他的手臂,而后上前,走到那最先撲過來的刺客跟前,冷冷一笑,“朕拿到這個弩弓也有半年了,今天還是第一次用,就用在了你的上。”
躬疼得面慘白渾鮮的刺客一聽他的話,眼睛頓時瞪大,面猙獰出了青筋。
皇上?!
猜你喜歡
-
連載9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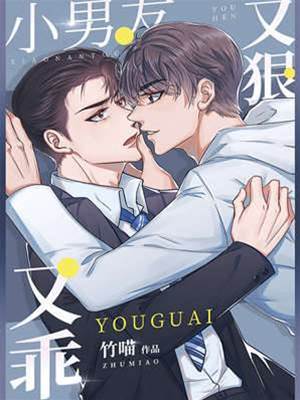
小男友又狠又乖
江別故第一次見到容錯,他坐在車裡,容錯在車外的垃圾桶旁邊翻找,十一月的天氣,那孩子腳上還是一雙破舊的涼鞋,單衣單褲,讓人看著心疼。 江別故給了他幾張紙幣,告訴他要好好上學,容錯似乎說了什麼,江別故沒有聽到,他是個聾子,心情不佳也懶得去看脣語。 第二次見到容錯是在流浪動物救助站,江別故本來想去領養一隻狗,卻看到了正在喂養流浪狗的容錯。 他看著自己,眼睛亮亮的,比那些等待被領養的流浪狗的眼神還要有所期待。 江別故問他:“這麼看著我,是想跟我走嗎?” “可以嗎?”容錯問的小心翼翼。 江別故這次看清了他的話,笑了下,覺得養個小孩兒可能要比養條狗更能排解寂寞,於是當真將他領了回去。 * 後來,人人都知道江別故的身邊有了個狼崽子,誰的話都不聽,什麼人也不認,眼裡心裡都只有一個江別故。 欺負他或許沒事兒,但誰要是說江別故一句不好,狼崽子都是會衝上去咬人的。 再後來,狼崽子有了心事,仗著江別故聽不到,在他看不見的地方悄悄說了很多心裡話,左右不過一句‘我喜歡你’。 後來的後來,在容錯又一次說出這句話的時候,江別故終於沒忍住嘆出一口氣: “我聽到了。” 聽力障礙但卻很有錢的溫文爾
56.5萬字8 6649 -
連載136 章
壯漢將軍生娃記
忠勇侯府的少將軍楊延亭把自己未婚夫婿給打了,還拐回家一個小倌兒。 不想這小倌兒堅持自己只是個陪有錢少爺玩的清白秀才。 後來沒想到兩人竟然被湊在了一塊,要當夫妻。 都說哥兒生子難,偏偏這將軍身體好,生了一個又一個! 設定:將軍是個膚色健康的哥兒,高大健壯,但是因為是哥兒又會有些不一樣的地方,比如寬肩腰細屁股大,再比如有個發情期,反正各種設定都加一點。 秀才不瘦弱了,俊朗一些的,會一些武功,是魂穿過去的。 孕期漲乳,生子產奶,後面流水,只一個穴兒。 肉文,俗爛劇情,1V1,雙潔。
32.9萬字8 16427 -
完結56 章
我就想離個婚[重生]
重生前,葉緋兢兢業業、勤勤懇懇,眼裡只有工作。 重生後,葉緋決定放飛自我。 去他媽的工作!去他媽的合約婚姻! 他再也不要過這種無1無靠,四海飄0的日子了! 離婚,必須離婚! 茶幾上,葉緋甩出一份離婚協議,美滋滋地掰著指頭數—— “最近有個小鮮肉,屁股翹腰窩深,一看就持久。” “還有一個鼻梁挺手指長,一定會玩花樣。” “哪個比較好呢?” 晏梟撩起眼皮,面無表情地看了他一眼。 後來, 葉緋腰酸腿軟的癱在床上,悔不當初地吐出一口煙圈:“失算了。” 呆呆子攻X騷浪受
16.5萬字8 636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