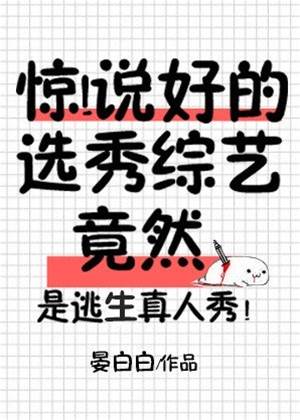《真香》 第14章
【“張先生您好,我是季總的助理,您現在有時間嗎?方便聊幾句嗎?”】
小老板這時候也顧不上什麼保不保溫壺的了,趕去找護士臺問了問七哥的去向。
前臺值班的是兩個年輕小姑娘,小老板報了七哥的房間號和床號:“麻煩您幫忙看看,這個病人轉院去了哪里?他、他怎麼會轉院呢……”
“稍等啊,”小護士低頭幫忙查著電腦,邊查邊問,“您是患者什麼人啊?”
旁邊的姑娘探過頭來,想了想,小聲說:“308房的2號床,啊,這不是昨天晚上的那個alpha嘛,個兒又高長得帥的那一個,一下來了好多人呢,季……”
兩個姑娘彼此看了一眼,敲電腦的那個看看小老板,又問了一遍:“您跟患者是什麼關系啊?”
“啊,”小老板腦子里,慢了半拍才緩過神,猶豫幾秒,說:“……我、我是他對象。”
Advertisement
兩個姑娘看看魂不守舍的小老板,又互相對視了一眼,另一個護士開口說道:“先生,那你還是自己去問他家人吧,這個涉及患者私了,我們不方便告知的。”
“他家人……他家里人昨天來了嗎?他原先腦袋過傷,他是不是想起來……”小老板說到一半就說不下去了,跟人家姑娘絮絮叨叨說這些個也沒用,他也不想讓人家難做,道過謝后就離開了。
恍恍惚惚的走出去十來米了,想起來還有東西沒帶走,又返回去拿。
東西零零碎碎的不算,小老板兩只手抱不過來,路過的保潔大姐好心給了他兩個大塑料袋。就黑的那種薄薄的垃圾袋,干凈的,沒用過,兩個袋子套一起,小老板把七哥留下的東西全裝了進去,再抱在懷里帶了回去。
七哥到底去哪兒了?
小老板是真的很擔心,一會兒想他是不是把以前的事兒都記起來了,找到了家里人,現在在親人的照顧下好好地養病,一會兒又想他會不會到什麼麻煩了,否則為什麼到現在都沒聯系自己。
Advertisement
就七哥失蹤的這兩天,小老板飯吃不下覺睡不好,但一時半會兒也想不到別的法子,從他撿了七哥開始,兩人就沒有分開過,小老板這時候就很后悔當初沒給七哥買個舊手機,不然現在可能也不會完全斷了聯系。
到第三天時,七哥那邊還沒消息,來消息的居然是對面的醫大夫。
大夫手里捧著個什麼黑漆漆的玩意兒,風風火火的就來了,人沒進門呢,聲音先進來了:“誒誒誒!你看你看!這是不是你家傻子?!”
小老板在柜臺后面,從椅子上一下站起來:“什、什麼?”
大夫舉著遙控,對著掛在一旁的電視狂按,按了好幾下才反應過來,“誒這是我那兒的,你遙控呢?!電視打開!一會兒沒了!”
兩個人一通手忙腳的打開電視,大夫給切了臺,指著屏幕一臉的興:“是不是他?”
電視畫面里正播放著幾個西裝alpha的遠景照,底下小標題寫著某大型電子娛樂公司召開直面會。
Advertisement
電視鏡頭有點晃,離得也遠,其實有點兒看不清。大夫湊在小老板邊,瞇著眼睛看半天:“是他吧?”
是七哥。
小老板仰著臉看電視,七哥發型似乎變了,頭發剪短了很多,一的西服領帶看上去覺也很令人陌生,但他肯定不會認錯:“是,是七哥……”
大夫快速掏出手機刷刷地查,“姓季……季哲遠,你看。”
“是個公司老總啊我的天,你居然撿了個大老板回來。”大夫拿著手機在小老板面前晃了晃,笑著跟他打趣地道:“你是不是要嫁豪門了?”
大夫一全程圍觀人員,也不知道自己興個什麼勁兒,從兜里出煙來,叼里接著逗小老板:“茍富貴,勿相忘。”
小老板呆呆的看著他,完全沒能把剛剛接收到的消息消化掉:“我……”
“請問張寒在嗎?”小賣鋪門口忽然進來個人,是個年輕的男beta,穿著正裝,進門稍稍打探了一下屋里兩個人,臉轉向小老板,又問:“請問是張先生嗎?”
Advertisement
“我是,”小老板——也就是張寒,朝來人禮貌點點頭,應了個聲,“您是哪位?”
大夫手里夾著煙,跟張寒比劃了一下,轉出去了。
年輕beta從兜里出張名片來,客客氣氣地遞過去:“張先生您好,我是季總的助理,您現在有時間嗎?方便聊幾句嗎?”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