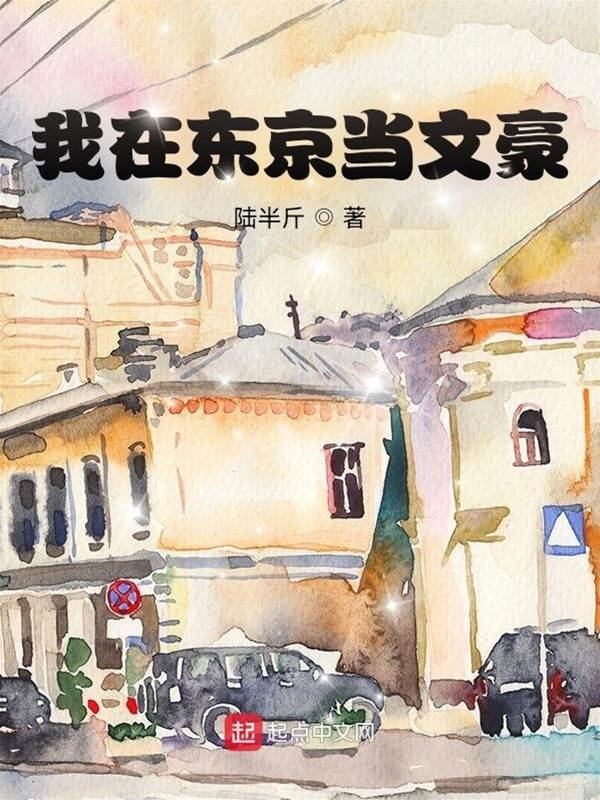《逍遙小地主》 第五十七章 其實我不是一個好人
傅小已于昨日回臨江。
父子倆飲酒座談了很久,傅大說起漆氏所做的那些廣告很是擔憂,認為自家酒坊是不是出了,否則他漆氏如何敢說拳打香泉腳踢天醇這等狂妄語言?
再看漆氏那勢頭,買了足足三十萬斤糧食啊,聽說還買了好多蛋,導致臨江蛋一時缺——這廝難道弄出了新的方?
如果他那酒真弄出來了,余福記該如何應對?
傅大很焦急,因為余福記是云清所建,而今在兒子的手上發揚大,這是榮耀的象征,可絕不能垮了。
傅小反而寬了他很久,說就算漆氏真的弄出了新酒,自己家的酒不是了皇商還供不應求嗎?無妨,說不定他那豪言壯語放出去了,卻弄不出來,豈不是了臨江天大的笑話。
傅大可不認為是笑話,做生意的人,誰會沒有把握就敢弄的滿城皆知的?不過自家的酒了皇商這倒是事實,價錢沒有低毫,特別是西山瓊漿,更是天價,如此想來,傅大才稍微寬了心。
然后對于傅小在下村所作所為進行了一番贊賞,卻批評了傅小著腳桿下田這事。
對于傅小要為王家村的百姓建房子,這事兒傅大是有看法的,但既然傅小已經那樣做了,也就沒說什麼,只說下不為例,因為我家是地主,不是善人。
傅小不以為意,最后傅大說道中秋夜半山書院詩會,這是劉之棟知州大人給他下了帖子的,明兒晚可得去一趟,畢竟知州大人的面子還是必須要給的。
Advertisement
傅小答應了,他也想去瞧瞧這年代的人是如何賞月度中秋。
然后父子散去,傅小回房休息。
十日前給董書蘭寫了一封信,算著時間應該正好在中秋這天收到,希能喜歡。
明兒晚那些才子們肯定又是要他寫詩的,這時候正好想想。
……
秋意雖淡,那梧桐的葉兒卻見黃。
傅小起床之后依然運了一番,洗漱之后和蘇墨春秀三人一同用餐。
這是傅小的強烈要求,春秀漸漸也習慣了,蘇墨當然無所謂。
傅小看著蘇墨,忽然問道:“你吃飯……是習慣還是故意,或者說是不是練什麼功夫?”
蘇墨一怔,他斜乜了一眼傅小,這家伙居然觀察的這麼仔細!
“小時候家里很窮,五歲那年遭了災,蝗災旱災水災然后是瘟疫,什麼都沒有了,父母也沒有了,我流浪在街頭,了一個饅頭,沒有人發現。”
蘇墨說的很平淡,可傅小卻明白這平淡背后的艱辛。
“你這種地主家的爺是難以理解那個饅頭對我而言是多麼味的東西,我咬了一小口,數著嚼了三十三下才吞下去,因為再多嚼就要反胃了,三十三下正好,就是這樣。”
“后來你就去了道院?”
“流浪了很久,打架,搶吃的,甚至……殺了人,直到十歲,遇見了我師傅,這樣才進道院。”
“哦,是慘的,不過嚼三十三次腮幫子會痛,我試過。”
Advertisement
春秀沒有吱聲,好奇的聽著,覺得蘇墨這年也不容易的。
兩人這次流的時間略微長一點,但這頓原本愜意的早餐卻被一個聲音終止了。
“傅小!你給我出來!”
這是張沛兒的聲音。
傅小抹了抹,嘿嘿笑了起來。
蘇墨便覺得這人賤的。
肯定是那酒出了問題,張沛兒這是登門發泄了。
“讓進來。”
春秀走了出去,傅小想了想,對蘇墨說道:“呆會你把李二牛帶過來。”
“你這是要攤牌?隔壁那邊怎麼理?”
“那邊先不管,就快要生了,讓順順利利的生個孩子吧。”
“行。”
傅小走了出去,對怒氣沖沖進來的張沛兒拱手行了一禮,笑道:“張姑娘請坐。”
張沛兒坐在石凳子上,那雙眼睛一直盯著傅小,就像傅小的臉上有一朵很的花一樣。
傅小煮茶,說道:“其實我這個人真的沒你想象中的那麼好——以前臭名昭著,現在只是被我藏了起來,骨子里還是很壞的。”
“你都知道?”
“漆遠明沒找你麻煩?”
“你故意給了我假的配方,讓我面掃地,讓我輸得一敗涂地——這就是你想看見的?”
傅小嘆了一口氣,“這一切都是漆遠明在運作,姑娘你不過在幕后,就算現在他那酒沒釀出來,損失的也是漆家的名聲,你為何非得把自己放進去?”
Advertisement
張沛兒哼了一聲,“是啊,敗壞的是漆氏的名聲,如果我不想他們將我拋出來,那我就必須嫁給漆遠明,這應該就是你想看見的結果了?”
和這種小蘿莉通很頭痛,傅小皺了皺眉頭,耐著子說道:“其一,是你在打我那配方的主意,我不過隨便布了個局而已,這我沒錯吧。其二,你要做什麼,或者說你要嫁給誰,那是你的事,和我一錢的關系都沒有。懂?還是不懂?”
張沛兒咬著,淚珠兒又撲刷刷的流了出來。
“你這個……混蛋!你就是混蛋!”
傅小這就很無辜了,這特麼怎麼變我是混蛋了呢?
果然是唯子與小人難養也!
“別忙著哭,給你瞧一個人。”
蘇墨將李二牛帶了上來,傅小指了指李二牛,問道:“張姑娘,你可認識此人?”
張沛兒當然不認識,下意識的搖了搖頭。
“好了,帶下去吧。”
“東家,東家,我,我冤枉!”李二牛大。
傅小站了起來,“哦,你說你冤枉?”
李二牛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小人冤枉小人冤枉,小人是因……”
傅小眉間一,牙齒一咬,一把抓起李二牛的手,摁在了茶桌上,順手將蘇墨背上的劍拔了出來,毫不猶豫的一劍劈了下去。
“啊……!”
鮮飛濺,濺了一桌,濺了張沛兒一臉。
“啊……!”張沛兒大,豁然后退,噗的一聲摔在地上。
Advertisement
傅小若無其事的把染的劍在李二牛的服上拭干凈,蘇墨背上的劍鞘,看著李二牛驚恐的眼睛,笑道:“記住,你是不冤枉的!”
李二牛抬起自己的左手,左手齊腕而斷,熱騰騰的鮮汩汩的流。
“啊……!啊……!”
“帶他下去,包扎一下。”
傅小向張沛兒走去,張沛兒嚇得拼命往前爬。
“別怕,起來,你看,我告訴過你我其實不是一個好人,你現在知道了吧。起來啊!”
最后這三個字語氣有點重,張沛兒嚇得一骨碌爬了起來。
“以后呢,不要用這些自以為是的小聰明來煩我,我很忙的,我最后一次告訴你,你若再招惹我……我會殺了你的!”
“去那邊洗一把臉,孩子家家的臉上那麼多跡,會嚇著別人的。好了,別怕,另外,我那姨娘是被你蒙騙的,這事兒和無關,我希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猜你喜歡
-
完結764 章
我在古代日本當劍豪
穿越到了公元1789年的古代日本,時值承平日久的江戶時代。開局只有一個下級武士的身份、佩刀、以及一個只要擊敗或擊殺敵人便能提升個人等級與劍技等級的系統。……“遇到強敵時我會怎麼辦?我會拔出第二把刀,改換成我真正拿手的劍術——二刀流。”“如果還是打不過怎麼辦?”“那我會掏出我的左輪手槍,朝敵人的腦袋狠狠來一槍。”緒方逸勢——擁有“人斬逸勢”、“劊子手一刀齋”等稱號的“大劍豪”如此對答道。
331.6萬字8 17536 -
連載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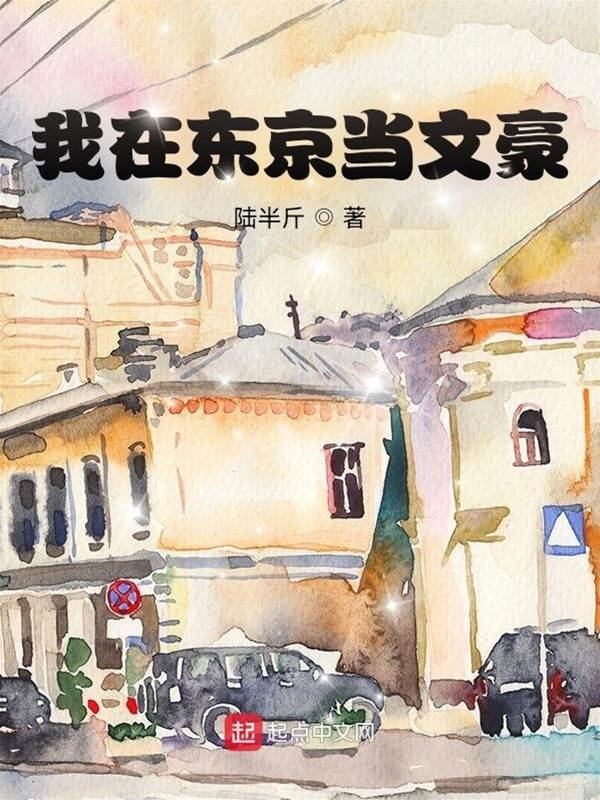
我在東京當文豪
這個霓虹似乎不太一樣,泡沫被戳破之後,一切都呈現出下劃線。 原本那些本該出現的作家沒有出現,反而是一些筆者在無力的批判這個世界…… 這個霓虹需要一個文豪,一個思想標桿…… 穿越到這個世界的陳初成爲了一位居酒屋內的夥計北島駒,看著孑然一身的自己,以及對未來的迷茫;北島駒決定用他所具有的優勢去賺錢,於是一本叫做暮景的鏡小說撬開了新潮的大門,而後這本書被賦予了一個唯美的名字:雪國。 之後,北島駒這個名字成爲了各類文學刊物上的常客。 所有的人都會說:看吧,這個時候,我們有了我們精神的歸屬……
41.5萬字8.18 140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