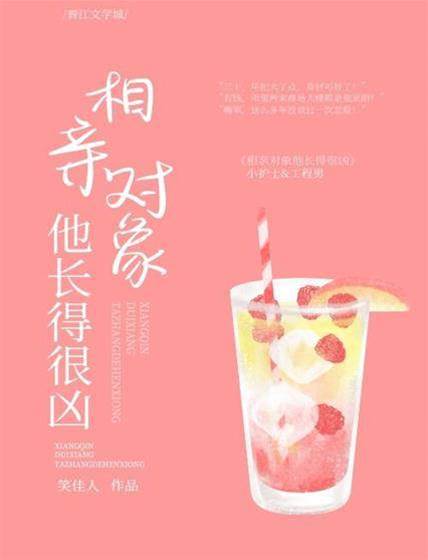《我終于失去了你》 第20章 莫鋮,我們……不再見
莫鋮獄后,許諾去看他,如果按懷孕的時間算,該大腹便便,但看起來,就跟這年紀的孩正常一樣,就是瘦得厲害。
莫鋮被帶過來,看到的第一句是:“阿諾,你怎麼瘦了?”
懷孕,該好湯好水伺候著,養得圓潤可才對,怎麼瘦這樣。他下意識向的腹部,那里很平坦,一點都不像懷孕的人。
莫鋮面一凝,遲疑道:“你……”
許諾平靜地坐下來,無波無痕:“我打掉了。”
“什麼?”莫鋮本不相信他聽到的。
“我打掉了。”許諾又重復了一遍。
“你——”莫鋮猛地站起來,握拳頭,強著緒問,“為什麼?”
他以為他是了解的,他的諾雖然看起來冷漠,但比誰都善良。不會的,怎麼會去害一個生命,何況那是他和的孩子?不!他不相信!莫鋮搖頭,眼睛充得厲害:“是不是有人你?我爸爸?你媽媽?”
“沒有,”許諾搖頭,相比他的震驚憤怒,看起來安之若素,就像說一件與自己無關的事,“我自己打掉的。”
看著莫鋮,那麼平淡的語氣:“我不能讓孩子有一個強犯的父親。”
我不能讓孩子有一個強犯的父親,我不能讓孩子有一個強犯的父親……強犯三個字不斷在腦中盤旋,莫鋮的思緒很,簡直天崩地裂,他有些失控地大喊:“阿諾,你怎麼能那麼做?那是我們的孩子!”
“為什麼不能?那是我的孩子,我有權決定他的生死,”許諾嘲諷道,坐著不,“我就是在單親家庭長大的,單親的痛苦我比誰都清楚。人言可畏,與其讓他飽冷言冷語長大,還不如他從未出生。”
Advertisement
“你怎麼能這麼想?不是還有我!”
“你?”許諾可笑地看他,“莫鋮,你以為發生這麼多事,我們還能在一起?別天真了!”
“那你也不能打掉,你怎麼能這麼殘酷?”
“我為什麼不能?”許諾也有些控制不住,猛地站起來,握拳頭,“一開始我就說了,對我仁慈點,可你怎麼對我?你強了我,我阿公死了,你讓我二十歲生日還沒過就背負未婚先孕的惡名!你怪我殘酷,那你好好看看,我就是這樣一個殘酷的人!”
莫鋮簡直要崩潰了,他心甘愿進來,拿自由去賭自己在心里有沒有一義,想去化解許諾的仇恨,可他輸了,輸得一敗涂地,不他,一點都不他。不然為什麼他都做到這地步,還是不放過,那是他們的孩子……
他著面前的孩,瘦弱纖細,像一陣風都能吹倒,可打掉他們的孩子,毫不留。這麼陌生的許諾是莫鋮沒見過的,原來他從沒有看。莫鋮握著拳頭,死死地盯著:“許諾,如果我是個強犯,你也比我高尚不了多,你這個殺人犯!”
最后幾個字,幾乎是咬牙切齒,簡直要把許諾撕碎吞進去。
許諾一震,面一白,沉默了一會兒,抬頭又是一張嘲諷的臉:“生命?那對你來說是生命,對我來說,不過是恥辱!莫鋮,別再說冠冕堂皇的話,我要生下來,給他一個強犯的父親,給他一個不完整的家,那才是殘酷!就算我是殺人犯,我殺了他,也是恩賜!”
“你——”莫鋮怒火攻心,氣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指著許諾全發抖,他怎麼也沒想到許諾會說出這樣的話。
許諾不再看他,坐下來,緩緩地把無名指的戒指摘下:“我來不是和你爭吵這些的。”
Advertisement
把戒指推上去:“我是來還你這個的。”
這個戒指,是他們第一次接吻,他跪下來戴在手上,說是他的承諾。
那天,一時沖拿刀要砍他,沒想下來,阿公去世,在墓地見到他,沒想下來,發現懷孕,要想打掉被他帶走,也沒想下來……有很多下戒指甩他臉上的理由,可一次都沒有,如今,要還給他了。
莫鋮看到戒指,呲牙裂,額頭的青筋突起:“你什麼意思?”
“你不是這麼不聰明的人,”許諾站了起來,還是無波無痕的樣子,該和他說再見,可他們大概不會再見。最后看了一眼這個快崩潰的男人,像要把他看進眼里,刻進心里,深吸了一口氣,盡量心平氣和地說,“莫鋮,我們……不再見。”
不再見,再也不見。
說完,許諾轉就走,后面傳來莫鋮的大喊,他用力敲打隔離窗。
“許諾!許諾!”
“你這樣恨我,到底有沒有對我心過?”
許諾一滯,停下腳步,看著無名指淡淡的痕跡,清晰道:“沒有,一點都沒有!”
“很好,許諾,你夠狠,是我瞎了眼上你,都進了監獄,還想著我的諾在外面一個人會不會孤單,會不會太辛苦,”莫鋮在后面哈哈大笑,他已經崩潰了,邊哭邊笑,“你說對,一開始我就該離你遠遠的,你不任何人,你沒有心。難怪我第一次見你,你就沒人疼沒人的樣子,像你這麼惡毒的人本沒一個人會你!”
“那也是我的事,”許諾回頭,昂頭,那麼驕傲,“一定會有人我的!”
說完,就走了,這一次沒再回頭。莫鋮在后面詛咒般地大吼:“不會有人你的,不會的,許諾,除了我,誰會像我這樣你……”
Advertisement
許諾往前走,直到出了監獄大門,仍覺得莫鋮在耳邊怒吼,詛咒般地大喊。
走出監獄,幾乎已經耗盡了所有的力氣。扶著門才沒倒下,服地在上,全是冷汗,掌心跡斑斑,全是指甲劃傷的。
門衛看到沒有一,好心問:“小姐,你沒事吧?”
“我沒事,謝謝。”許諾擺手,沖他虛弱地笑,卻比哭還難看。
傻瓜,有什麼好難過的。
他們本該如此,各自遠離,不再見,唯一的羈絆也沒了,現在更了無牽掛了。
結束了,一切都結束了。那些被剪去刺的純白時,最終還是逃不了命運,全部灰暗。
許諾休息了一會兒,繼續往前走,走得很慢,邊走邊想,再也不會要莫鋮見面,一次都不要了,死也不要了。
沒走多久,就看到趙亦樹在前方,神哀傷地著。
許諾路過他,聽到趙亦樹在邊問:“為什麼一定要這麼做?阿諾,你怎麼這麼傻,世間那麼多條路可以走,你偏偏選了最難走的那條。”
許諾沒有停下,往前走,喃喃自語,神經質般重復道:“因為我不他,我一點都不他,連喜歡都沒有,我從來沒有喜歡過他……”
趙亦樹默默地跟在后,直到崩潰地蹲下來,大喊:“因為我恨他,我恨他!”
抱著膝蹲在地上,把臉埋在膝蓋上,不泄出一點表,可聲音卻是哽咽痛苦的:“我說了,我不要,我不要人,他還要過來,就那樣一點預兆都沒有就過來,說來告訴我什麼他喜歡我……”
“幫我學,給我扛行李,買早餐,夏天天氣熱,怕我中暑買涼茶,怕我不喝,還一買就是整個班,軍訓才幾天連教都請了好幾次飯,后面更神經,一聲不吭就跑到我家,說要看看我怎麼長這麼鐵石心腸的樣子,走了好多地方,拍了好多照片,每張都給我留了位置,說要帶我一起走……”
Advertisement
原來都記得,每一件都記得,深深地刻在腦海里,怎麼都忘不了。
“我煩他,超煩他,連我阿公都以為我了男朋友,說不擔心我了,我真是討厭死他,可是我長這麼大,從來沒有一個人這樣對我,一個都沒有。真的,誰都沒有他對我好。他從不沖我生氣,我再怎麼氣他,他也是不說話,第二天又跑過來找我。我喜歡的討厭的他全都記得清清楚楚,他討厭上圖書館,可每天提早替我占位置,我故意到關門才肯走,他也不會讓我一個人走……”
“二年,宿舍的白玫瑰就沒斷過,很多都是他去摘的,說阿諾要用最好的。還給我宿舍姑娘送禮,送得比們男朋友還勤,說要討好娘家人……我對他做了很多壞事,可他還是對我好。他這樣好,我已經習慣他對我好,習慣他替我安排了一切,習慣他說什麼我就相信他能做到,可他為什麼要這麼做,為什麼?”
“他說要我和來日方長,可現在在哪里,在哪里?”
許諾哭得聲嘶力竭,哭得幾乎要把淚流盡。就這樣放肆地哭,直到嗓子啞了,直到眼淚快流干,袖子都了,夢囈般:“我恨他,我恨我他。”
最后還是上他了……
他說,你能讓云不嗎,不能就不能阻擋我你,也一樣。
一旁的趙亦樹聽到,心一震,他覺得要說什麼,又覺得什麼都沒必要說,他沉默地陪著。直到許諾站起來,眼睛哭腫了,頭發了,但卻比剛才萬念俱灰的樣子多了些生氣。
站起來,很麻,一瞬間幾乎站不住,趙亦樹扶住,好一會兒,才緩過來:“謝謝你,我要回去了。”
他們倆何時需要說謝謝,趙亦樹著許諾,真誠地說:“阿諾,無論什麼時候,如果你需要幫助,都可以找我。”
趙亦樹的話,從來不是客套,也不是敷衍。
許諾點頭,慢慢往前走,激他,但現在誰也救不了,這是選的。
趙亦樹說得對,那麼多條路,偏偏選了最難走的路。這完全是自找的,但再難走也要走下去。
許諾回到家,媽媽在收拾行李,收拾得差不多了。
莫永業步步,蘭清秋一敗涂地,資金被套牢,就連這套房,也得賣了。
蘭清秋沒辦法,在白城呆下去,只有山窮水盡的一天,趁著還有一點點本金,去別的地方發展,帶許諾一起走,反正許諾學業也沒了。母倆一起,就不信,莫永業再厲害,出了白城,還能這樣打。
接二連三的事,讓蘭清秋神也不好,眼底全是疲倦。
看兒進門,淡淡問了一句:“回來了,去哪了?”
許諾沒回答,哭了那麼久,口干了,想喝點水,可房間收拾好了,連口水都沒有。
蘭清秋早就習慣許諾的冷淡,這兩天母倆就是這樣,許諾一句話也不同說。
蘭清秋繼續說:“阿諾,你看下有沒有落了什麼東西,車票媽媽買好了,下午就走。”
終要離開了,許諾環視房間,阿公的照片還掛在墻上。
搬了椅子摘下來,著老人的臉,說:“你走吧,我不跟你走。”
“許諾你什麼意思?”蘭清秋急了,嗓音很尖厲,“你還真和媽媽記恨上了?你不走,你一個沒文憑沒學歷沒社會經驗的學生要到哪里去?”
“現在只要不懶就不會死。”許諾淡淡道。
“許諾!”蘭清秋大吼一聲,真心累也很煩。如今的局面讓煩,兒讓煩,怎麼這麼命苦,就沒一個能讓省心的,老公被小三搶了,事業毀了,就連許諾,簡直生來跟作對的,冷漠道,“許諾,你這是在恨我嗎?”
“對,我在恨你!”許諾也按捺不住。
“恨?你有什麼資格說恨我?”蘭清秋反問,冷哼一聲,“要不是你報警,會變這樣?你把你未婚夫弄到監獄,害得你媽媽快破產了。媽媽沒有扔下你,還要帶你走,已經仁至義盡,你還想怎樣?早知道你這樣,我就不該生下你。也對,許淮安這顆壞種,能生出什麼好東西,有你這樣的兒還不如沒有!”
“你不想要我這個兒,我也不想要你這個媽媽!”
“許諾!”蘭清秋大吼一聲,一怒之下,手狠狠甩過去。
許諾沒躲,生生了這掌,盯著母親:“難道不是嗎?有哪個媽媽會像你這樣做,先是我嫁給他,后來——”
許諾說不下去,抱著相片:“要不是阿公不在,他會讓你這樣做?”
“你還臉提你阿公,阿公就是你害死的!”蘭清秋不了地大喊。
一霎時,許諾的嚨堵住了,媽媽說得對,阿公確實是害死的。
蘭清秋也恍然意識到這句太重了,走過來,試圖解釋:“不是的,阿諾,媽媽不是這個意思……”
許諾往后退了一步,眼里有淚:“對,你說得對,我害了阿公。可是媽媽,你做的一切真的為我好嗎?你是為我好,還是想我為你鋪路?”
眼淚落下,許諾終究是把這句最傷人的話說出來。
蘭清秋滿臉的難以置信,兒竟然這樣看,頹廢地坐下:“阿諾,你要這樣想,媽媽也沒這麼辦法,但沒有一個做父母的會想害自己的子。”
“可你毀了我,”許諾打斷,看著母親,全是絕,“媽,你走吧,我是不會跟你走的,你說得沒錯,我恨你,我一看你,就想到——”
許諾不想再提,痛苦地別開臉:“這樣子,我們怎麼可能共一室?你走吧,你放心,我二十歲了,能夠好好照顧自己。”
許諾最后還是沒跟蘭清秋走。
母倆像世仇,帶著各自的行李,搭上了不同的車,背道而馳。
許諾沒什麼行李,就一個箱子,還有阿公的照片。
對司機說去火車站,可下了車,去售票買票,看著大屏幕。天南地北的火車會把這里的人帶到全國各地,有可能去見他們的親人,有可能去找他的人,有的只是去出差,那呢,又何去何從?
天下這麼大,屏幕上那麼多地名,許諾竟不知道選哪個地方。
哪個地方都沒有的親人,的人,到哪都是一個人。
“你到底要去哪?”售票員不耐煩地催。
“我,我——”許諾張了張,還是讓給排隊的下一位旅客。
在火車站了坐了很久,想了很多事。其實也沒想什麼,無非是生命中來來去去得可憐的幾個人。莫鋮說沒人,許諾不信,不信一輩子都沒人。
天沒黑,許諾做了個決定,走出車站,坐公車去白城最破舊的老城區崇明。
從公車走下來,天已黑了,許諾在街上走了一會兒,看到一家房產中介。進門,對里面正打哈欠的工作人員說:“我要租房。”
工作人員熱地介紹起來,問許諾有沒有什麼要求。
許諾抱懷中的照片,啞著嗓子說:“沒什麼,便宜就行。”
幾天后,把照片掛在小得可憐的租房墻上。
看著上面永遠笑得和藹可親的老人,微笑地說:“阿公,你放心,我會好好的。我不會像媽媽,總讓你擔心,我會人,也會有人。”
是笑著的,可心卻空的,很苦,苦得荒無生息。
白城白城,終究還是留在這里,留在有他的城市。
可又能怎樣,他們完了。沒有留下莫鋮給的任何東西,除了小木塊,一面后會無期,一面來日方長。許諾把木塊掛起來,對著的總是后會無期那一面,看得心煩,收起來放在屜里,扔進去假裝無意讓正面是來日方長。
但他們沒有來日方長。
猜你喜歡
-
完結1111 章

蜜婚情深:戰少的心尖寵
“你願意跟我結婚嗎?就現在。” “可是我很窮,我還小,我還在上學。” “沒關係,隻要是你就行了。” 一個是荒唐無稽的不良少女,打架、逃課,不學無術。 一個是根正苗紅的年輕權少,正直、果敢,權勢滔天。 誰能想,這樣的顧城驍竟然把這樣的林淺寵得上天入地。 “少爺,少奶奶又打架了。” “還不趕緊去幫忙,別讓她把手打疼了。” “少爺,少奶奶又要上房揭瓦了。” “還不趕緊給她扶穩梯子。” 問世間是否此山最高,一山還比一山高,這是一個馴服與被馴服的正經言情故事。
196.4萬字8 67152 -
完結6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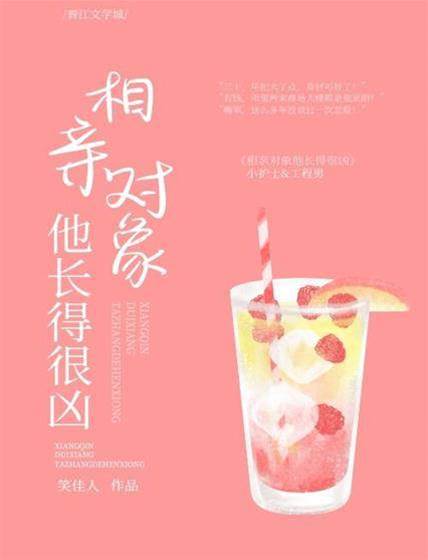
相親對象他長得很兇
江桃皮膚白皙、面相甜美,護士工作穩定,親友們熱衷為她做媒。 護士長也為她介紹了一位。 「三十,年紀大了點,身材可好了」 「有錢,市裡兩家商場大樓都是他家的」 「嘴笨,這麼多年沒談過一次戀愛」 很快,江桃
20.8萬字8.57 45623 -
連載1194 章

大佬歸來,假千金她不裝了
(真假千金+玄學打臉,男女主雙強,1V1)被關家掃地出門後,關栩栩搖身一變成了身價千億的真千金。關家人後悔了,仗著養育之恩,要姜家一半身家做報答。 關栩栩冷笑一聲,一道真言符,直接揭穿關家人的醜惡嘴臉。 渣男想回頭糾纏, 關栩栩抬手就讓他夜夜見“祖宗”。 一向和姜家有舊怨的徐家舔著臉登門, “過去都是小弟不懂事,只要姜大師肯幫忙,以後姜總是我哥!” 回過神的薑家人才知道,他們以為的小可憐居然是個真玄門大佬。 驅邪,畫符,救人,還要追金大腿。關栩栩表示,“我好忙。” 褚·金大腿·北鶴主動分擔壓力:“不用追,已經是你的了。”
222.4萬字8.57 360017 -
完結1257 章

偏寵狂妻:大佬是我心頭寶
顧家棄女顧北風,人不愛花不喜。 可江都城的江家少爺,江野,卻把她寵成了心頭寶。 人人都傳江少手段毒辣,人見人懼,是個不好惹的人物。 江野:介紹一下,我家小未婚妻,人見人愛花見花開,很乖的。 衆人震驚:爺,您怕是對乖有什麼誤解? 江少:我家小朋友尊老愛幼,特別善良。 衆人:???顧家被滅了,老貓都沒留一隻。 江少:……總之,你們得寵着。 好好好,都寵。 直到有一天,江家大門被各方大佬踏破門檻: “爺,香會要搶夫人了,說夫人調出了S級香……”“爺,中醫那邊也來搶夫人了,說夫人是不出世的神醫……” “爺,殺手聯盟也來人了,說窩藏了他們會長。” 江野大怒:“滾!” 其它人可以理解,爲什麼殺手聯盟也來?!
124.1萬字8.18 10482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