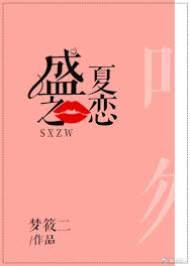《夜裡星辰夢見你》 第74章 拿女兒當跳板
黎景緻嚴重懷疑陵懿去M國談的生意因爲提前回來而談崩了。
原本以爲他在病房裡陪自己三五天也就過去了,沒想到,他竟然一直在醫院陪呆了大半個月直到出院。
之前只匆匆來看一次的黎家人,卻忽然每天按時報道,來噓寒問暖了。
黎母坐在牀邊,著眼淚看著,除了問吃了什麼吃的好不好,卻再也說不出什麼其他的話來;黎父則想盡辦法跟陵懿搭話,想從婿這裡再獲得一點好;黎雅緻就站在父親後,眼的看著陵懿的臉,時不時一句話。
第一次,黎家三口在的病房裡逗留了一個多小時。
最後還是陵懿嫌煩而委婉的把人給趕了出去,之後,黎家三口就每天都往的病房裡跑。但陵懿嫌煩了,基本上只聊個三五分鐘,讓他們把東西放下,就送人了,藉口是,需要靜養。
Advertisement
黎家人依依不捨的離開,不捨的對象卻是陵懿。
有時候,不笨也是一件悲傷的事。
看得出,父親來這裡,只不過是以自己爲藉口,明正大的接近陵懿罷了。是個人,不是個件,爲什麼父親對自己可以冷漠至此?明明對待雅緻的時候不是這樣的。
陵懿自然看出了的失落,也看出了黎家的況。
之後,黎家人一直被擋在門外,再也沒進來過。
出院時,左鼓著,行不便,陵懿讓人買了個椅送過來。
他橫抱著,放在了椅上,也是他親自推了椅,帶出去。
接他們回陵家的車停在醫院門口,陵懿低下,輕的將抱起,放在後座,還溫仔細的替扣上了安全帶,這才走到另一側,打開車門跟坐在一起。
車門關上的剎那,黎景緻眼睛好像被什麼東西閃了一下,有點像,相機的閃燈?
Advertisement
四看了看,卻沒有任何拿著相機的人。
見眼睛,陵懿了過來,怎麼了?
沒什麼。可能是多心了,誰會閒的蛋疼去拍一個骨折人員出院?
黎家冷漠,也沒提過要接黎景緻回家修養之類的話,連一句客套都沒說。郝映心疼,強烈要求把接回陵家的老宅照顧,家裡傭人多,還有家庭醫生每天侯著,營養師備著,最適合養病。
黎父對此肯定沒有任何異議,他不得把大兒放在陵家呢,這樣,他纔可以藉著探病的藉口,時不時往陵家跑一跑,套一套關係。
郝映脾氣是極好的,最開始幾天,黎父來看黎景緻,總是笑臉相迎。
幾次三番過去之後,也覺察出不對味了。
哪有看兒每次都找著藉口跟自己說話,還非要等著兒子回來跟兒子說話的,見不著兒子就跟老公說話。每次帶來的東西也從不說營養品,反而是些檀木手串、清代鼻菸壺之類小玩意兒。
Advertisement
這哪裡像是探病的?分明是利用兒當跳板。
饒是再好的脾氣也經不住這麼消磨,可格又,不好意思說出太難聽的話,畢竟這人是自己兒媳婦的親生父親。
猜你喜歡
-
完結485 章
萌妻小寶神秘爹地求抱抱
魚的記憶隻有七秒,而我,卻愛了你七年。 ——喬初淺。 喬初淺從冇有想到,在回國的第一天,她會遇到她的前夫----沈北川! 外界傳言:娛樂圈大亨沈北川矜貴冷酷,不近人情,不碰女色。 卻無人知道,他結過婚,還離過婚,甚至還有個兒子! “誰的?”他冰冷開口。 “我……我自己生的!” “哦?不如請喬秘書給我示範一下,如何,自—交?”他一字一頓,步步趨近,將她逼的無路可退。 喬景言小朋友不依了,一口咬住他的大腿,“放開我媽咪!我是媽咪和陸祁叔叔生的,和你無關!” 男人的眼神驟然陰鷙,陸祁叔叔? “……” 喬初淺知道,她,完,蛋,了!
86.5萬字8 13911 -
完結471 章

萌寶尋爹:媽咪太傲嬌
母親去世,父親另娶,昔日閨蜜成繼母。 閨蜜設局,狠心父親將懷孕的我送出國。 五年后,帶娃回國,誓將狠心父親、心機閨蜜踩在腳下。 卻沒想到轉身遇上神秘男人,邪魅一笑,“老婆,你這輩子都逃不掉了……”
83.4萬字8 75541 -
完結84 章

敗給喜歡
多年后,雨夜,書念再次見到謝如鶴。男人坐在輪椅上,半張臉背光,生了對桃花眼,褶皺很深的雙眼皮。明明是多情的容顏,神情卻薄涼如冰。書念捏著傘,不太確定地喊了他一聲,隨后道:“你沒帶傘嗎?要不我——”謝如鶴的眼瞼垂了下來,沒聽完,也不再停留,直接進了雨幕之中。 很久以后,書念抱著牛皮紙袋從面包店里出來。轉眼的功夫,外頭就下起了傾盆大的雨,嘩啦嘩啦砸在水泥地上。謝如鶴不知從哪出現,撐著傘,站在她的旁邊。見她看過來了,他才問:“你有傘嗎?”書念點頭,從包里拿出了一把傘。下一刻,謝如鶴伸手將傘關掉,面無表情地說:“我的壞了。” “……” *久別重逢/雙向治愈 *坐輪椅的陰郁男x有被害妄想癥的小軟妹
24.9萬字5 8280 -
完結501 章

金牌律師Alpha和她的江醫生
ABO題材/雙御姐,CP:高冷禁.欲腹黑醫生omegaVS口嫌體正直悶.騷傲嬌律師alpha!以為得了絕癥的岑清伊“破罐破摔“式”放縱,三天后被告知是誤診!換家醫院檢查卻發現坐診醫生竟是那晚和她春風一度的漂亮女人。岑清伊假裝陌生人全程高冷,1個月后,江知意堵住她家門,面無表情地說了三句話。第一句:我懷孕了。第二句:是你的。第三句:你必須負責。——未來的某一天,江知意堵住她家門......
172.4萬字8 11794 -
完結1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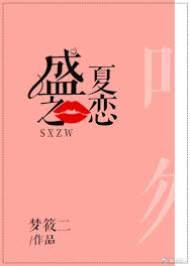
盛夏之戀
那天,任彥東生日派對。 包間外走廊上,發小勸任彥東:“及時回頭吧,別再傷害盛夏,就因為她名字有個夏沐的夏,你就跟她在一起了?” 任彥東覷他一眼,嫌他聒噪,便說了句:“煙都堵不住你嘴。” 發小無意間側臉,懵了。 盛夏手里拿著項目合同,來找任彥東。 任彥東轉身,就跟盛夏的目光對上。 盛夏緩了緩,走過去,依舊保持著驕傲的微笑,不過稱呼改成,“任總,就看在您把我當夏沐替身的份上,您就爽快點,把合同簽給我。” 任彥東望著她的眼,“沒把你當替身,還怎麼簽給你?” 他把杯中紅酒一飲而盡,抬步離開。 后來,盛夏說:我信你沒把我當替身,只當女朋友,簽給我吧。 任彥東看都沒看她,根本就不接茬。 再后來,為了這份原本板上釘釘的合同,盛夏把團隊里的人都得罪了,任彥東還是沒松口。 再再后來,盛夏問他:在分手和簽合同之間,你選哪個? 任彥東:前者。 那份合同,最終任彥東也沒有簽給盛夏,后來和結婚證一起,一直放在保險柜。 那年,盛夏,不是誰的替身,只是他的她。
25.4萬字8.18 759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