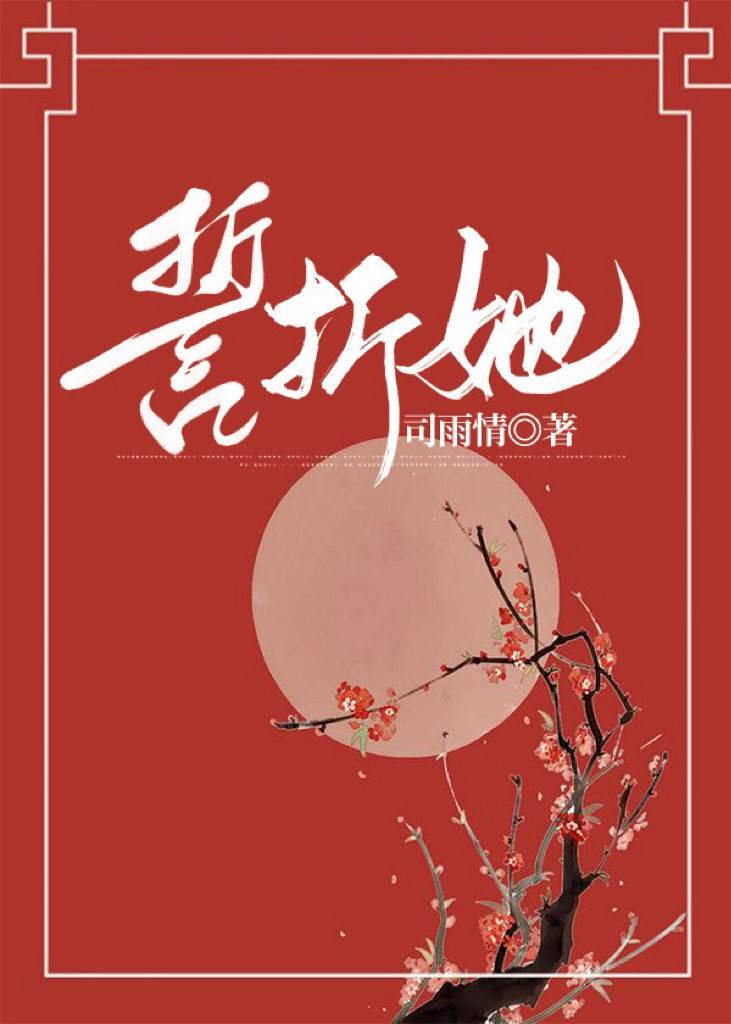《世子爺他不可能懼內》 第144章 遇難
禪房燈搖曳。
顧淮之面前德高重的方丈,堂而皇之的晦棋再晦棋。
哪兒對得起世人里‘得道高僧’之譽。
顧淮之耐心不足。被來下棋,已然是十分不虞。
他嘲諷:“外出云游一遭,這又是哪兒學的?”
方丈常年敲木魚的手,又了顧淮之的一顆棋,面上不見尷尬:“讓我幾個棋子怎麼了?幾年不見,顧小友還是這般小氣。”
“將軍府的公子,以往可都得讓我贏上幾局。”
顧淮之冷笑:“那你尋他便是。”
方丈有些憾,卻又知權貴之間互不相容的道理,可惜了,顧小友同慕小友以往如此要好,今兒卻恨不得拔刀相見
說著,他喝了杯茶:“這天底下就屬與你下棋最是暢快。”
顧淮之:……他!一點!也不!暢快!
還不如同阮蓁一塊兒用飯。看看還能耍什麼小心思近自己的。
如此一想,面對方丈平平無奇的臉,顧淮之頓覺索然無味。
“不下了。”
說著正要起。
“欸,怎麼說不下就不下了,世子爺這是輸不起?”
顧淮之:……
易霖看著熱鬧:……這方丈竟然比我還不要臉!
男人嗓音低沉,裹著漫不經心,敷衍:“嗯。輸不起。”
Advertisement
方丈:???
“我都這麼說了,你不該氣的同我下八百回合?”
嗤。
顧淮之冷笑,起往外走。
方丈手打棋盤:“這一局算我輸,顧小友再同我下一盤?”
易霖上前和稀泥:“他不陪你,你給我算個姻緣,我陪。”
方丈卻沒看易霖一眼。
只是對著顧淮之的背影道:“聽說這次與你前行的姑娘要在寺立牌位,顧小友再陪我下一盤,明日我親自做法。”
話音剛落,男人的腳步一頓。
又過了片刻,他臉很不好的轉走了回來。
方丈著佛珠,笑了。
瞧瞧,這人要親,倒有了些許人味。
“我觀你面相,想來這姻緣一世順遂。”
這話聽著倒是舒服,顧淮之臉好看了不。
不過。
他只是不咸不淡道:“還需你說?”
他看不起醫堪憂的池太醫,又哪里看得上這整日裝神弄鬼的方丈。
要不是他,盛祁南能整日里嚷嚷著出家?
重開一局后,顧淮之著黑棋油鹽不進:“死心吧,我絕對不會對你手下留。”
方丈:……
要不是顧淮之棋藝好,他早就把人趕出去了!
這顧淮之可不及盛祁南萬分之一。
即便,他真的想收盛祁南如此悟之人為徒。
Advertisement
可他擔心,顧淮之能將梵山寺給掀了,甚至!日后不會同他下棋。
方丈憾的嘆了口氣,而后示意易霖上前。
“施主想算姻緣?”
易霖顯然不死心:“對!您給我仔細看看,我可有機會趕在顧淮之面前親。”
方丈認真看了片刻,說的相當委婉:“姻緣之事由天定,施主不必給自施加力。”
易霖:……
顧淮之嘲諷:“呵。”
可到底,這盤棋不曾結束,就被急匆匆面凝重趕過來的暗七打斷。
暗七平日里多威武的人,此刻的都是的。
“主子,姑娘不見了!”
眼里都是自責,和數不完的擔憂。
可偏偏,不過是轉倒水的功夫,姑娘就像憑空消失那般。
對,就是憑空消失。
適才神自若倦懶的男子倏然起。作大的甚至掀翻了一旁的棋奩。
黑的棋子全部灑落一地。
他顧不上這些,只是直直看向暗七。
眸沉沉。
暗七的功夫和本事,他是放心的,不然也不會派到阮蓁邊伺候。
男人的面上卷著風雨俱來的波濤。
他像是覺得荒謬。
怎麼可能呢?
下頜線繃,一字一字帶著刺骨的寒,心口好似缺了一塊:“什麼做不見了?”
Advertisement
————
“怎麼,讓你送個姑娘過來,你卻一次送了兩個,也不心疼爺子吃不消?”
“藕的子便是爺點名要的,小的查過了,那是戚家不得寵的庶,年前曾出嫁,但花轎還沒過門,便被休棄,這樣的人,爺放心玩就是。玩死了想必也無人收尸。”
話音剛落,邊上的哭聲凄凄慘慘,愈發的讓人心生恐懼。
“這小蹄子,我還沒弄,就哭這樣。另外那個呢?”那人說著骯臟的話。
阮蓁疼的睜不開眼,后背濡,染了裳。
眼只有昏暗的燈,還有四周冷的墻。
室全封閉,不知出口。
屋的味道腥的很。
渾渾噩噩間,眼底閃過些許清明,猛然抬眸。
“那個不省人事的小娘們是自己掉進了機關,這可怨不得小的,生的那般姿,自然得給爺留著。”
“可查了,什麼份?”
“爺放心,那一素,渾上下也就那張臉值錢,臨安的貴個個都是穿金戴銀,就連那戚家庶發上都有大金簪子,那人怎麼可能有份!”
回話的依舊是男聲。他殷勤的給躺在貴妃塌的胖男人敲著。
說著奉承的話。
Advertisement
“再說,就連那太師府的正房太太,爺都嘗了滋味,還不是照樣屁都不敢放一個,您有什麼可擔憂的?”
這一句話顯然讓藍男子聽的百般舒服。
他頭大耳的,眼珠子綠豆般顯得十分小。
“不錯,那人如今還有了孕,就連打胎都不敢。人前高貴,人后還不是在爺下哭。”
說著,笑的得意又猥瑣。
“都說梵山寺求子靈驗,想來爺也是出了一份力的。”
這幾番對話下來,阮蓁又怎會不知兩人的機。
可沒想到,更惡心的還在后頭。
隔著屏風,瞧得并不真切,只依稀看著那站著的,爬到貴妃塌男人上。
深款款:“我給爺辦了如此好差事,您可不能忘了小的。”
他的嗓音很快化為一道愉悅的吸氣聲。
再往下的,污穢不堪。
兩個男人……
呼吸一滯。水盈盈的眸子布滿了驚恐。
子顧不上疼,往后。
甚至渾都在抖。
偏偏邊上的哭泣聲一下又一下的加深的恐懼。
猜你喜歡
-
完結1996 章
神醫農女:買個相公來種田
外科聖手穿越古代農家,逗逗相公鬥鬥渣!
344.2萬字8 162026 -
完結501 章

天才萌寶腹黑娘親
一朝穿越,變為農家女,家徒四壁也就算了,為何身邊還帶了個拖油瓶? 幾經波折,才發現原來與她生出這個拖油瓶的男人一直在她身邊,更讓她大跌眼鏡的是,這個男人的身份,並不尋常……
88.4萬字8 15562 -
完結11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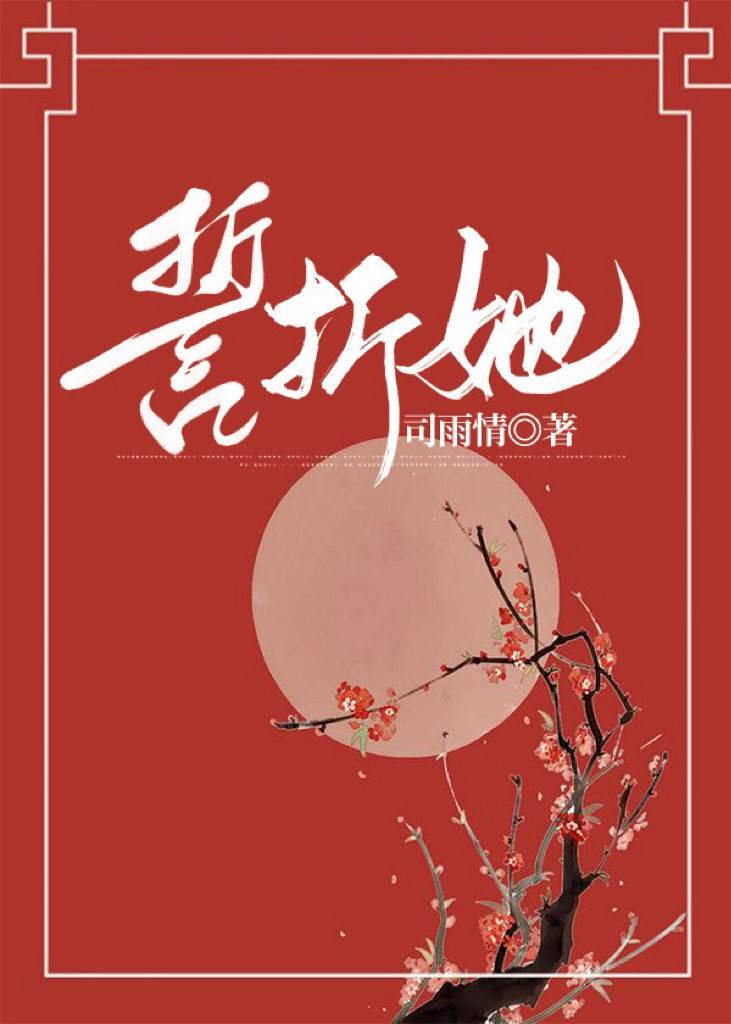
妄折她
昭華郡主商寧秀是名滿汴京城的第一美人,那年深秋郡主南下探望年邁祖母,恰逢叛軍起戰亂,隨行數百人盡數被屠。 那叛軍頭子何曾見過此等金枝玉葉的美人,獸性大發將她拖進小樹林欲施暴行,一支羽箭射穿了叛軍腦袋,喜極而泣的商寧秀以為看見了自己的救命英雄,是一位滿身血污的異族武士。 他騎在馬上,高大如一座不可翻越的山,商寧秀在他驚豔而帶著侵略性的目光中不敢動彈。 後來商寧秀才知道,這哪是什麼救命英雄,這是更加可怕的豺狼虎豹。 “我救了你的命,你這輩子都歸我。" ...
40.2萬字8.18 66353 -
完結622 章
重生后手撕婚書,嫁給前任他親叔
衛靈犀一睜眼,回到了及笄那年。那個狼心狗肺的負心漢蕭子煊再次登門要抬她回府做妾。上輩子,她為愛奮不顧身地跟了他,換來的卻是衛家滅族,自己被磋磨,屈辱一生。臨了,還被他送上了蕭珩那個權勢滔天的男人的床榻。這輩子,做妾?呸!她要正大光明嫁給那個男人,雪前世屈辱,護衛府周全。新婚次日,蕭珩溫柔地握著她的手,容顏冷淡的看著他:“子煊,這是你嬸母。”她嘴角勾著淡笑,看著他垂首斂目,彎腰恭敬地喚了她一聲:“嬸母。”
114.9萬字8 12263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