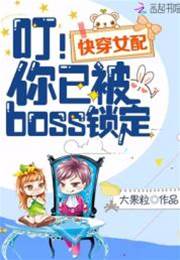《紈绔世子妃》 第一百一十二章 乍聞驚喜
天下黑了三日三夜才恢復明。
百姓們從恐慌中離出來,對著天地跪拜,千恩萬謝佛祖保佑。
當日,夜輕暖出戰攻打南凌睿的四十萬大軍,因為日食被阻,半路撤了兵。三日后,一待天明,迫不及待地調兵遣將,打響了到達北疆之后的第一戰。
南凌睿將四十萬大軍從八荒山拉到了北疆,堂而皇之地踩踏著北疆的地盤。見夜輕暖出手,也毫不客氣地還擊。
兩軍鋒,大約是天黑了三夜才恢復明,兩軍士兵的狀態都不太好,沒有多輸贏。
第一戰草草結束。
夜輕暖不甘心,再度重整軍隊,日夜訓練,準備再開戰。
南凌睿到也不著急,慢悠悠地等著夜輕暖,不手,他也不出兵,只讓四十萬大軍盤踞在北疆地界的第一座城池外。
十日之后,夜輕暖再度出兵。
南凌睿迎戰。
這一戰,又是溫水青蛙,不溫不火,沒有任何輸贏可談,傷亡也不大。
一晃又是十日。
夜輕暖再度出兵,結果又是與前兩次一樣。
夜輕暖雖然下狠了心要除掉南凌睿和他的四十萬兵馬,軍紀嚴明地整頓大軍,鼓舞士氣,但還是奈何不得南凌睿,心中氣悶,也無可奈何,只另想辦法。
正在絞盡腦想辦法的時候,這一日,吃過早飯,忽然嘔吐起來。
北青燁這些日子一直纏在夜輕暖邊,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實打實的一個好駙馬。如今見夜輕暖嘔吐不止,立即吩咐人,“來人,去請大夫!”
“請大夫做什麼?我不過是胃口不適。”夜輕暖三次攻打南凌睿不勝,心煩躁,語氣也不如這些日子以來對北青燁和緩了。
北青燁看著,“你這樣可不像是不適。”
Advertisement
夜輕暖心思一,直直地看著他,“那你以為是如何?”
“我宮里以往有妃嬪懷有孕的時候,就是這般。”北青燁溫地看著。
夜輕暖面一變,瞬間被懷有孕幾個字驚得呆住了。大婚以來,北青燁每日夜里都纏著做那等事,即便厭惡,但是也得忍著。既然選擇嫁給他,就要迎合他,他雖然無用,也是一國之君,他后還是有人馬的,清楚地知道,北疆有云淺月的人和容景的人,但是都埋在暗,不知道哪些人是,沒有他和他的將士在后的話,無兵力,怕鎮不住北疆的將領,所以,一直對他的予取予求不言語半個字。如今乍聞懷孕,才想起,和他大婚圓房近兩個月了,他日日索取,是會有喜……
“高興得不會說話了?”北青燁將抱在懷里,溫地著的臉笑道:“我如此賣力,你自然該有孕了。這也不奇怪。”
夜輕暖腦中嗡嗡直響,聽不清他說什麼。
北青燁的手從臉上下,到小腹,來回著,“他若是男孩,就是我北青燁的三皇子,若是孩,就是十公主。”
夜輕暖剛回過些神,便聽到了這句話,突然一把推開他,眸凌厲,“你剛剛說什麼?”
“我說他若是男孩,就是我的三皇子,若是孩,就是十公主。”北青燁重復了一遍。
夜輕暖臉霎時慘白如紙,抖地看著他,“你……你在北崎有兒?”
北青燁忽然笑了,看著夜輕暖道:“公主,你不會不知道吧?我有兩個皇子,九個公主,都是后宮妃嬪所生。你放心,我沒娶皇后,如今北崎歸順了天圣,以后更不會有皇后了。”
Advertisement
夜輕暖子栗,蒼白的臉突然鐵青,指著北青燁忽然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皇上后宮本來就是三千佳麗,北崎雖然是小國,但是后宮里幾個人還是有的。公主這是什麼表?像是看負心漢一般的神看著我。”北青燁挑眉。
夜輕暖忽然眼前一黑,子向地上倒去。
北青燁眼明手快地手接住,看著懷里纖細的人兒,角勾了勾,慢悠悠地對外面喊,“傳大夫!”
“是!”外面有侍立即應聲去了。
北疆的戰場因為夜輕暖懷孕昏迷,暫且擱置下來。
天下終于恢復了短暫的平靜,蘭城和馬坡嶺從那匆匆一戰后,也未起兵戰。
容景從四個月前那一日從蘭城總兵府回來后,便每日有半日站在中軍帳外看著東方,眸是誰也解讀不懂的期盼和思念。
這一日,已經是云淺月從東海離開前往云山的第五個月,算起來,已經離開天圣,離開他整整半年有余。
離開的時候,正值五月末,春夏替,如今已經十一月末,了深秋。天圣國土遍地已經秋葉飄零,萬蕭索。軍中已經開始士兵冬的棉。
而容景依然是一襲月牙白錦袍,遠遠看來,分外清冷單薄。
“公子,您再這麼站下去的話,都快變夫石了。”墨飄而落,膽子地戮了戮容景的后背,笑嘻嘻地道。
容景忽然轉過,盯著墨看。
墨一個高蹦出老遠,收了嬉笑,張地看著容景,“公子,您這麼看著屬下……”
“是不是有消息了?”容景打斷他的話,聲音抑著緒。
墨一怔,訝異地問,“您怎麼知道?”
容景眉眼瞬間如盛開了的煙花,璀璨得刺眼,大約是極喜,子驀地僵在原地,表也定格在這一瞬。
Advertisement
多日夜孤枕難眠,多日夜心心念念,多日夜擔驚怕,多日夜期待變絕,多日夜等待得幾近崩潰,多日夜怕萬一不回來,他該怎麼辦……
如今終于有消息了!
終于有消息了!
這一刻,誰也會不到他的心!
他曾經對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當做三百六十五年來過,每一天就是一年,他和會在一起千年萬年,天長地久。
可是這半年里,他恨不得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恨不得一天不是一年,半年一百八十多天,他過了一百八十多年,每一天都如在苦海中煎熬,終于會了度日如年的說法。
“公子,您……你不是高興得傻了吧?”墨上前一步,試探地喊了一句。
容景仿若不聞。
墨又上前一步,手戮了戮他,見他還不,他有些傷又憂心地嘆息道,“公子啊,您這半年來,是有些傻氣,如今這模樣,更是傻氣,主母若是回來看到你這個樣子,屬下擔心怕是不要你了……”
容景回過了些神,似乎極力制著緒,但聲音還是控制不住地輕,“……如今如何了?什麼時候回來?”
墨見容景如此模樣,有些心疼,也不敢再與他拿這件事開玩笑,主母離開,生死未卜這麼半年來,不止公子日日盼著,擔驚怕著,他們跟在公子邊的這些人也是日日盼著,擔驚怕著,甚至是整個墨閣,整個馬坡嶺大營,整個臣服于公子的子民們,都期盼著。幸好蒼天不負他們的期盼。他正了,低聲道:“屬下剛剛得到東海的消息,說玉太子去了云山,但被擋在了云山外,不過得回一個消息,說上主和主母安然無恙地從萬年寒池下出來了,就是目前還在云山的云宮昏迷不醒著。”
Advertisement
“的毒是不是解了?”容景輕聲問。
“定然是解了!那樣的毒,若是不解的話,主母怎麼可能活著出來?”墨想著公子腦子真是被主母折磨得不靈了。
容景忽然仰頭看天,臉上是從來未曾出現的激神,喃喃道:“蒼天厚待容景。”
墨看著容景,想著也不怪公子得到主母的消息如此神,他在公子邊,是親眼看著他這半年來其實是在靠著一口氣苦苦地支撐著,如今乍然得到消息,焉能不喜?連他得到消息的時候,都喜得不知如何是好,生怕做夢不真實,抓著東海來的那名衛問了好幾遍,直到將那衛問得無奈,他才相信是真的,急忙回來告訴公子。
許久,容景從天空收回視線,神鎮定了幾分,問道:“說什麼時候會醒來嗎?”
“據說主母和上主從萬年寒池下出來的時候是月前‘天狗食日’的時候,到如今算起來也有一個月了。據東海玉太子邊來的衛說,云山掌刑堂三長老說主母和上主月余應該會醒來,但他們如今靈力不及主母,也不敢保證時間是否會更長些。”墨立即道,“總之主母肯定是無恙了,公子不必擔心了。”
容景點點頭,低聲道:“活著就好!”
墨也想著主母活著就好,活著,許多人都能活,若是真出事,許多人都活不。
“你去將玉太子那名送信的衛來,我親自問他。”容景看向東方,又對墨吩咐。
“公子,那名衛從東海奔波來,累得昏過去了,屬下將關于主母的所有消息都問出來了,您有什麼問題,問屬下吧。”墨想著不愧是公子,連主母的半消息都不放過。
容景蹙眉,毫不憐惜地道:“昏過去就潑醒他。”
墨角了。
容景轉進了中軍帳,步履一改半年來的沉重,恢復了往日的輕緩優雅。
墨想著做衛的都是命苦的,那位仁兄只能留待日后玉太子勞他了,他不是自己弟兄,為了公子,潑醒就潑醒吧!轉去了。
容景進了中軍帳后,站在桌案前,看著桌案上的那盆并牡丹。
這一株并牡丹正是曾經榮王府紫竹院那一株,當時云淺月特別喜歡,日日為它澆水剪枝。后來要將紫竹院的牡丹移去皇宮,他料準了,先一步移出了這株牡丹,半年前離開馬坡嶺,他便將這株牡丹挪來了軍營,眼看著牡丹一日比一日枯萎,就如的生命在一點點兒的消逝一般,在全部枯萎的時候,他已經絕。沒想到一個多月前日食前一日,它忽然從底部發了芽,這株牡丹,曾經被夜輕染掌風所傷,被用靈力救了回來,與的氣息是有些關聯的,所以,它重新長出新芽,他才敢那麼肯定地對夜輕染說還活著。
但是一株牡丹,一株新芽,終究代替不了真實活著的消息。
他這一個月來,依然是日日惶恐不可終日,日日期盼夜不能寐,心里真的了夫石,只著云山的方向,盡自己平生所有的意志力控制自己耐心等待。
如今,終于等到了活著的消息!
對他來說,還有什麼比得上活著更好?
“公子,人我給您帶來了,他可是玉太子手下除了言棠外的得力助手,您可溫些詢問啊。”墨拖著一個渾淋淋的人進來,正是玉子書從不離近侍候的另一衛秋葉。
容景“嗯”了一聲,慢慢坐下,看著秋葉對墨道:“賜坐!”
秋葉臉極苦,從太子在云山得到消息,不放心飛鴿傳書,怕被夜輕染攔住或出什麼事,命令他親自跑一趟,他日夜兼程,馬不停蹄,一日就吃一頓飯,喝幾口水,終于半個月趕來了這里,已經困得睜不開眼睛,剛睡下,就被潑醒了,心中雖然哀怨,但想著這位可是景世子,自家太子的知,二公主的駙馬,是個黑心的主,不能得罪,只有氣無力地道:“在下一水,怕臟了世子的地方,您問吧,在下站著說,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容景點點頭,沒有潑人家一水的不好意思,事無巨細地問了起來。
其實秋葉對于云山的況也是知道得也極,只能將他半個月前跟著太子殿下找去了云山,走到黑風林外,被云山掌刑堂的大長老攔住,將聽到的太子殿下和云山大長老在黑風林外的對話說給容景聽了。
猜你喜歡
-
完結57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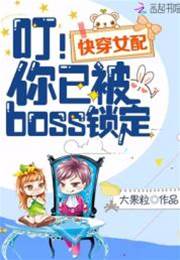
快穿女配之你已被boss鎖定
阮綿綿隻想安安分分地做個女配。 她不想逆襲,也不想搶戲,她甘願做一片綠葉,襯托男女主之間的純純愛情! 可是為什麼,總有個男人來攪局?! 阮綿綿瑟瑟發抖:求求你,彆再纏著我了,我隻想做個普通的女配。 男人步步逼近:你在彆人的世界裡是女配,可在我的世界裡,卻是唯一的女主角。 …… (輕鬆可愛的小甜文,1v1,男主都是同一個人)
103萬字7.83 14294 -
完結1218 章
快穿之大佬又瘋了
《快穿之大佬又瘋了》修鍊狂魔南鳶拐了一隻神獸,助她穿梭於三千世界,收集信仰之力。向來只殺人不救人的南鳶,從此洗心革面,做起了好人。可惜,好人難當。當成兒子來養的小怪胎搖身一變成了魔域大佬,發瘋地想圈養她?恐女自閉癥晚期的便宜夫君突然不恐女不自閉了,發瘋地纏著她生娃娃?就連隨手撿個死物,都能變成果體美男躺床上,陰測測地求負責?後來南鳶啥都不想養了,一心只跟男主battle。結果,男主他、他也瘋了。……南鳶面無表情:「大佬,你身上的氣息熟悉得讓人討厭。」大佬波瀾不驚:「我的世界給你。你,給我。」
218.1萬字8 12496 -
完結699 章

農門醫妃:團寵福女她美又颯
特種軍醫林染穿成古代農女,以為自己是一個沒爹沒娘的小可憐,卻不想她的親人個個是大佬不說,還把她寵上了天。 娘親:「染染從小在外面長大,受苦了。 娘親的銀子隨你花,想去哪就去哪」 父親:「都怪爹不好,沒有保護好你,害你從小在農家長大。 爹爹送你尚方...
123.2萬字8 13768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