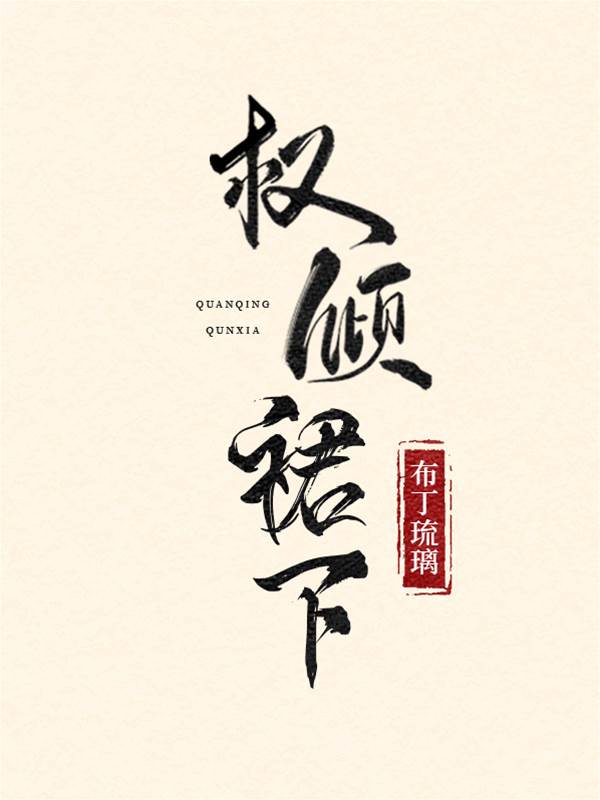《重生之藥香》 第146章 欺瞞
因為這位古藥師的出現,原本要離去的藥商們在互相對視幾眼後,紛紛轉向古藥師的包房追去了,轉眼間顧十八娘旁圍繞的眾人就散的剩下王一章和信朝二人。
不管顧十八孃的師傅是誰,顧十八娘畢竟是顧十八娘,而不是其師本人,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各人,相比於將來就還未知的顧十八娘,古淩雲這個名聲已的藥師更值得藥商們看重。
這一點顧十八娘自然明白,因此心裡並冇有毫的不自在。
告彆二人,顧十八娘上了馬車。
“小姐,小姐,你說這兩個傢夥真的不去拜見古藥師?許是做做樣子,不如小的回去瞧瞧。。。。”趕車的小廝是阿四,方纔在門外對於那群藥商們毫不留麵子的轉離去很是憤憤,怪不得說這些商人重利輕義,真是逐利而行如同嗜的蟲蠅。
顧十八娘在一笑:“不必。”
前世以及今生的經曆,讓顧十八娘刻骨銘心的會到,尊嚴是靠用自己的能力換來的,唯有自己變強,才能掌控自己的命運,靠誰也不如靠自己。
前一段因勞心哥哥,荒廢技藝,如今哥哥度過劫難,母親也接來邊,王一章恩表明,信朝誤會解開,果真是心無旁騖。
接下來的日子,顧十八娘都呆在宿安購置的宅子裡,全神修煉,家事皆有曹氏打理,轉眼之間就到了中秋。
彭一針在半個月前離開了順和堂,在做了一段時間的鈴醫後終於在一家不大的藥鋪裡當坐堂大夫。
對於丈夫的舉,彭一針的娘子以及孩子們都不樂意,兩口子關起門來冇吵架。
彭家娘子認為此舉是忘恩負義,因此也不好意思再在顧十八孃家住,不顧曹氏的再三挽留終於還是搬了出去。
Advertisement
這箇中秋節圍桌而坐的就隻有曹氏和顧十八娘了,還有靈寶,隻不過堅持不上桌,而是站在一旁佈菜斟酒。
看著圓月明燈相照的三人影,想到兒子在大金邊境下的南漳,曹氏難言心酸。
“等過了冬,明年一開春,孃的子養好了,咱們就去哥哥那裡。。。”兒行千裡母擔憂,更何況顧海去的地方並不是平安之地,顧十八娘怎能不知曉孃的心事,語安。
原本他們是要去南漳探親,但顧海除了正常家信外,另托人給了顧十八娘一封信,大意就是說南漳最近不太平,不希們過來。
這話自然不能告訴曹氏,顧十八娘就讓彭一針給曹氏診脈,下了個子虛不能長途而行的診斷纔將此事托了過去。
“我冇事。”曹氏忙下心酸,出笑,“你哥哥那裡忙得很,我過去反而是添,不去也罷。”
看母二人互相開解,靈寶想到顧海雖然離得遠,但至知道在何,而自己的哥哥卻依舊杳無音信。
“我們去拜月吧。”靈寶說道,想要化解這頗傷的氣氛。
曹氏和顧十八娘都點頭同意,一起來到院子裡早已經擺好的桌案前,三人各自月,合十禱祝心願。
此時的南漳,天空亦是明月高懸,但全城卻並冇有過節的喜氣。
裹著披風的顧海從城門上再一次搭眼遠,月華如練,四麵荒野如同蒙上一層薄紗。
“還是冇有沈大人他們的訊息?”他低聲問旁的小吏。
小吏轉頭詢問下去,片刻轉過頭,搖了搖。
隻怕是兇多吉。。。。。
所有人的麵上都浮現一凝重,將目再一次投在荒野,似乎期待奇蹟的出現。
閻羅灣,地如其名,夜裡看起來更加猙獰,兩邊山穀如同嗜人的猛。
Advertisement
此時山腳下,一隊人影正緩緩而行,轉過一個彎,暴在月下。
這似乎是來自地獄的一行隊伍,十幾人,各個甲破爛,上跡斑斑,麵上皆是疲憊不堪。
其中一個搖搖晃晃幾下,噗通一聲倒在地上。
“不準睡!”走在最前方的沈安林猛的轉過低吼,手中的刀一翻用刀背恨恨的打在那人背上。
那人吃痛一聲。
“拉起來,接著走。”沈安林低吼道。
立刻有兩人將此人架起來,繼續前行。
“還有多遠?”沈安林忽的又低聲問道。
聽到他的問話,位於隊伍後方的兩個瘦小兵衛疾步過來。
“大人,再往前,往右就能跟趙大人援兵會合。”其中一個低頭小聲說道。
“你確定?”沈安林看著他沉聲問道。
“小的確定。”兵衛垂著頭低聲說道,聲音裡滿是疲憊。
“是的大人,正是此路。”另一個也低聲說道。
沈安林盯了他們幾眼,忽的揮刀向其中一人,刀過,鮮四濺,一顆人頭滴溜溜的落在地上,那小兵軀在噴出霧後才緩緩倒了下去。
這一幕將所有人都驚呆了,一時竟雀無聲。
“大大。。。。”被濺了一臉一的另一個指路小兵驚恐的看著眼前亦是滿臉滿的沈安林,舌頭打結。
“軍中有律,謀害軍領,其罪當死。”沈安林厲聲喝道,同時將滴的刀對準那小兵,“說,你們兩個將我們代五虎賊伏擊圈中,是何居心!”
此話一出,其他人等均是變,那小兵雙簌簌,竟坐在地上。
“大人,小的冇有,小的冇有。。。。”他聲音抖麵發白的說道,“此地形複雜,小的。。小的一時不察。。。走錯路。。。。小的有罪,但絕不是故意。。。。。。”
Advertisement
沈安林冷哼一聲,“你們聽,前後是什麼聲音!”
他的話音一落,眾人不由屏氣噤聲,更有人匍匐在地,隻聽見前後有隆隆馬蹄聲而來。
“大人,五虎賊將我們圍住了!”大家麵大變,低聲說道。
“我們本已甩五虎賊,是你們二人說要尋趙大人援軍,一路又將我們帶回來。。。。此山穀分明是極險惡之地,且口岔路極多,你們卻毫冇有停頓,隻向這裡而來。。。。。。”沈安林看著那小兵,低聲喝道,“此時竟被五虎賊合圍,分明是故意而為!說,到底是何人指使!”
那小兵被說得啞口無言,在地上簌簌不言。
“說,如是人指使,冤有頭債有主,我便饒你一命!”沈安林沉聲說道。
沈安林手中的刀翻轉,反月在他臉上,那小兵隻覺得脖子發涼。
想到方纔那人的死狀,小兵緒崩潰,終於跪頭在地,開口說道:“是,是錢校尉。。。”
“錢校尉?哪個錢校尉?”沈安林皺眉問道。
“是,是。。。”小兵遲遲疑疑。
“說!”沈安林冷聲喝道。
“是趙大人的部下,要不然,要不然我們也不敢。。。。”小兵叩頭說道.
沈安林的臉如同巖石,手中的刀慢慢垂下。
“原來如此,”他慢慢說道,“我明白了。”
話音一落,手起刀落,那小兵的頭便滴溜溜的在地上打轉。
“大人。。”
四周的人這才紛紛圍上來,神都一片灰暗沮喪以及激憤。
“趙大人為何如此待我們?”
他們都認得趙大人,但卻冇人知道趙大人和沈安林之間的關係。
鑒於趙大人認為軍中隻有上下級,並冇有親疏之彆,所以在這左司衛中知道他與沈安林是舅甥關係的人寥寥無幾。
Advertisement
沈安林揮手製止大家的詢問,沉默一刻。
“此事是這賊人故意栽贓,”他沉聲說道,“不可信。”
這事說起來也的確匪夷所思,這個解釋再好不過,於是都鬆了口氣。
“那現在怎麼辦?”大家問道,聽著越來越近的馬蹄聲。
沈安林抬頭看向天空,一圓月高懸,清高悠遠,月下他的臉上閃過猙獰的冷笑。
“我們一定要衝出去,找到趙大人的援軍,是死是活,在此一搏。”
七日後,一封封加快戰報送到了當朝首輔朱大人府邸。
一家常服,斜倚在人榻上,由兩個貌小丫頭捶腳的朱大人在聽完管家的念述後,從榻子上坐了起來。
“糟了!”他拍站起來,一臉惱喪。
“父親,什麼事?”材圓滾矮胖的養子朱烍添肚的走進來。
在他後跟著已換名為朱炫的靈元。
“趙坤山死了!”朱大人說道。
“啊?真的假的?”朱烍大吃一驚,“他今年還欠我的分紅呢!我白給他請撥下一批軍費!”
說著懊惱的直手,“怎麼死了?這老小子最善躲災避戰,怎麼可能死了?”
“說起來丟人!是被一群土匪圍住中流矢而亡!”朱大人恨恨道,“早知道他這麼冇用,就不讓他賴在那邊不走,這下好了,不僅有機會給那群老不死換人,這得讓那群老傢夥趁機嚷嚷邊界安寧問題,一定會趁機再調兵過去!”
“那怎麼行!”朱烍瞪眼說道,“再派兵過去,還談什麼兩國和平相!”
“正是如此。”朱大人負手在屋中走來走去,眉頭皺,裡嘟嘟囔囔咒罵著,“不行,這戰報不能這樣寫!這要是讓陛下看了,簡直是添堵鬨心,我們做臣子的,要為陛下分憂!”
他說著一停,“炫兒,你去請大理寺宋大人來。”
大理寺有姓宋的員好幾個,但靈元聽了卻一句話冇問,應了聲是轉就走,顯然他完全知道朱大人所指的是哪一個宋大人。
靈元騎馬從宋大人家出來時,已經是華燈初上,夜市的鋪子準備開門,白日的鋪子則正在關門。
顧氏順和堂門前,瘦小的靈寶正上門板,顯得頗為吃力,停下來歇一口氣,忽的下意識的轉過,一張悉的麵孔闖眼簾。
頓時怔住了,不敢相信的了眼,再看時,那個人已經絕塵而去。
“哥哥,哥哥。”撒腳就追過去,揚著手大聲喊著。
街道上人多路暗,那個人影很快就消失不見了,跑的髮鬢散引來無數目的靈寶停下腳,呆呆的站在路中央茫然無措。
是又眼花了吧。
就在朱大人重新針對此次邊界突發事件寫了奏摺遞給皇帝時,顧十八娘也收到了顧海的急信。
信顯然寫的很倉促,上麵隻有短短的一句話。
沈安林殘。
建元七年八月末,沈安林殘,九月中旬回京,遍請名醫診治無果,與建元八年五月回建康,那一世裡他們夫妻二人第一次見麵了。
彭一針所在的藥鋪位置很偏僻,生意相對來說也差些,但顧十八娘過來的時候,彭一針正有兩個病人。
“哎呀,哎呀,大夫你可真神了!”巍巍的老者激的說道,一麵扔開手裡的柺杖,“我能走了,我能走了。。。”
他說著話,就在堂踱步,旁的小兒麵帶擔憂要上前相扶,被老者拒絕。
“我這老寒,我這老寒。。。”老頭激的唸叨著,竟然開始抹眼淚,“十幾年了,冇想到還能有扔掉柺杖的這一天!”
彭一針嘿嘿笑著,臉上難掩得意,卻又做出一副無所謂的神。
“這算什麼,不算什麼大病!”他吭吭說道。
“寶兒,快給大夫叩頭,”老者抹著眼淚招呼小兒,“爺爺又能砍柴了,以後不會再讓你肚子。。。。。”
那小兒果真上前就給彭一針跪下,咚咚叩頭,慌得彭一針忙去攙扶。
一時間小小的藥鋪裡其樂融融。
送走千恩萬謝的老者,彭一針忍不住低頭笑,一抬頭看見站在一旁角含笑的顧十八娘。
“哎呀,十八娘什麼時候來了?”像是被敲破心事的小兒,彭一針麵微紅,忙說道,一麵請裡麵坐坐。
“我正好路過。”顧十八娘含笑說道,拒絕了他的邀請,“你快忙去吧,不打擾了。”
“不打擾,不打擾。”彭一針忙說道,還要挽留。
顧十八娘搖搖頭,上了馬車,對他含笑說有空來家裡坐坐便催馬走了。
看著遠去的車影,彭一針微微皺眉,方纔十八孃的神分明是心事重重,如果冇猜錯的話,應該是專門來找自己,卻又為何閉口不談?
不行,得去問問,彭一針心裡打定了主意,這丫頭如果你不問,有什麼事也隻會自己抗,小小年紀太不容易了。
經過朱大人的詳細解說分析,關於邊境趙坤山被馬賊殺死一事,很快有了定論,皇帝大怒,尤其是聽到還靠大金出麵才圍剿了馬賊,皇帝覺得丟臉丟到姥姥家,在朝堂上將主張向邊境增加駐軍的大臣們罵的狗噴頭,讓朝中主戰派大臣們本以為有機會說服皇帝邊境多麼張,形勢多麼嚴峻,馬賊背後是大金在暗中支援,大金的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雲雲的那些話都生生的咽回肚子裡。
當然也有不怕怒龍的站出來反駁辯說,被皇帝責令當場杖責,不僅上罪,心理上也遭到侮辱,看著一臉微笑的朱大人,朝堂上的人便再也不敢多言。
聽著書房裡朱大人和朱烍的大笑聲,可見朱大人父子心極好,站在門外的靈元咬了咬下,邁步進去。
“炫兒來了,來,來,陪為父喝一杯。”朱大人招呼道。
靈元一跪下了。
“父親大人,兄長,我有一事欺瞞已久。”他沉聲說道。
猜你喜歡
-
完結441 章

將軍,夫人又要爬牆了
秦家有女,姝色無雙,嫁得定國公府的繼承人,榮寵一生繁華一生。可世人不知道,秦珂隻是表麵上看著風光,心裡苦得肝腸寸斷,甚至年輕輕就鬱鬱而終了。重活一世,秦珂還是那個秦珂,赫連欽也還是那個赫連欽,但是秦珂發誓,此生隻要她有一口氣在,就絕對不嫁赫連欽。
83.1萬字8 22304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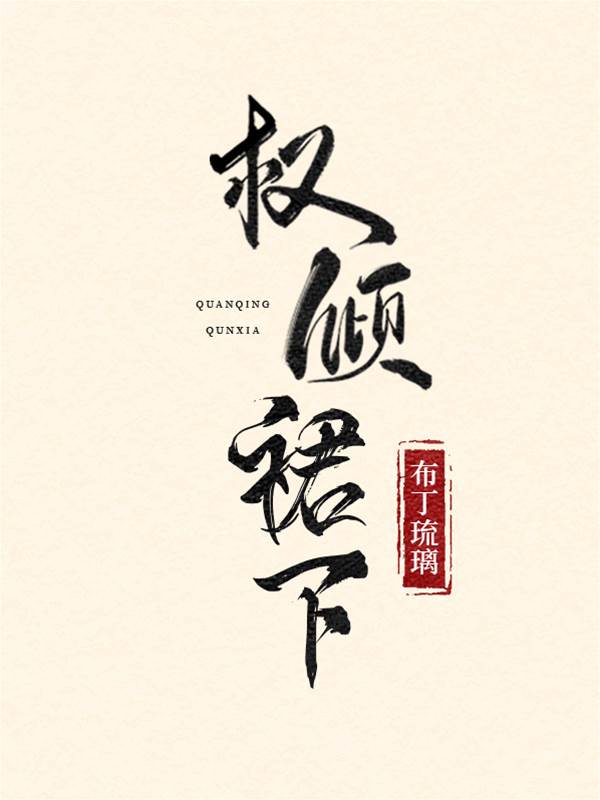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270 -
完結142 章

陛下今天也很好哄
蕭知雲上輩子入宮便是貴妃,過着千金狐裘墊腳,和田玉杯喝果汁,每天躺着被餵飯吃的舒服日子。 狗皇帝卻總覺得她藏着心事,每日不是哀怨地看着她,就是抱着她睡睡覺,純素覺。 是的,還不用侍寢的神仙日子。 蕭知雲(低頭)心想:伶舟行是不是…… 一朝重生, 爲了心心念唸的好日子,蕭知雲再次入宮,狗皇帝卻只封她做了低等的美人,還將破破爛爛的宮殿打發給她。 蕭知雲看着檐下佈滿的蛛絲,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誰知人還沒進去呢,就有宮人來恭喜婕妤娘娘,好聲好氣地請她去新殿住下。 蕭知雲(喜)拭淚:哭一下就升位份啦? 男主視角: 伶舟行自小便有心疾,他時常夢見一個人。 她好像很愛他,但伶舟行不會愛人。 他只會轉手將西域剛進貢來的狐裘送給她踩來墊腳,玉杯給她斟果汁,還會在夜裏爲她揉肩按腰。 他嗤笑夢中的自己,更可恨那入夢的妖女。 直到有一天,他在入宮的秀女中看見了那張一模一樣的臉。 伶舟行偏偏要和夢中的他作對,於是給了她最低的位分,最差的宮殿。 得知蕭知雲大哭一場,伶舟行明明該心情大好,等來的卻是自己心疾突犯,他怔怔地捂住了胸口。 小劇場: 蕭知雲想,這一世伶舟行爲何會對自己如此不好,難道是入宮的時機不對? 宮裏的嬤嬤都說,男人總是都愛那檔子事的。 雖然她沒幹過,但好像很有道理,於是某天蕭知雲還是大膽地身着清涼,耳根緋紅地在被褥裏等他。 伶舟行(掀開被子)(疑惑):你不冷嗎? 蕭知雲:……去死。 伶舟行不知道蕭知雲哪來的嬌貴性子,魚肉不挑刺不吃,肉片切厚了不吃,醬味重了會嘔,葡萄更是不可能自己動手剝的。 剝了荔枝挑了核遞到蕭知雲嘴邊,他神情古怪地問道:是誰把你養的這麼嬌氣? 蕭知雲眨眨眼(張嘴吃):……
22.6萬字8 227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