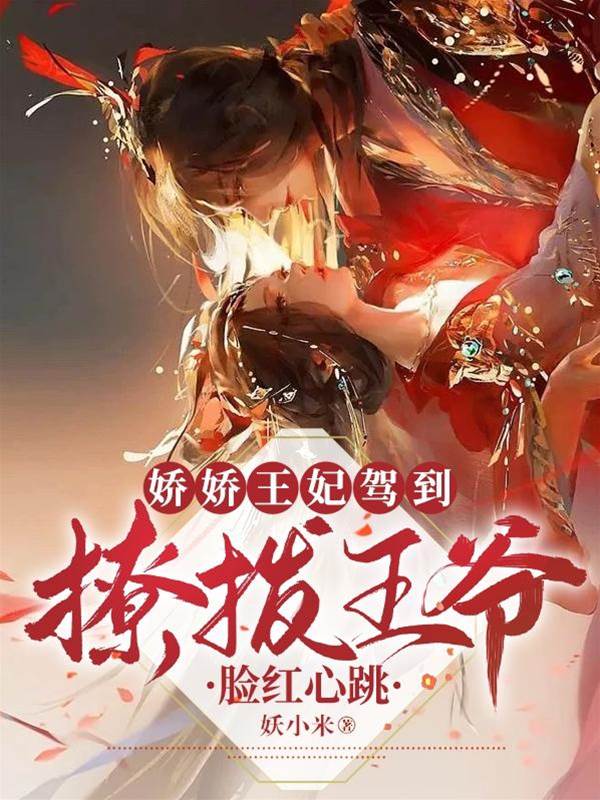《重生嫡女狠絕色》 第70章 好消息,壞消息
京城平江河畔,有條街臨水而建,街中青樓院遍地,而其中,數萬花樓名頭最盛。
夜暮降臨。
華燈初上。
古古香的萬花樓大紅燈籠高掛,竹聲聲,鶯鶯燕燕好不熱鬧。
二樓最裏的雅間,著鏤空紗的子轉珠袖,掩麵眺,如同一隻花蝴蝶般,極盡嬈的纏著旁的男子。
李錦夜一手端著酒杯,一手在子的腰間輕輕婆娑。
“爺,玉兒口不舒服,您給。”
“是口,還是心口,你倒是說清楚了。要是口,還能一,要是心口,那可就不是一這麽簡單的了!”
“爺好壞!”子拳輕敲,杏眼瀲灩流轉。
你好浪!
張虛懷一襲青衫臨窗而立,時不時回頭看一眼那對尋歡作樂的狗男,眼裏的幽怨,活像被男人拋棄的小妾。
門,從外麵被推開。
蘇長衫搖著把扇子,皮笑不笑的踱著方步走進來,“滾出去。”
人紅一嘟,朝著邊男子的耳朵吹了口氣,嗔魅道,“爺,一會記得來找玉兒,玉兒晚上好好侍候爺。”
李錦夜慵懶的笑笑,手在人的腰間狠狠了一把,“去吧。”
張虛懷恰好回頭,把李錦夜那一笑,那一看在眼裏,心裏恨恨的罵了句:“禽。”
Advertisement
玉兒妹妹離開,蘇長衫長袍一掀坐了下來,自己給自己斟了杯酒,一飲而盡。
“一個好消息,一個壞消息,先聽哪一個?”
李錦夜俊眉微攏,沒理他這一茬。
窗邊的張虛懷又無聲的翻了個白眼,“先聽好消息吧,年歲大了,不得驚。”
蘇長衫低低一笑,道:“好消息是,暮之你很快就要開府了;壞消息是,有人見你這夜夜苼歌的,怕懷了子,打算和你攀攀親家呢。”
李錦夜不聲地看了他一眼,“這個有人,是哪些人?”
“這個娘娘,那個娘娘的,連中宮那一位,聽說都把娘家人進了宮。”
蘇長衫端起酒杯與他了,“你這條鹹魚,很快就要翻了。”
李錦夜輕輕的笑了一下,沒說話。
蘇長衫一偏頭,看向一旁支著腦袋看好戲的張虛懷笑道:“你也有個喜事,娘娘們聽說你這老大不小的人,連個暖床的丫鬟都沒有,也在暗中張羅呢。”
張虛懷朝地上狠狠的“呸”了一聲,“喲喂,我這是何德何能啊我!”
蘇長衫眼中閃過,笑道:“堂堂太醫院院首,終大事還是讓人心的。”
“他個二舅的心!”
張虛懷罵了句髒話,捧著酒杯就往裏灌。這日子,還不如在孫家莊來得自由。
Advertisement
李錦夜眼中劃過波瀾,“要不,你就說你不能人道?”
“呀呀個呸,你才不能人道呢,你全家都不能人道。”
李錦夜不怒反笑:“虛懷啊,了京,你的脾氣是一日不如一日啊。”
“再這樣下去,你將會為京城最短命的太醫院院首。”蘇長衫添了一句。
“你,你們……”張虛懷點了幾下手指,還能不能盼著他點好。
這時,蘇長衫突然低了聲道:“還有一件事,不知道是好是壞。”
李錦夜睨他一眼,目如電。
“那一位聽說要下江南。”
“又下?這次是為什麽?”
蘇長衫搖搖頭:“不知道。”
張虛懷頓了頓,火氣略消,“這些年他一次一次下江南,勞民傷財不說,祖宗積下來的家底都快被敗了,真不知道是為了什麽?”
“想知道?”蘇長衫眉頭一挑。
“你知道?”張虛懷不答反問。
蘇長衫輕咳一聲,食指沾了點酒,在桌上寫了一個字。
張虛懷湊近一看,後前直冒冷汗,立刻向李錦夜看過去。
李錦夜目如電,早就看出一個高字。
難道說……跟高家有關?
不對啊,高家的在帝都,江南那邊……
他猛的抬起頭,視線與張虛懷遇上,兩人都從彼此肯裏看出了幾分驚悚。
Advertisement
許久,張虛懷才扯了扯角,眼裏毫無笑意,“看來,孫家莊那對母有變啊!”
李錦夜眸一沉,“來人。”
青山悄然而,“爺。”
“你回一趟孫家莊看看,打聽一下那對母在何?”
“打聽什麽?”蘇長衫冷笑一聲:“謝家前兩天已經上了折子,稱高氏母已回到謝家。”
“回去了?”張虛懷氣短悶,神僵,那丫頭不是說要跑得遠遠的嗎?
蘇長衫默默點了一下頭。
李錦夜眼中劃過波瀾,“青山,你還是去一趟,我要知道詳細的消息。”
“是。”青山應了一聲,瞬間消失在暗夜裏。
蘇長衫俊眉輕攏,青山,山是暮之邊最得力的侍衛,江南這一趟最快一個來回也得七八天,看來那丫頭……
“那丫頭於我有救命的恩。”李錦夜突然開口。
“而且,還是藥王的傳人,我的徒弟。”張虛懷補了一句。
蘇長衫輕輕一笑,“心裏既然惦記著,何必專程讓青山跑這一趟。”
“你……什麽意思?”張虛懷一頭霧水。
蘇長衫目幽幽向李錦夜看過去,“暮之,你說呢?”
李錦夜先是皺了皺眉,片刻後臉上有了一容,“我明白了,明兒一早就上折子。”
Advertisement
“你明白什麽了,上折子幹什麽,你倒是把話給我說清楚啊!”張虛懷急得跳腳。
偏偏那兩個人一個舉杯,一個搖扇子,哪個都沒有搭理他。
張虛懷氣得胡子翹得比天高,眼白都快翻出天際了。
這兩貨,真想一口咬死人他們!
……
翌日一早。
謝玉淵剛起,羅媽媽就把昨兒綠柳居,福壽堂的事兒一五一十的說與聽。
謝玉淵聽罷,別的沒有,隻在心裏歎羅媽媽有府裏的眼線,可真不。
自己前世是有多麽愚蠢,才冷落了這麽好的一個忠仆,生生把自己變了籠中之鳥。
“媽媽,綠柳居那頭,能不能想辦法安個人進去?”
羅媽媽眼皮一跳,“小姐的意思是……”
謝玉淵對上的視線,微不可察的點點頭。
猜你喜歡
-
完結10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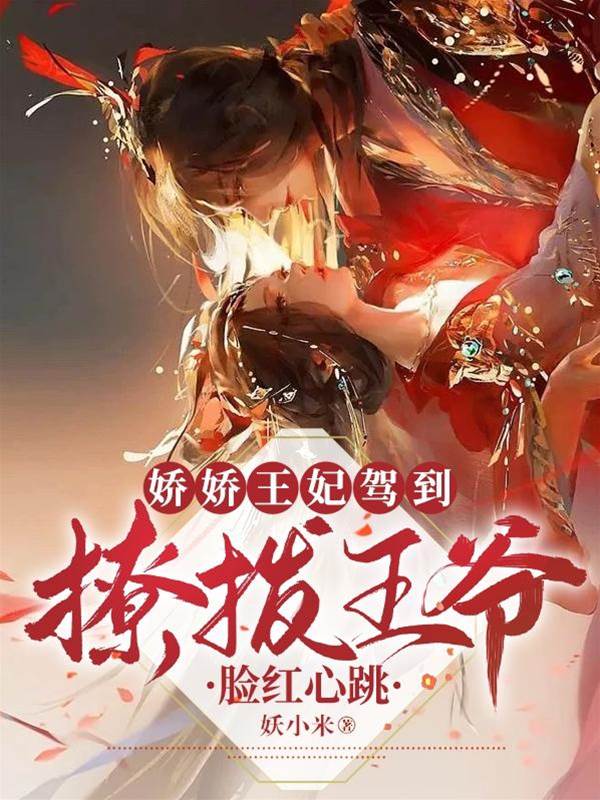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83.7萬字8.18 101760 -
完結449 章

太子妃退婚后全皇宮追悔莫及
簪纓生來便是太子指腹爲婚的準太子妃。 她自小養在宮中,生得貌美又乖巧,與太子青梅竹馬地長大,全心全意地依賴他,以爲這便是她一生的歸宿。 直到在自己的及笄宴上 她發現太子心中一直藏着個硃砂痣 她信賴的哥哥原來是那女子的嫡兄 她敬重的祖母和伯父,全都勸她要大度: “畢竟那姑娘的父親爲國捐軀,她是功臣之後……” 連口口聲聲視簪纓如女兒的皇上和皇后,也笑話她小氣: “你將來是太子妃,她頂多做個側妃,怎能不識大體?” 哪怕二人同時陷在火場,帝后顧着太子,太子顧着硃砂痣,兄長顧着親妹,沒有人記得房樑倒塌的屋裏,還有一個傅簪纓。 重活一回,簪纓終於明白過來,這些她以爲最親的人,接近自己,爲的只不過是母親留給她的富可敵城的財庫。 生性柔順的她第一次叛逆,是孤身一人,當衆向太子提出退婚。 * 最開始,太子以爲她只是鬧幾天彆扭,早晚會回來認錯 等來等去,卻等到那不可一世的大司馬,甘願低頭爲小姑娘挽裙拭泥 那一刻太子嫉妒欲狂。
72.9萬字5 91345 -
連載1463 章

穿成病嬌大佬的惡毒大嫂
裴家被抄,流放邊關,穿成小寡婦的陶真只想好好活著,努力賺錢,供養婆母,將裴湛養成個知書達理的謙謙君子。誰知慘遭翻車,裴湛漂亮溫和皮囊下,是一顆的暴躁叛逆的大黑心,和一雙看著她越來越含情脈脈的的眼睛……外人都說,裴二公子溫文爾雅,謙和有禮,是當今君子楷模。只有陶真知道,裴湛是朵黑的不能再黑的黑蓮花,從他們第一次見面他要掐死她的時候就知道了。裴湛:“阿真。要麼嫁我,要麼死。你自己選!”陶真:救命……我不想搞男人,只想搞錢啊!
220.7萬字8 89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