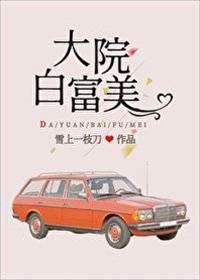《蜜婚:老公大人輕點撩》 第353章 你欠我一個條件
婚禮前一天,所有的賓客都已經抵達了南延島。
這夜注定是難眠的,江舒夏站在三樓房間的臺上,那雙盈盈目平靜地朝著海麵上看去。
夜晚的海波洵洵,海風溫地吹拂在海平麵上,卷起一層層的浪花。
海邊停著很多遊艇,都是送賓客島的遊艇c。
的下枕在胳膊上,紅稍稍一彎起。
淩旭堯拿了外套蓋在了的肩頭,高大的將圈了懷裏,薄輕輕地過的麵頰,“在想什麽呢?”
江舒夏轉頭,小手輕輕地了男人的額頭,“在想,明天的婚禮。”
男人輕輕地恩了一聲,眼眸裏的笑意深邃,結實的手臂將圈著。
“淩旭堯,我隻是覺得有些張!”從男人的懷裏轉,稍稍冰涼的手臂圈上了男人的脖子,認真地一字一頓著說,“明天我會是你的新娘——”
“嗯,是最的新娘!”淩旭堯的大掌向下一摟,薄熨帖在了的耳邊,嗓音低沉而磁,多的是勾人。
江舒夏抬起了腳,的秀足直接踩在了男人的腳背上,瞇著眸,小手攀上男人的肩頭。
吸了吸鼻子,“你這麽說我可是會當真的!”
“本來就是真話。”淩旭堯低頭凝視著漂亮的容,沉下了聲道。
他並沒有給開口的機會,就著這個姿勢把直接抱了起來,驚呼了一聲小手很自然地勾住了男人的脖子。
淩旭堯抱著的小妻子,直接將人放在了的大床上,他的吻落在的額頭上,“睡吧!我明天最的新娘——”
江舒夏抿笑,眼底映出來的也全是男人的模樣。
他眼底的溫寵溺,很容易就能讓人溺斃在其中。
江舒夏點點頭,乖乖地閉上了眼。
Advertisement
明天要做男人最的新娘,這樣的時刻更是馬虎不得。
睡足了,明天才是最好的狀態。
淩旭堯見著閉上眼眸睡覺的模樣,薄稍稍著一彎,掀開一旁的被子上了大床,而後便了上來,將抱在懷裏。
呼吸著上悉的氣息,才讓人覺著滿足。
按理說,結婚前一晚,新人是不能見麵的。
隻不過兩人都不在意,反而離了彼此就覺得睡不好。
便也沒有人提起這點。
翌日上午九點三十五時,江舒夏已經在休息室畫好了新娘妝。
鏡子裏的人眉眼彎彎,角笑意延綿得十分漂亮。
多了點修飾,人的麵容致而秀,屬於新娘的將襯得越發可人。
化妝師的是專業的,畫個新娘妝完全將江舒夏最的一麵給襯托得淋漓盡致。
江舒夏穿著上次試過的那條婚紗,婚紗在那凹凸有致的上特別地有味道,顯得氣質高貴優雅。
的手裏拿著香檳玫瑰的捧花,很浪漫的。
整個休息室就剩一人,是張的,哪個人麵對著這樣一天的時候是不張的?
江舒夏拿著捧花的手稍稍著收攏,第一次有這樣的經曆,的確是該張的。
生怕到時候若是做得不好,在大家麵前丟了臉就不大好了。
看著鏡子裏麵的人,練習著微笑,隻想要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麵給那個男人看。
突然聽到的開門聲,收斂了笑容,朝著門口看去,是穿著一黑的zora。
zora黑的短包,臉上化著濃豔的妝容,看上去得很,跟當初見到的那個小孩差別大得很。
也對,現在zora可不再是當初那個看著單純可的小姑娘了,變化了也算正常。
Advertisement
江舒夏角的笑意一僵,倒是還記得,這個所謂的同父異母的妹妹對的敵意貌似還真的不是一般的大。
之前的那一次見麵,鬧得如何的不愉快,還覺得有些曆曆在目的覺。
抿了角朝著zora看去,聲音冷淡,“你怎麽進來的?”
這裏是新娘的休息室,不是雜人能進的,也不知道zora是怎麽進來的。
“怎麽?覺得心虛了?”zora走過來,角帶著嘲諷。“當初不是表現得不在意嗎?怎麽?轉眼就要了sr百分之十的份。你知不知道百分之十的份夠你這樣的人活好幾十輩子了?你這樣低賤的私生,憑什麽得到sr的份?你還好意思收下,簡直不要臉到極致。私生就是私生,不管怎麽偽裝都改不了私生這個份!見錢眼開,在我麵前裝清高,忘了告訴你,我從來不吃你那一套。”
聞言,江舒夏眉頭微擰了起來,這話聽得到覺得真的不是很舒服,不要臉?低賤?
抱歉,可不是什麽白白了辱罵不會還的小白兔。
抬手將捧花放在桌前,抬眸直直地看向了zora,“不要臉,低賤?不要忘了,zora小姐,我上流的一半的可是你父親的,我低賤,那你算什麽?你覺得你很高貴?你若是高貴?還會說出這些低賤的話嗎?zora小姐,高貴如你卻還在做著低賤的事,低賤是從一個人的行為談吐中現出來的而不是上流淌著的所決定的。還有,你若是不讚同大可以找威廉先生說,讓他把那百分之十的份收回去,我絕對不會說半個不字!”
見著zora變了的麵,角揚開笑來,“畢竟不是誰都跟zora小姐一個樣——”
Advertisement
“你,你竟然敢這麽罵我?你知不知道我的份?我在法國有公主的稱號,你居然敢罵我,你這個低賤的私生!”zora放大了聲音,眸子都快要瞪出來。
江舒夏聳肩,並沒有將的罵聲放在眼裏。
“你在法國有公主的稱號那有能怎樣?這裏不是你的法國,要猖狂就回去你的法國。”
zora瞪著江舒夏有些口不擇言地罵,“你個賤人,你媽媽是狐貍,你也好不到哪裏去。果然是有其母必有其,一樣的下賤。”
江舒夏麵轉冷,垂在側的手不由地握。
忍了忍,深吸了一口氣,“出去!”
“惱怒了?”zora笑得得意洋洋。
江舒夏挽隻覺得諷刺,麵冷得厲害,聲音卻顯得平靜,“zora小姐,你怎麽想就怎麽想。不過,今天是我婚禮的日子,這裏還是不歡迎你的!請出門!順便幫我把門帶上!”
這樣的日子裏,並不是很想生氣,但是隻要zora在,控製不住,恨不得上前撕碎那張。
zora看了一眼江舒夏上的婚紗,不瞪大了眼。
這條婚紗是mercedes設計的唯一一條婚紗,mercedes這輩子就設計過這麽一條婚紗,是因為這條婚紗名的。
之後便放了話出去,這輩子就設計這麽一條婚紗,後來事實也證明了,之後的設計作品都沒有婚紗。
這條婚紗曾引起了一時的轟。
因為,而顯得珍貴。
後來就算有人花大價錢去要求mercedes為他們設計婚紗,到最後都是吃了閉門羹的。
隻不過現在,這條婚紗居然出現在了江舒夏的上,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有多的人想要這條婚紗,就連也不例外。
Advertisement
跟威廉先生提起過幾次,威廉先生算是應下了,隻是現在是被江舒夏穿著的。
抬手指著江舒夏上穿著的婚紗,驚訝地捂住了,“這婚紗——這婚紗——”
江舒夏低了頭,看了眼自己上的婚紗,並沒有覺得什麽不妥。
“是爸爸幫你弄來的吧?江舒夏,你還真是有能耐,不但拿去了sr百分之十的份,還能讓爸爸去幫你拿下這條婚紗!”zora咬牙,眼眸裏含著怒火。言辭間卻全都是篤定。
江舒夏還沒開口,zora便撲了過來,江舒夏穿著高跟鞋往著一邊一讓,zora撲了個空,直接撞到了華麗的椅子上,把椅子推倒在地。
江舒夏見狀順手拿起了手機按下了號碼。
zora會做什麽,江舒夏大概是知道的,人一旦瘋狂起來,誰也擋不住。
電話還沒接通,門便被人從外麵推開,淩旭堯穿著新郎西服,姿筆,他就站在門口。
看到裏麵的況,男人英的眉頭不滿地一皺。
zora還沒來得及從地上起來,淩旭堯便大步上前,將江舒夏摟到了懷裏。
見著淩旭堯來了,鬆了一口氣。子地靠在了男人的膛上。
很快,威廉先生和齊放也跟著進來。
威廉先生見著zora,麵一沉,直接上前把zora給拉了起來,聲音冰冷,冷冷地看著zora“誰讓你過來的?給我回去!別在這給我搗!”
zora委屈地撇,咬牙,“爸爸,你怎麽可以把我要的婚紗給了這個私生?你就是偏袒這個份低賤的私生!不但給了這人sr的份現在還把我喜歡的婚紗拿來討歡喜,沒有你想的那麽好,就是一個賤人!一個小三生的份卑賤的私生”
威廉先生見著越說越離譜,抬手一掌便落在了的麵頰上。
“啪!”的一聲在休息室格外地清晰。
zora被打懵了,含著淚水難以置信地朝威廉先生看去。
“那婚紗不是我給的!”威廉先生咬牙。
zora眼底的水落了下來,威廉先生現在是為了這個私生打了。
他居然敢打!居然敢打!
威廉先生盯著看,對上眼底的恨意,眸複雜而深沉,吩咐了書。“立馬人把小姐送回法國,沒有我的命令不準放出來!”
書聞言點頭,帶了保鏢過來,把zora給帶走。
威廉先生朝著門口看了眼,zora的影已經消失在視線裏,他轉而朝著江舒夏看過去。
“舒夏,是爸爸對不起你,沒把zora管好。讓到這樣的地方鬧事。”
威廉先生的眸底帶著歉意和愧疚。
明明吩咐過的這段時間沒有他的命令就不能讓zora出境,但是卻沒想到居然現在就出現在這裏,還是在這樣的一天裏。
江舒夏抿,聳肩微笑,“沒事,不是什麽都沒發生嗎?”
的確是什麽都沒發生,隻不過是稍稍影響了一點心而已。
威廉先生看著江舒夏,點點頭,對這個兒他愧疚得很,但是卻什麽都不計較,像極了對媽媽。
隻是現在,都要嫁人了,隻是他卻不能牽著的手走進禮堂裏。
威廉先生看了眼江舒夏的小手,眼眸漸漸著有些潤,“舒夏,抱歉,爸爸不能牽著你的手進禮堂。”
兩人的關係並沒有公開,這樣的場合裏若是讓威廉先生帶著江舒夏進禮堂,想必是會引起不必要的轟,現場的記者也在,所以江舒夏明白。
挽,“沒關係的,隻不過是個形式而已。”
說完抬眸看了眼旁的男人,一個形式而已,但是卻讓覺得無比的欣喜。
淩旭堯對上的視線薄微微上挑,溫寵溺。
這時,有人過來通知婚禮快要開始了,馬上去做準備。
淩旭堯垂眸看,俯在的角印下淡淡一吻,“待會見!”
江舒夏輕笑著點頭,“待會見!”
婚禮的場地在島上地勢較高的地方,就是一道走上教堂的階梯,白的小教堂格外地雅致,階梯兩邊,是用鮮花做的花柱,呈現著扇形朝著四周放,看上去非常的寬闊,放眼去,全是的香檳玫瑰,有很強的畫麵,讓人覺著震撼。
這場婚禮隆重而又充滿著浪漫的氣息。
江舒夏挽著慕老爺子的手一步步地走教堂裏,紅的地毯一直延到了主持臺上。
教堂裏坐滿了賓客,伴隨著婚禮進行曲的響起,江舒夏頭頂著白頭紗,一步步地朝著紅毯盡頭的男人過去。
猜你喜歡
-
完結88 章

和周先生先婚後愛
婚後,宋顏初被周先生寵上了天。 她覺得很奇怪,夜裡逼問周先生,“為什麼要和我結婚,對我這麼好?” 周先生食饜了,圈著她的腰肢,眼眸含笑,“周太太,分明是你說的。” 什麼是她說的?? —— 七年前,畢業晚會上,宋顏初喝得酩酊大醉,堵住了走廊上的周郝。 周郝看著她,隻聽她醉醺醺地歪頭道:“七年後,你要是還喜歡我,我就嫁給你吧!” 少年明知醉話不算數,但他還是拿出手機,溫聲誘哄,“宋顏初,你說什麼,我冇聽清。” 小姑娘蹙著眉,音量放大,“我說!周郝,如果七年後你還喜歡我,我就嫁給你!”
13.1萬字8.09 58565 -
完結280 章

總裁夫人她馬甲轟動全城了
前世,花堇一被矇騙多年,一身精湛的醫術被埋冇,像小醜一樣活了十三年,臨死之前她才知道所有的一切不過是場巨大陰謀。重生後,她借病唯由獨自回到老家生活,實則是踏入醫學界,靠一雙手、一身醫術救了不少人。三年後她王者歸來,絕地成神!先替自己報仇雪恨,嚴懲渣男惡女;同時憑藉最強大腦,多方麵發展自己的愛好,畫家、寫作、賭石...隻要她喜歡,她都去做!她披著馬甲在各個行業大放光芒!權勢滔天,富豪榜排名第一大總裁席北言:媳婦,看看我,求求了!餘生所有,夢想、榮耀、你。
51.6萬字8 29860 -
完結21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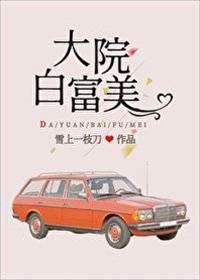
七零大院白富美
別名:大院白富美 肖姍是真正的天之驕女。 爸爸是少將,媽媽是院長,大哥是法官,二哥是醫生,姐姐是科學家。 可惜,任性的她在婚姻上吃了虧,還不止一次。 二十二歲時,她嫁給了識于少時的初戀,可惜對方是個不折不扣的渣男,兩年后離婚。 但她并沒為此氣餒,覺得結婚這事兒,一次就美滿的也不太多。 二十六歲再婚,一年後離婚。 三十二歲三婚,閃婚閃離。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集齊了極品婆婆,極品小姑子,極品公公之後,她終於遇上了最適合的人。 三十五歲肖姍四婚,嫁給了最後一任丈夫趙明山,二人一見鍾情,琴瑟和鳴,恩愛一秀就是幾十年。 重生後,她麻溜的繞過一,二,三任前夫,直接走到趙明山的面前,用熱辣辣的目光看著他, “哎,你什麼時候娶我啊?” 趙明山一愣,肩上的貨箱差點砸到腳了。
97萬字8 12440 -
完結1436 章

我在娛樂圈修仙
【女強+絕寵+修仙】暴發戶之女林芮,從小到大欺女霸男,無惡不作。最後出了意外,一縷異世香魂在這個身體裡麵甦醒了過來。最強女仙林芮看了看鏡子裡麵畫著煙燻妝,染著五顏六色頭髮的模樣,嘴角抽了抽。這……什麼玩意兒?! “雲先生,林影後的威亞斷了,就剩下一根,她還在上麵飛!” “冇事。”雲澤語氣自豪。 “雲先生,林影後去原始森林參加真人秀,竟然帶回來一群野獸!” “隨她。”雲澤語氣寵溺。 “雲先生,林影後的緋聞上熱搜了,據說林影後跟一個神秘男人……咦,雲先生呢?” (推薦酒哥火文《我,異能女主,超兇的》)
135.2萬字8 23125 -
完結169 章

勾月亮
『特警隊長×新聞記者』久別重逢,夏唯躲著前男友走。對他的形容詞隻有渣男,花心,頂著一張帥掉渣的臉招搖撞騙。夏唯說:“我已經不喜歡你了。”江焱回她:“沒關係,玩我也行。”沒人知道,多少個熬夜的晚上,他腦海裏全是夏唯的模樣,在分開的兩年裏,他在腦海裏已經有千萬種和她重逢的場麵。認識他們的都知道,江焱隻會給夏唯低頭。小劇場:?懷城大學邀請分校特警學院的江焱學長來校講話。江焱把她抵在第一次見她的籃球場觀眾席上撕咬耳垂。他站在臺上講話結束後,有學弟學妹想要八卦他的感情生活,江焱充滿寵溺的眼神落在觀眾席的某個座位上。一身西裝加上他令人發指的魅力,看向觀眾席的一側,字音沉穩堅定:“給你們介紹一下,你們新聞係的19級係花小學姐,是我的江太太。”--婚後有天夏唯突然問他:“你第一次見我,除了想追我,還有沒有別的想法?”他低頭吻了吻女孩,聲音帶著啞:“還想娶你。”他擁抱住了世間唯一的月亮......於是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布他江焱——已婚!〖小甜餅?破鏡重圓?治愈?雙潔〗
28.6萬字8 752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