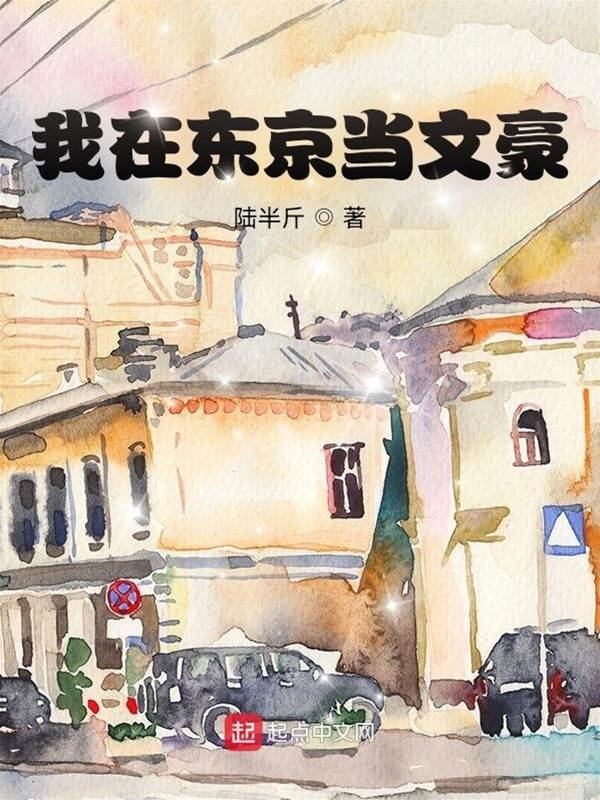《大唐女法醫》 第265節
?”何寺正並不意外這個結果,因為之前也有仵作驗了一次,也說這不像是從臉上流出來,卻說不清怎麽回事,所以他很想知道原因。
冉解釋道,“做出這種判斷,主要有兩個依據:其一,若是從皮裏滲出鮮。皮一般不可能沒有任何諸如傷口之類的表現,並且倘若是均勻的從皮滲出來,並不能形這樣流柱狀的痕。其二,之所以形這種流柱狀痕。是因為從創口流出的由於其重力作用從高向低流。而傷口必定是傷到較大的靜脈管,但死者的頭部並沒有可以形大量出的明顯傷口。”
何寺正愣了愣,才消化這段解說中的大致意思。
劉青鬆適時的補充道。“靜脈並非經脈,而是隻脈的一種,倘若隔斷比較大的靜脈,不會噴濺的到都是,而是湧出。何寺正你經常監斬,應該比較有啊。割腕自殺和被斬頭是不一樣的。”
這又不是什麽榮的事。何寺正臉不佳,卻還是道。“我一直以為四噴濺是因為傷口太大了。”
大脈一般都埋於深,一般小傷自然傷不到它。
“你這麽說也沒錯啊,改天兄弟也不藏私,給你好好解說一下,日後對於破案很有用的。”劉青鬆道。
醫生的知識一般都是不外傳的,劉青鬆如此不拘小節,也是何寺正雖然與他小攃不斷,卻未曾真正翻臉的原因,何寺正拱手道,“那就多謝劉醫生了。”
冉趁著他們對話的這會功夫,已經將竇四娘上大概都檢查了一遍。竇四娘的手指上殘留著跡,大約是自己拭臉頰時沾道,而其上的都是正常的滴落殷染。
Advertisement
冉的注意力被左肩膀一塊印吸引,這塊印很大,但按照正常的滴落,肯定是不可能在這裏形這麽大片的。
冉想著,便解開了竇四娘的。上著的是一件襦,鬆開束帶之後,那驚心魄的曲線讓劉青鬆眼睛直了一下,不過想到是一,立刻便沒有了雜念。
“驗,死者左肩上有大片跡,經解檢驗,證實死者左肩上有大片瘀痕,疑似指印。”冉看見在雪白肩膀大片黑紫的瘀痕,立刻道。
之所以說疑似,是因為這片瘀痕與斑混在一起,一時辨不出很清晰的手指印。
劉青鬆心裏一喜,驗到這個,就足以證明死者在臨死前可能被人實施過暴力行為,而他們也沒有任何殺人機,再找到不在場證據,便可以很大程度的擺嫌疑,而這個最有力的不在場證據,就是李恪!
冉將整個實仔細檢查完畢,耗費了整整小半個時辰。
而後才總結道,“死者麵部腫脹,眼結下有出點,疑為窒息而死。”
“眼結是覆蓋在眼瞼麵和眼球前麵眼白部分的一層,如果死者不能呼吸,比如被人用什麽東西捂上,或者勒死、自縊,那個上都會出現針尖一樣的點。”劉青鬆說著從工箱裏取出一把鑷子,夾住的上眼皮,拉開之後,指給何寺正看。
經過劉青鬆不停在旁解釋,何寺正等人基本能夠瞭解,但像眼結下出可能就是窒息死,他們也將信將疑,畢竟以前從來不知道。
冉在蘇州驗時,劉品讓的態度是,隻需要知道結果,過程不重要,所以一些專業名詞能忽略就盡量忽略了,了這一點也無所謂,隻要抓到兇手,並且案能夠說得通,人證證俱在,再加上兇手招認便萬事大吉了。那些員顯然沒有大理寺這些好學。
Advertisement
“這個問題,何寺正不妨回去捂死幾個試試看,反正死囚也不在數。”冉一邊把竇四娘上的理好,一邊不鹹不淡的道。
但話一出口,屋裏幾個男人頓時覺得腦門上冒冷汗。
何寺正道,“這位娘子說的如此輕飄,豈不知人命不可兒戲?”
在權貴的手裏,人命可不就是兒戲?冉心裏如是想,卻未曾說出口,隻道,“死人看的多了,也就能將生死看淡不,何寺正不信也可以一試。”
何寺正平時都是監斬,看的是死亡的過程,而冉平時看到的都是,有新鮮的,有腐敗的,也有一堆白骨。
“這麽說來,竇四娘是被人捂死?”何寺正盯著冉黑沉的眼眸看了須臾,轉移了話題。心裏想著,是不是回去真的捂死幾個瞧瞧。
冉搖頭,“死者頸部沒有勒痕,可能是被人捂死,但也不一定,肺炎、狂犬病等都有可能窒息,還有可能是中毒,何寺正可以去查查竇四娘是否有病史,倘若沒有,那我更傾向於懷疑中毒。”
第362章你和他真有一?
劉青鬆扶額,萬一真是中毒,這事兒可就又說不清楚了!
“如何才能確定是何種毒藥?”何寺正暫時拋去了雜念,將注意力投案之中,於他來說,沒有比破案更加重要的事了。
“據所表現出來狀態,我懷疑兇手是用烏頭殺人。因為服用烏頭致死,檢無特殊征象,一般窒息死的征象較為明顯。本查不出來,所以烏頭可謂是殺人必備的良藥。”冉答道。
劉青鬆了鬢角的汗,“必備良藥……你這是在說玩笑話嗎?”
冉淡淡道,“我說的是事實。”
“這麽說,隻要中了烏頭之毒,便查不出死因?”何寺正不甘心的追問。
Advertisement
“也不是。”冉手在的腹之間輕輕按,“如果幸運的話,剖開腹腔,可能會在胃找到烏頭藥渣,粘和漿可能有點出。不過烏頭的殘留毒極易被氣破壞,倘若不及時解剖,本驗不出毒。”
在大唐這種條件下,即便解剖也不見得能驗出烏頭的毒,就算冉能弄出無水乙醇,以及一切檢驗毒所用的東西,大唐無人看懂這個檢驗報告也是徒勞。而所謂用銀針驗毒,並不是能驗出所有的毒,本就靠運氣。
“何寺正不妨從竇四娘上的線索著手,比如這個手印。我個人認為,這個大小不太可能是個。據竇四娘侍婢芍藥的供詞,一直與竇四娘在一起,隻是在竇四娘臉部有些異樣以後,才到門口去喚了小廝來要了一碗消暑湯。”冉半張臉被口罩遮掩,發出的聲音有些嗡。見何寺正頜首,便繼續道。“倘若推敲的供詞,說,起找小廝要了一盅消暑湯,返回來便瞧見娘子麵上流,何寺正不妨找小廝確認一下,芍藥離開的這段時間究竟有多長,是否足夠有人闖進來襲擊竇四娘。”
“這麽說來,端梁夫人沒有任何嫌疑?”何寺正剛剛從剖的震撼中回過神來,探究的看著冉。
冉自知道大理寺不可能讓解剖竇四娘的。便將手套下丟進箱子裏,聽見何寺正的話,便答道,“可否容許我問何寺正幾個問題?”
何寺正點頭道。“可。”
“破案在於機。掌握了殺人機便等於鎖定了兇手,不知道何寺正以為端梁夫人殺人機是什麽?”冉目直視著他。
何寺正也算是掌生殺權利,監斬了不知多次。此刻卻在冉上到一種力,“這……需要再進一步調查。”
Advertisement
“人證證呢?”冉見旁邊的員要開口回答,輕笑了一聲,“人證不會是芍藥吧?證是那包潔麵?那個芍藥,比任何人都有嫌疑,讓來做人證。豈不是貽笑大方?至於潔麵,我至今還不知裏麵摻的是什麽毒。但竇四娘是窒息而死,倘若不是被人捂死,便是服毒藥,不知潔麵是能捂死人,還是有人會服?”
一番犀利的言辭,讓大理寺三名員啞口無言,倘若冉此時不說,他們也並非想不到,隻是一個娘子,短短時間便理出頭緒,實在讓他們有些汗。
“好!”劉青鬆一掌,發現眾人目都聚集到他上,便立刻改口道,“分析的好!”
冉收拾好工箱,何寺正立刻揮手令獄卒來幫忙拎著。
“多謝。”冉衝何寺正微微欠。知道,其實何寺正早就看出的份,卻不知道是出於什麽原因,竟然沒有拆穿,並且對於犀利的言辭並無惱怒,是應該道謝。=本=作=品=由=思=兔=網=提=供=線=上=閱=讀=
何寺正淡淡笑道,“客氣了。”說罷令人引劉青鬆和冉出了停館。
何寺正隨後出來,站在外曲門的門廊上看著遠去的馬車,心歎,怨不得能鎮得住煞氣衝天的長安鬼見愁,倒是個奇子。
“何寺正,我得即刻將此事上報,先行一步了。”何寺正後一名綠服的中年男子拱手道。
“張史請便。”何寺正拱手道。
張史的職其實是監察史,而非大理寺的人。
史臺分為三院,一是臺院,主要是掌管糾舉百僚,推鞫刑獄;二是殿院,掌整齊朝班,檢察儀仗;三是察院,掌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糾視刑獄,肅整朝儀,監決囚徒等等。
臺院史的職品級最高,殿院次之,而察院品級最低,管理的事卻雜而廣,亦有彈劾百的權利,所以縱然張史的職要比何寺正低,何寺正也不願意怠慢。
張史翻上馬,冒著炎炎烈日向朱雀大街一路疾馳。
彼時劉青鬆將將撥開簾子探頭向外,便覺一人一騎卷著熱風席了過去。
“誒?”劉青鬆半個子都從小小的窗口探了出去,盯著那一騎絕塵看了半晌。
冉撥弄著鏤花銅缽裏的冰塊,仰頭看著劉青鬆的姿勢,麵上難得出現了毫不掩飾的吃驚。那車窗極小,連普通盆口的大小都比不上,他居然能鑽出去,並且輕鬆的回來。
“你,這是什麽表!”劉青鬆轉回頭被嚇了一條,立刻到馬車一角,“我說冉法醫,我看慣了你麵癱,偶爾有表讓我有點慎得慌。”
冉臉一黑,一直知道劉青鬆瘦的能在四級風裏打晃,卻沒想到真是個竹竿,“我覺得這個窗口便是再開大一倍,蕭鉞之也未必能輕鬆通過。”
劉青鬆吊著眼梢看了一眼,並不曾繼續這個話題,“先不說這個,我方才終於想起來那人是誰了!”
“騎馬經過的那個?”冉道。
劉青鬆點頭,“方才我在停館見過他,就是何寺正側的那兩名員之一,當時我隻覺得他眼,不過滿朝員我眼的多了,便沒在意。剛剛見他騎馬那架勢,我突然想起來以前見過他,那個人不是大理寺的員,而是史臺的人。”
“史臺?”冉皺眉。
彈劾百這一項職責,使得朝廷員和員家屬對其都沒有什麽好印象。這三院史為清要之,雖秩品不高,但威權甚重,所以錄用的員,必定是要清正耿直。但冉私以為,在這樣的表象之下,為史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一刻熱八卦的心。
“我驗之事恐怕敗
猜你喜歡
-
完結764 章
我在古代日本當劍豪
穿越到了公元1789年的古代日本,時值承平日久的江戶時代。開局只有一個下級武士的身份、佩刀、以及一個只要擊敗或擊殺敵人便能提升個人等級與劍技等級的系統。……“遇到強敵時我會怎麼辦?我會拔出第二把刀,改換成我真正拿手的劍術——二刀流。”“如果還是打不過怎麼辦?”“那我會掏出我的左輪手槍,朝敵人的腦袋狠狠來一槍。”緒方逸勢——擁有“人斬逸勢”、“劊子手一刀齋”等稱號的“大劍豪”如此對答道。
331.6萬字8 17550 -
連載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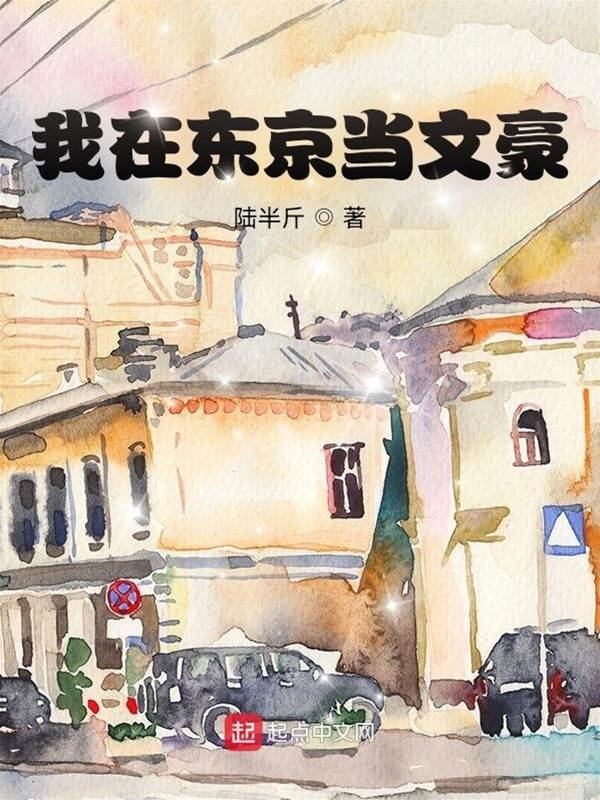
我在東京當文豪
這個霓虹似乎不太一樣,泡沫被戳破之後,一切都呈現出下劃線。 原本那些本該出現的作家沒有出現,反而是一些筆者在無力的批判這個世界…… 這個霓虹需要一個文豪,一個思想標桿…… 穿越到這個世界的陳初成爲了一位居酒屋內的夥計北島駒,看著孑然一身的自己,以及對未來的迷茫;北島駒決定用他所具有的優勢去賺錢,於是一本叫做暮景的鏡小說撬開了新潮的大門,而後這本書被賦予了一個唯美的名字:雪國。 之後,北島駒這個名字成爲了各類文學刊物上的常客。 所有的人都會說:看吧,這個時候,我們有了我們精神的歸屬……
41.5萬字8.18 141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