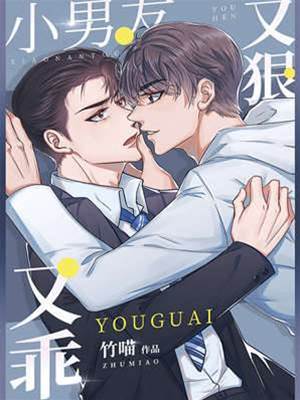《妻為上(新)》 第100章
100、第一百章 獨佔
聽到屋裡慕含章喚人來把秦昭然送去客房,景韶轉離開了。雖然現在整個人都要氣炸了,但強迫自己要冷靜下來,這個樣子進去說不定會做出什麼不可挽回的事。
「王爺還沒回來嗎?」眼看著太已經落山,慕含章看了看面前盛的飯菜,不住皺起眉頭。
下人們面面相覷,他們自然不知道王爺去哪裡了。
慕含章歎了口氣,讓人把冷掉的飯菜收了,剛剛起,就聽到門外悉的腳步聲,還未抬頭去看,就被迎面而來的人一把抱進了懷裡。
「你去哪兒了……唔……」突然被打橫抱了起來,慕含章掙扎兩下沒掙開,已經被抱進了室。
景韶把懷中人扔到床上,了衫就撲了上去。
「你傷了?」慕含章看到景韶肩頭的青紫,忙起要看,卻又被景韶了回去。
景韶按住試圖掙扎的人,一把扯開他的衫,俯啃了上去,急切地想要確認這個人是屬於他的,誰也奪不走。
慕含章起初還想勸他先吃飯,漸漸地就被景韶練的手法挑起了興致,按在他膛上推拒的手,不知不覺地了下來,改為攥下的床單。
景韶快速地作著,看著下的人目迷離,輾轉低的樣子,卻覺得心中空落落的。重生以來的一切都太順利,他一直以為君清以前是喜歡子的,或者說一心讀書的他本就沒有喜歡過誰,卻不料半路殺出個秦昭然。他們青梅竹馬,志趣相投;他們可以聊詩詞歌賦,針砭時弊。而自己只是北威侯強迫他嫁的皇子,他只是不得不接……
景韶知道或許是自己想得多了,所以下午又去找顧淮卿打架想把這事忘掉,但越是刻意去忘掉越是忍不住去想。君清心中或許早有喜歡的人,前世的種種怨懟,今世起初的抗拒,一幕幕的在眼前閃現,無一不在嘲諷著他,這一切只是他自己的一廂願,如果給君清選擇的機會,他或許本就不會看自己一眼……
Advertisement
這般想著,景韶的作便兇猛了許多。
慕含章很快就到了疼痛,不住蹙起眉:「輕……輕點……啊……」
景韶卻是不管不顧,越發的橫衝直撞起來。
「唔……」慕含章抬手推他,奈何本沒有力氣,上人的作越來越魯,堅如鐵的巨在來回翻攪,的愉悅如水般褪去,隨之而來的是越來越劇烈的痛楚,「啊……痛……」
慕含章揚起頭,白皙的脖頸拉出一道優的弧線,很快就被上的人一口咬住,他覺得自己正被一個野撕咬,恐懼伴著疼痛席捲了全:「停……停下來……啊……」
下人的越來越繃,景韶沒過多久就瀉出了華,息了片刻,緩緩離,看著下的人抖著蜷起了子,才意識到自己剛剛做得過分了。
「君清……」景韶猶豫著手,上他的手臂,卻被一把甩開。
看著他疼得蜷著子,頓時後悔不已,緩緩攥了攥拳頭,這個人是他認為的最乾淨溫暖的存在,若是失去了,他重活一世本就沒有意義,景韶深吸一口氣,底氣不足道:「我,我告訴你,不管你心裡裝著誰,你這輩子都只能我的王妃,我是不會放你走的。」
慕含章緩緩回頭,怪異地看了他一眼:「你發什麼瘋?」
「秦昭然是怎麼回事?」景韶覺得自己作為一個抓住妻子紅杏出牆的丈夫,委屈的應該是他,越說越理直氣壯,「你十八歲那年為什麼不去會試?」
「先生說我學得太雜,不如只讀聖賢書的秦昭然,所以讓我再讀三年……」慕含章愣怔半晌,下意識地照著景韶的話小聲回答。
「那他為什麼說等你中狀元?你嫁給我之前是不是跟他有什麼約定,誰先中狀元就娶對方啊?」景韶完全豁出去了,把自己想的都給說了出來。
Advertisement
慕含章瞪大眼睛看了他許久,這才反應過來,敢這傢伙是吃醋了啊!忍著上的難緩緩坐起來,輕歎了口氣:「有件事我是不是一直沒有告訴你?」
景韶聽得此言,頓時全的汗都豎了起來,難道君清要跟他坦白一起跟秦昭然私定終過?心下憤恨,縱然他們兩人如今依舊兩相悅,他也定然會做棒打鴛鴦的惡霸,把這人牢牢鎖在邊,他活了兩世,就只有這一個完全屬於他的人,誰也不許奪走!
慕含章緩緩手,上景韶英俊的側臉:「我你。」
「哼,我告訴你,就算你們先認識,我也……」景韶說了一半突然頓住,「君清,你說什麼?」
慕含章白了他一眼,轉要躺回去,卻被他一把扯進了懷裡。
「你再說一遍!」景韶激地抱著懷中人,不等他開口,便接著說,「我就知道,本王這麼英明神武你怎麼可能喜歡別人!我也你,君清,我兩世也只喜歡過你一個人。」
慕含章覺到抱著自己的雙臂有些抖,終是歎了口氣,當初覺得景韶在上還是個孩子,如今看來依舊如此,只是他的如此的簡單,摻不得半分的虛假,像一隻劃定了地盤的小,誰也別想沾染一一毫:「我與秦昭然僅僅是同窗之誼,若不是他中了狀元,我都要忘了這個人了。」
景韶聽了,心中越發的高興,突然想到了什麼,忙把懷中人放回床上:「快給我看看,傷到沒有?」
「沒,沒有……」慕含章頓時紅了臉,卻拗不過他,被他按住看了個徹底。
景韶仔細看了看,慢慢探了一指進去,還好沒有出,只是略微有些紅腫。
「嗯……」慕含章輕哼了一聲,推了推他。
Advertisement
景韶了還埋在其中的手指,的地方,引著他繼續深。這個人是他的,完完全全從裡到外都是他的,只是這般想著,心中就被漲得滿滿的。湊過去,吻住那被咬出齒痕的瓣,藉著方纔的,毫無阻滯地再次衝進了那妙的。
月上中天,若水園中萬籟俱寂,屋簷上昏昏睡的飛鳥,卻被屋中偶然溢出的聲響驚得高飛。
「彭!」景韶抱著枕頭,呆呆地看著面前閉的房門。
他,竟然,被,自家王妃,趕出房門了!
「哇唔!」在院子裡玩耍的小黃聽到響,立時扔了口中的樹枝,竄到了廊下。
「看什麼看,蠢老虎!」景韶瞪了跑來看熱鬧的小黃一眼,「本王要重振夫綱,讓他意識到把丈夫趕出房門犯了七出!」
老虎回他了一個鄙視的眼神。
景韶冷哼一聲,上前拍門道:「君清,我知道錯了,讓我進去吧!」
院子外巡邏的衛兵都是從親軍調過來的,聽到王爺扯著嗓子喊,齊齊的一趔趄。領隊的罵了眾人一句,加快了腳步帶隊離開了主院大門。
「嘎吱」房門開了半扇,慕含章站在門瞪他:「大半夜的嚎,你不嫌丟人嗎?」
景韶立時單手撐住房門,賠笑道:「君清,我錯了,別把我趕出去,這若水園也沒有我的臥房,你讓我睡院子嗎?」
小黃趁著兩人說話,已經先行從門裡了進去。
慕含章了額角,轉回屋裡,景韶滋滋的跟著進去,反手好房門。
大老虎已經自覺的竄上了床,在的被子上打滾。
慕含章爬到裡面,把老虎擺到中間,當做楚河漢界。
景韶看到他這番舉,立時垮下臉來:「君清……」那人不理他,面朝裡睡下,只給他一個漂亮的脊背。夏日衫在上面,隔著薄薄的一層綢約能看到那帶著紅痕的蝴蝶骨,單是看著就覺得心難耐,好想把那帶著清香的溫暖摟到懷裡,結果一手,就到了乎乎的大老虎。
Advertisement
小黃如今已經長大,躺著跟人差不多長,寬寬的子睡得四仰八叉,阻隔了景韶的所有方向。
景韶氣憤不已地揪住一隻耳朵,往床裡面了,睡覺!
過了良久,在景韶都要睡著的時候,忽然聽到慕含章問他:「你說你兩世都只喜歡我一個人是什麼意思。」
景韶一個激靈睜開眼,就對上了一雙炯炯有神的虎目,在黑暗裡泛著,手彈了一下老虎腦袋:「今生如此,來世亦然。」
慕含章轉過來,定定地看著他:「那你親之前的那些妾室呢?」
「咳咳,」景韶差點被口水嗆到,「我都沒過們。」
「那宋凌心呢?」
「宋凌心也沒過!」
「真的?」
「真的!」景韶堅定地說。
慕含章看著他,緩緩地笑了,慢慢湊過去,給了他一個輕吻:「睡吧。」
景韶瞪大了眼睛,追上去想再要一個,結果啃了一。
「嗷!」小黃嫌棄地在枕頭上蹭了蹭。
次日,慕含章因為昨晚的事不適沒能起來。
景韶心疼不已,親手餵了早飯才磨磨蹭蹭地去了戰場。
秦昭然昨天喝多了在若水園住了一夜,聽說他病了忙跑來看,卻被衛兵攔在了門外:「王爺吩咐讓王妃休息,誰也不許打擾。」
「是昭然兄嗎?」屋傳來慕含章的聲音,「讓他進來。」
秦昭然推門進去,看到慕含章半躺在床上,手中還拿著一本書:「怎麼突然病了?」
「常有的事,」慕含章笑了笑,「昨日你喝多了沒來得及問,今日我便直說了,府對海商的事,你可知道?」
秦昭然看了一眼他脖頸上的一抹青紫的齒痕,心中微苦:「我知道,但我一分未拿過。」
慕含章點了點頭:「這些日子江州會有大作,你莫參與。」
接下來的一個月裡,慕含章開始著手查找江州員盤剝海商的證據,而景韶則繼續慢慢悠悠的跟顧淮卿打仗。
直到慕含章拿到了足夠的證據,帶著親兵圍住江州知府宅院的時候,他才明白當初大皇子那個沉的眼神是什麼回事。
「我可是大皇子的母舅,侯爺,不僧面看佛面,這些不過是小事,沒的為此上了皇家兄弟的和氣,您說是也不是?」江州知府冷冷地看著慕含章,這位侯爺帶來的不過百人,憑著自己手中的兵力,定能將之拿下。
慕含章看著江州知府後的兵丁,忍不住蹙眉,沒想到這小小一個知府竟然有這般大的勢力,而且大皇子定然是知曉此事的,他沒有阻止自己來江南,是不是就是為了把他代在這裡?
心中盤算著景韶撥給他的這一百人能抵擋多久,江州城裡平江五十里,讓左護軍現在回去報信不知來不來得及。
「我勸侯爺還是放下手中的寶刀,咱們進屋好商量,不然您這細皮的傷到了,下也不好向王爺代不是?」江州知府皮笑不笑的揮手,示意拿下這文淵侯。
原本是想把他綁了藏起來,過兩個月海商之事毫無進展,皇上就會斷了這個念想,卻不料有人通風報信走了消息,如今還給他拿到了證據,連累大皇子,這樣一來只能拚個魚死網破,只要這文淵侯死了……
「大皇兄何時有個做知府的母舅,本王怎麼不知道?」明朗的聲音從人群後傳來,一匹黑駿馬緩緩走了出來,景韶冷笑著跳下馬,站到了自家王妃邊。
「,王!」江州知府看到還穿著盔甲的景韶,心頓時涼了半截,「你,你不是在戰場上嗎?」
「哼,」景韶單手摟住邊的人,抬了抬手,「一個都不許放過。」說完,後的將士便衝了上去,他自己則抱著慕含章翻上馬,躲到遠去看戲。
而打了一半被晾在戰場上的顧淮卿氣得摔了手中的長刀。
幾日後,大皇子勾結江南員收海商賄賂的折子就遞到了宏正帝的面前。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