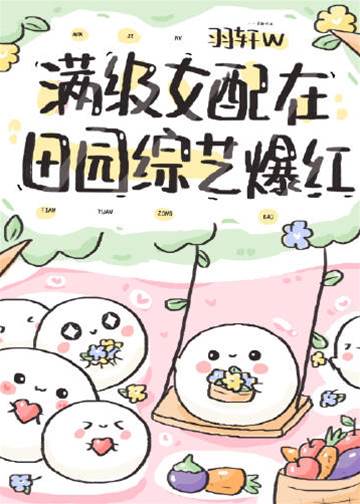《恰似你的溫柔》 《恰似你的溫柔》第5章
一回到家,我就一頭紮進了工作作坊,廢寢忘食的查閱文獻,細細的研究老照片上的紋路,就連配都不知道試了多遍。
對待工作我一向賦予十分的熱忱,有誰能夠把喜好當作事業來做,我就是其中一個。
就在我頗有就的給木箱上釉的時候,舍友小心翼翼的閃進來,雙眼放的焦灼在品上,裏不住的發出驚歎。
“你這雙手是不是得上保險啊,咋就這麽巧呢,送來的時候就跟一堆爛木頭似的,讓你幾天一折騰就變這麽上檔次的東西,你這比點石金還誇張。”
甚至神叨叨的捧著我的手一臉崇拜,我眉心一抖,先寫講料塗到的臉上。
“有話快說,有屁快放,我這正在最後的趕工,一點都馬虎不得。”嫌棄的甩開的胳膊,頭也不抬繼續最後的收尾工作,突然被打斷工作,我語氣有些衝,好在也習慣了,並不和我計較。
Advertisement
“那個背後打你悶的主使者抓到了,就是你曾經的好閨,藍心。”淺舒不恥的撇撇,我們之間的糾葛大概知道一些,連帶著不怎麽待見藍心那個心機。
我點了點頭不發一言,甚至臉都沒什麽波瀾,淺舒拳掌的手了半天,見我沒反應,焦急地追問。
“你不會就這麽吃了這啞虧了吧?”都有做好大鬧一場的準備工作了,卻沒想到我這正主不鹹不淡的比還淡定。
我垂眸點了點桌角的送貨地址,示意自己看,淺舒狐疑的撿起來,在看清收貨人的水後不由得瞪大眼睛。
“四月二十九日,君雅酒店頂樓花園餐廳,藍心收。”
有些怔忡,被這詭異的巧合整的有些發懵,半晌才嘟囔道:老天眷顧,孽緣不斷啊......
Advertisement
小時候吃的苦太多,現在我最忍不了的就是委屈。吃了這麽大的暗虧,我豈能善罷甘休!
講木箱烘幹,我興致的籌劃送什麽禮好呢?
聽說之所以能調小流氓給當打手,全仰仗前男友標哥,在道上有點名號,沒配合標哥的喜好排些小視頻,洗點小藥調劑生活。
而我,自從知道藍心是害死我媽的兇手之後,除了工作,大半經曆都用在調查上。兩年的切關注,也算是小有收獲,珍藏在鞋盒裏的優盤算是可以拿出來了。
“藍心!”我咬牙切齒的重讀這個名字,講優盤裏的彩容刻錄了幾十份,正好裝滿裝點一新的紅漆木彩繪的老木箱,準備給個大大的驚喜。
每次想起那張總是矯造作的弱小臉,我就恨不得撕碎那份天真無邪的假象。害死我唯一的親人,更是差點毀了我的清白,這次竟然還威脅我,想將我趕出榕城,這是當我蘇芒是嚇大的嗎?
Advertisement
四月二十九日,我拎著複原完好的木箱子到了君雅酒店的頂樓,靠著那位老的名,一路上暢通無阻。
猜你喜歡
-
完結1762 章
国民男神是女生:恶魔,住隔壁
三年前,帝盟解體,遊戲天才莫北,低調隱退。三年後,她女扮男裝,埋名回歸,從被人唾棄到重登神壇,引來了全民沸騰他俊美禁慾,粉絲無數,電競圈無人不識。入隊一開始他對她說“安分點,不要有非分之想。”後來她身份暴露,他從桌前抬眸,緩身站起“遊戲裡結完婚就想始亂終棄嗯”
192.6萬字8 20995 -
完結16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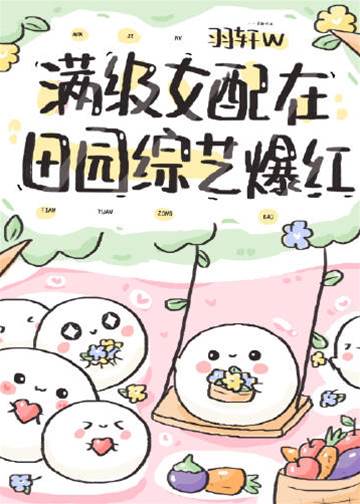
滿級女配在田園綜藝爆紅
滿級快穿大佬洛秋穿回來了。死后進入快穿之旅她才知道,自己的世界是一本小說。這是一本男頻娛樂圈爽文,男主一路升級打怪,紅顏相伴走上人生巔峰。而她,是倒貼男主反被嘲,被全網黑下場凄慘的炮灰女配。彼時洛秋剛剛進入一個復古懷舊田園生活綜藝,綜藝直播…
58.6萬字8 7292 -
完結522 章

軍婚甜蜜蜜:俏軍嫂在八零賺麻了
剛實現財富自由,準備好好享受人生的白富美左婧妍,被一場車禍撞到八零年,開局有點不妙!她成了作天作地,尖懶饞滑,滿大院都避之不及的潑婦,軍人老公天天盼著和她離婚!
81.9萬字8 177403 -
連載370 章

顧總別虐了,鐘秘書她不干了
為了當年的那驚鴻一眼,鐘意甘愿做了顧時宴三年的地下情人。 白天,她是他身邊的得力干將,替他擋酒,喝酒喝到胃出血。 晚上,她是滿足他生理需求的工具人。 整整六年,鐘意眼里只裝得進他一個人,原以為她一定會感動他,他們會走到結婚、生子的路上。 可忽然查出胃癌,她只有不到半年的生命,她才瞬間清醒過來。 跟著顧時宴的這三年,他從未對自己有過關心,從未有過愛意,甚至還要另娶他人。 心死之下,鐘意斷情絕愛,不
87.2萬字8.18 400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