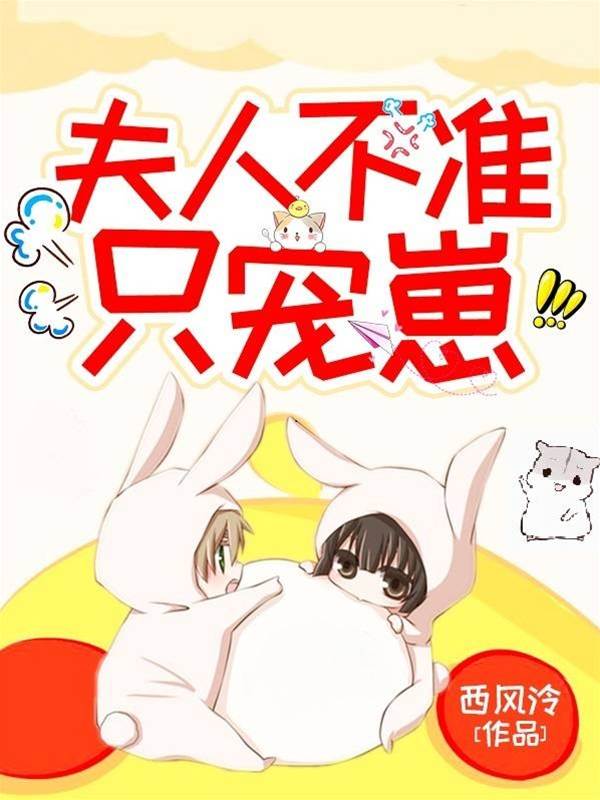《酷丫頭的貼身霸道總裁》 第100章 快叫大夫!
我幹脆靠在門口,看個現場直播。
我的監護人隻許州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連我同學親我一口都恨不能將我切了重長。
我倒是要看看,他,今兒是不是該將這張臉帶整個人皮都拔下來丟洗機泡七七四十九天?
不過,也可能,他換口味了,不要我,該要這種類型的子。
那,也沒所謂,大家說開了,我也不用繼續愧疚懺悔吃齋念佛誦經。
或者說句實話,眼下,我什麽都不想,就是想看看。
心底裏一火氣一拱一拱,想要扁人。
床上的子肯定是知道我來了,的眼睛微微的閃了一下,迅速從我的臉上劃開。
卻毫不覺得有人礙眼,或者相反,猶如演員,有觀眾愈發賣力,口齒不清的:
“殷,抱我,進,進,我要......”
腰不停的扭,猶如水蛇。
何?限製級。
佛曰,不可說,不可說。
角落的櫃機涼風不停的吹,我看看設定:18℃。
不過這個溫度顯然太高,室幾人似乎都一汗。
子燥熱的手要扯掉自己的服。
我脊背發涼,汗涔涔。這樣子,有些看不下去了。
“嗯哼,”我清清嗓子,出言提醒那子,“不要再他了,他會窒息的。等他清醒,有多吃不得,非要趁他暈過去做啥?”
我的聲音出奇的平靜,出奇的清冷,沒有一火氣,也沒有夏天的溫度,平靜的,頗有幾分舒服的風味;
外加幾分妝式特有的冷靜。
我不知道這子是誰,最終目的是什麽
不過既然舒服聽之任之,我想一定不是普通人。
雖然我有一刻有上去扁的衝,但終究沒有行。
子停了一下,扭頭看我。
眼裏......火熱、憤恨,紅......妖豔。
Advertisement
子憤怒的看著我。
我微微皺起鼻子,角微翹,安靜的回視著。
我的監護人是我的飯票,他暈了我擔心,天經地義,看我也沒用。
理由充分,怕你作甚?
子子挪了一下,低頭,準備繼續。
靠!
恨啊,這也能繼續,我佩服你五投地!
“如果你不介意去坐牢,我會考慮起訴你故意將他弄暈,意強一民男……”
不行,我想笑場了!一狼如殷亦桀之流,也有被人強一的可能。
這個世界,果然魔幻了!
努力忍著,我雙手抱斜靠在門上冷眼瞧著,聲音清冷。
我自己都懷疑,這種時候竟然還能保持冷靜,果然,我很沒人。
也許,就象是殷亦桀不會真正我一樣,我也未必真的就了他。
這份曖昧的裏,有多真的,有多演的,誰能分得清楚。
“你說什麽,他怎麽了?”
玉壺冰衝進來,邊大喊。
一看形,立刻停在在我旁邊,眼裏的神非常詭異,看看床上,看看我,似乎在欣賞一幅畫。
“他已經暈了有一會了。”
我靠著沒。
我不知道這些人的關係,但我知道別的,我要說。
殷亦桀是頭多兇猛的狼,我十分清楚。
如果他正在,本不是這個樣子。
除了他的利,他通常都是極為主的角,喜歡掌控全局,從到神,他要做控製者。
殷亦桀一向喜歡做控製者。
而現在況恰恰相反,子弄了這半天,他卻一點反應都沒有。
另外,他手臂也相當有力,本不可能讓子如此扭。
他眼睛一直半閉,整個人都的沒力,臉紅的也十分不正常。
不又不拒絕,再看他的樣子,又呼吸重,就隻可能,他早暈了。
殷亦桀暈掉的樣子我見識過,如果實在撐不住暈過去,就會這麽無力。
Advertisement
玉壺冰吃了一驚,臉大變,立刻走過去。
子似乎也知道事不好,趕爬下來,連鞋子也不及穿,跌跌撞撞的向門口跑來。
那覺,不是好事被撞破,而是有,什麽謀?
我要死了,腦子裏總想著“謀”二字,一定是心理不健康。
不過,由不得我啊!
深呼吸,我蹲下,左突然抬起來,離地一尺高。
“啪!”
如我咒語所言,麗的子,立刻五投地了。
“啊啊,好痛!”子呤著,恨恨地看我。
此時,我覺得神一陣舒暢!
舒服聽到屋裏的鬧騰,丟下手裏的事跑過來,閃到一邊避開,側奔到屋裏,看殷亦桀的形。
我緩緩的站起來,瞅了子一眼,目落到殷亦桀上。
“快大夫!讓人抓住!”
玉壺冰聲音沉穩中略顯抖,說到子時又稍有些不確定。
大家都顧不上管這子了,見連滾帶爬跌跌撞撞的逃出去,連包和服都沒敢拿。
我懶得管。
倒是殷亦桀,我也不顧得他這些日子理我不理我,玉壺冰的話讓我擔心,我......
舒服趕抱著電話開始打。
玉壺冰衝出去不知道做什麽,我靜靜的走到殷亦桀邊。
輸管一滴一滴的流著,卻都流到了地上。
殷亦桀另一隻手背上,隻有膠布,沒有針頭。
地上,了一片。
深的,浸的。
深的,猶如凝固的......
殷亦桀的上臉上,到都是人的口紅印,鮮豔奪目,要多刺眼有多刺眼。
紅,刺目驚心。
我,拳頭,不知道,該做什麽。他這副尊容,我就算幹淨也難。
沒理由,就是看著格外不舒服。
我知道他吻起來很,他抱起來很舒服。
現在愈發肯定,我不想別人到他。
Advertisement
就這樣一種覺,我希他永遠都隻吻我一個人、抱我一個人。
可是,他不要我了。
好奇怪,我一會覺得自己不會是很他,一會兒又對他的有一種強烈的獨占一!
莫非我神經已經錯了。
還是,這種東西,實在是神莫測的很。
殷亦桀艱難的呼吸著,我不知道能做什麽。
隻覺得眼角有些酸。
我,似乎知道他為什麽和我生氣這麽久了。
如果,他和我一個覺,那他,也一定特別的不希別人我。
不論我們什麽關係什麽,隻要我們擁抱過,就,一點兒也不希別人介。
可是,那次,不是我的錯,為什麽要怪我。
我現在還覺得委屈,你為什麽不睜開眼,抱抱我?
我,有種覺,不想要他吻,可是,我想要他抱。
我不了那些口紅印子,但我看見他並未用心抱那個子,所以,我想要確認,他肯不肯抱我。
我想要。
至於生氣和憤恨,委屈和失,
那些都是靠後一點的事。
是直接,舒服了就是舒服了,喜歡某人就是喜歡了,和我們的靈魂不同,靈魂由裏拐彎,連自己都欺騙!
大夫護士一陣風似的和玉壺冰衝進來,後麵還有擔架車。
不容分說,和玉壺冰抬起他就往擔架車上放。舒服和護士推著擔架車就跑......
我隻是挪個位置,不擋住他們急救。
現在,屋裏,就隻有我,呆呆的站在原地。
一旁,地上的深的水跡還在;
床上,子的還在;空氣中,悶熱還在;我心中,霾還在......
好神奇的事,簡直太不可思議了!
對著窗外梧桐思索半天,我才想起來,似乎,這有點兒李國豪死亡現場。
原本是一場戲,結果道槍讓人換了真槍,空包彈換實彈。
Advertisement
於是,男主角,倒下了。
呃......我脊背一陣寒涼,趕從空調口挪到另一個角落,可上的寒意還在。
我,上冷得發抖。
我想出去看看,或者到殷亦桀邊去,隻有他才能給我堅強的依靠。
我從未如此熱切希,有個人能讓我靠一下;而這個人,隻能是殷亦桀。
可是,他不在這裏,他去了急救式。
他正在輸卻被人拔掉,看地上的水漬,拔掉的時間不短。
為什麽,為什麽會這樣?
看舒服的意思,還有玉壺冰的覺,一定認識那個子,就連逃走,二個人都沒有抓住的意思。
為什麽,難道是我搞錯了,還是那個子是臥底?
嗬,我的想象真富。
我剛才想到那個人的激,現在又想到是臥底,我......
我抱著胳膊,靠在牆上,我冷。我怕。
使勁咬著牙齒,還是抵擋不住這層涼意。
額頭上汗不停的掉,我,都搞不清究竟是冷還是熱了。
房間裏隻有我一個人,不知站了多久,還是沒人來。
殷亦桀也沒回來,看來況不容樂觀。
我走到門口,樓道裏很安靜,雖然是下午正常探時間,不過人不多。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道急診室或者哪裏去找找殷亦桀。
可,我不知道那樣做意義何在?
我,是該回去,還是去看住我的監護人?
一遍遍的想著,剛才的形,還有那個子,以及整件事。
腦子裏揮散不去的,盡是“謀”二字。
當然,這麽大的謀,不可能針對我,我還沒這麽重要。
那麽,就隻可能是殷亦桀。不論他之前了什麽傷得了什麽病醉什麽樣,估計吊二天藥也就差不多了。
不過被人這麽一掐斷,反而會有生命危險。我這麽胡猜來著。
那麽,他到底會有多危險?
別人,是要讓他有危險,還是要置他於死地?
我,該做什麽?
我,又能做什麽?
將門虛掩上,我挪回到室與小客廳之間的門口,靠在上麵。
那是我看著殷亦桀的地方,我看見他暈掉了,然後按捺住心頭不快開口的地方。
如果,我憤然拂袖而去,會怎麽樣?
如果我撲上去和那子打一架,又會怎麽樣?
恩,估計那一跤五投地也摔得也夠嗆的。
早知道我該再踹上二腳,那樣或許殷亦桀就沒事了。
阿彌陀佛,無量天尊,阿薩拉姆,艾賴以昆,哈裏路亞......
我現在能做的,似乎就是坐等。
看人家電視上,家屬也就是在急診室外麵幹等。
我,嗬,我夠冷靜啊。自己飯票出了大事,也能安靜的坐等。可我不坐等又能如何?
眼睛朝屋子轉了二圈,裏麵一圈,外麵一圈。
裏麵,是殷亦桀住著的,這會兒稍顯淩。
我不想收拾,或許還要留個現場。
如果他有個三長兩短,估計這還有用。
外麵,我目落在那件馬甲和時尚包包上。
我,忽然對包包產生了興趣。
不過,我的書包呢?舒服把它理到什麽地方去了?
小小的客廳,旁邊,似乎有扇門,似乎,可以通到隔壁那間屋子,和這個類似。
就像,有些飯店的包間,二間包間之間的作間相通。
我過去試了下,果然,二個推拉門,雙向都可以鎖定,確保既可以獨立又可以聯通。
我,既然大家都不在,我要去找我的書包,還有我的刀子。
我要做好準備,如果還有人敢來試試,我一定會捅一刀,死活不論,反正是在醫院。
我有些擔心那個子,更擔心如果真的有人意圖對殷亦桀不利,那麽,這之後一定還會再傷害他。
不,不!不行!
我一定不要人傷害到他。
他是我的,監護人。簡稱“他是我的”。
隻要冠以“我的”名頭,我就要對他負責,我要行使自己的權利。
比如,要求他盡到監護責任。
前提,就是他平安無事。
看,我現在腦子多清晰,比哲學家還哲理。估計世上比我沒人的也沒幾個。
嗬,那又如何?
撲在死人上哭以及守在急診室外麵急,我私下以為還不如回去睡一覺醒來繼續做該做的。
因為,我的路就是這麽一步步走過來的。
我父母走了,我也沒有哭的權利。
嗯,丟開這些七八糟的。
趕開始,研究眼前的東西。
我想翻翻謀子的包包,雖然我以前沒有翻人家包包的習慣。
不過作為一個嫌疑人,我作為我監護人的捍衛者,似乎有這個權利。
或者,誰管那些個,我就是疑,想翻翻。
猜你喜歡
-
完結106 章

對你不止是喜歡
唐馨暗戀自己的老板四年,那會兒老板正在追她的閨蜜,她作為他的隊友,陽奉陰違,成功把他PK出局后。她趁虛而入,卻在告白時被他拒絕:“抱歉,我們不合適。” 然后,她干了一件大事—— 她當著助理的面,把老板撲在辦公桌上強吻了,水亮的眼睛對上他那雙復雜的眼,低低地說:“這樣也算得到了,以后也不會再惦記了。” 后來,唐域發現這姑娘當真不惦記了。 他卻一天比一天煩躁,她怎麼能說不喜歡就不喜歡?還說只喜歡他的臉和錢。 這他媽什麼扭曲的愛情觀。 唐域一直致力于糾正唐馨扭曲的愛情觀,卻常常被她帶進溝里,順便瘋狂愛上她,總裁包袱掉一地,騷話滿天飛,最后不得不用“暴力”治服她—— “叫唐爸爸也沒用!” —— 三觀總是被狗吃的霸總X永遠有心機應付霸總的小富婆。 小富婆日記:在他徹底愛上我之前,我一定不會承認,我當初對他一見鐘情了。 文案二 據助理匯報,劇本會議上,唐馨跟另一個編劇吵得不可開交,毫不退讓。 唐域聽完,問:“原因?” 高助理:“另一個編劇要給女二加戲,唐小姐說那段戲加進去女二就是個傻缺,還拉低男主智商情商,那編劇氣哭了。” 唐域起身,一走進會議室,那編劇就哭訴:“唐總,你評評理!” 唐域看了她一眼,淡淡地說:“抱歉,我評不了,我跟她吵架從來沒贏過,得哄著讓著。” 其他人:…… ——
36.6萬字8.38 93047 -
完結434 章

柏少夫人太撒野
容知從小被抱錯,在鄉下生活十八年,家裡窮,高中就輟學打工 十八歲親生父母找上門,說她是京城容家少爺,來接她回京城 上有盯家產叔伯,下有親生兄姐 她被父母警告:向你哥哥姐姐多學規矩,不要惹是生非,容家丟不起你這個人 容知撥了撥額前的碎發,笑顏如花:“好的。” 所有人都等著看這個不學無術一事無成的容三少笑話,結果看著看著,人家混成了京城說一不二的太子爺 眾人:這跟說好的不太一樣? ? * 柏家家主回國,京城所有世家嚴陣以待,唯獨容家那位依舊瀟灑 某日宴會,眾人看見那位站在金字塔頂端的柏家主彎下腰來,手裡提著一雙高跟鞋,語氣無奈:“嬌氣。” 再一看他身前那個穿著黛青旗袍的長發女子,光腳踩在他的皮鞋上,“我就嬌氣,你管不著。” 這熟悉的臉,這熟悉的囂張語氣... 眾人瞠目結舌,大跌眼鏡:容三爺? ! 【前期女扮男裝+微科幻+無邏輯+爽文+1v1sc】
74.9萬字8 69986 -
完結10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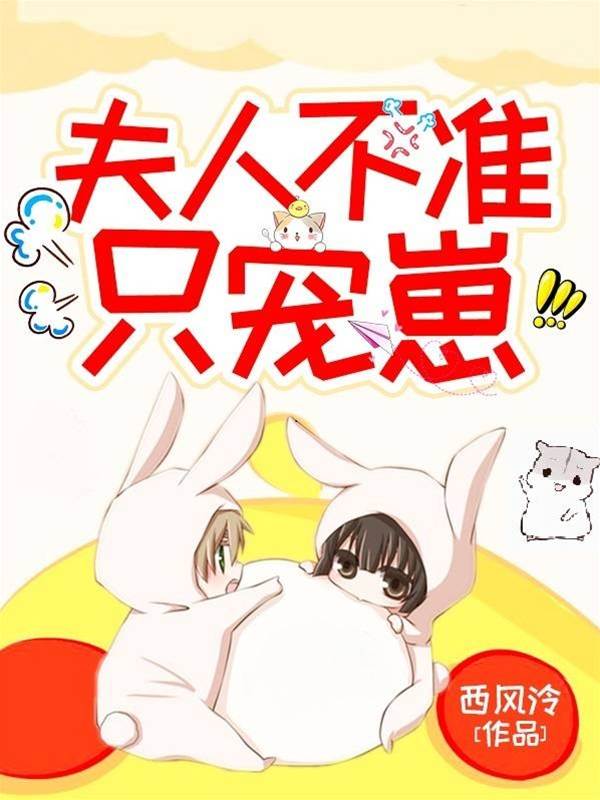
夫人不準只寵崽
南悠悠為了給母親治病為楚氏集團總裁楚寒高價產子,期間始終被蒙住眼睛,未見楚寒模樣,而楚寒卻記得她的臉,南悠悠順利產下一對龍鳳胎,還未見面就被楚家接走。
24.6萬字8 6796 -
完結695 章

她撕碎孕檢單消失,段總終於慌了
【雙潔】【帶球跑】【先婚後愛】林織羽發現懷上雙胞胎那天,還沒有來得及告訴段渡深,段渡深的白月光回來了。他向她提出了離婚。“如果我說我不願意呢?”“你知道,我不會再讓她因為任何人受委屈。”林織羽無言以對,隻能將懷孕通知書藏在了身後,選擇放手。三年後,他們在陌生城市狹路相逢。彼時,她是堅強努力的單親媽媽,帶著父不詳的萌寶,在酒店做著服務生工作。一見麵,莫名其妙失憶的狗男人就將她堵在門口,“你領口拉這麼低,身上這麼香,是不是想勾引我?”規規矩矩穿著酒店職業裝,素麵朝天的林織羽氣紅了臉,看著這個不要臉的男人,“段總,請自重!”後來,林織羽又懷孕了,她氣急敗壞找段渡深算賬。悄悄將動了手腳避孕藥丟進垃圾桶,男人無辜道:“老婆,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誰是你老婆?”“都懷了我的孩子,你不是我老婆是誰?”“……”
86.1萬字8 99334 -
完結148 章

趕我走後,姐姐們求我原諒
簡介: 蘇霖剛剛確診絕癥,就接到大姐電話,她們找到了自己的親弟弟,蘇霖的親生父母也被找到。 蘇霖這個替代品被毫不猶豫地拋棄,趕出了蘇家。 蘇霖終於明白自己為什麽總是得不到姐姐們的認可,哪怕他萬般討好。 他隻得接受了這一切,但他被趕出蘇家的影響還不止於此,剛剛回國的女友選擇分手,一直苦追他的學妹罵他是騙子。 蘇霖默默回到自己真正的家,看到家人因尋找他多年而過的苦日子後,蘇霖決定讓他們過上好的生活。 而之後的時間,姐姐們在蘇霖不在身邊後,各自的生活都出現了難以接受的變化,蘇霖這些年的默默付出也漸漸被她們得知。 她們知道全部真相後,紛紛來到蘇霖麵前,痛哭著祈求蘇霖原諒……
28.1萬字8.18 497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