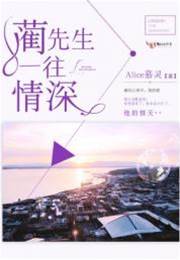《荒野植被》 61
說:“以免給他任何希。”
許言沒有回答,他清楚湯韻妍絕不是會夸大其詞的人,他在腦海里反復回憶早上和沈植對話時有什麼異常,但唯一能作為線索的只有最后那幾秒——沈植險些站不住的樣子,以及逃避對視的眼神。
熬了個通宵,許言凌晨五點才收工回家,他累得睜不開眼,洗完澡后倒頭就睡,按理說應該能睡得很香,但并沒有。這一覺不太安穩,做了些七八糟的夢,夢里的畫面斷斷續續,大學時寬闊的場,籃球場上蹦跶的球,樹影斑駁的一地落葉,取景里模糊的臉,只有那雙眼睛很清晰,墨黑的,過來。
他和那雙眼睛對視,很久,沈植的眼睛。
你要說什麼。許言想問他,他覺沈植有話要說,沈植卻始終沉默。
“不說就算了。”許言閉上眼。
“救我……”
低啞痛苦的嗓音,許言猛然睜眼,但已經不在夢里。
許言從床上坐起來,低著頭發呆,他昨天把話說得那麼重,歸結底是想法不夠堅定。心剛剛化一點,就被迫又僵起來,束得高高的,收,懸空,如此反復,太罪了。
但凡他真的可以對沈植做到視而不見心如止水,也不至于用再出國一次來做威脅。
聽起來很堅決,仔細一想就會發現里面包含了多心虛、搖、矛盾。
已經十二點了,吃過午飯就要去攝影展,許言發了會兒呆,起床洗漱。
出門前收到一條快遞短信,許言下樓去快遞柜取件,他不太清楚是什麼,拿到車上以后他把小小的快遞盒拆開,在氣泡的最里面,是一摞單反存卡和幾個U盤。
許言愣愣地看著那些東西,幾年前他剛和沈植分開,讓沈植把這些寄過來,但沈植說找不到了,結果今天它們卻毫無征兆地到了自己手上。
Advertisement
看了一眼發貨地址,是沈植的小區。
許言往后靠在椅背上,他很想問問,之前為什麼不給?找了三年才找到嗎?現在寄過來是什麼意思?
還想問問,為什麼你又進醫院了。
太久沒來這座城市了,攝影展結束后,許言跟朋友一起吃了晚飯,對方喜氣洋洋地給他看兩歲兒的萌照,許言一邊看一邊想到葉瑄也懷孕了,高興的。
吃完飯又坐著聊了很久,出餐廳時已經是十點多,許言跟朋友道了別,上車。這塊地方他很,是離沈植家最近的大商圈,到了街盡頭,右轉,過一條江大橋,再開幾里路,是個公園,繞過公園就是沈植的小區。
許言以前出來買夜宵,開到橋上時總要降下車窗,吹晚風,看燈火,聽船笛。他不止一次地想,要是沈植能跟他出門買東西就好了,風景這麼棒,一起看看。
沿著大道開到盡頭,右轉,許言看著前路,筆直往前開是江大橋,走右行道會進快速路。如果要回家,他應該變車道走快速路,接著上高速。
許言握著方向盤,前方大橋上燈灼灼,無數車流匯,開向橋的那一端。
該變車道去快速路了,但許言遲遲沒有打轉向燈。岔道口的那塊藍指示牌很顯眼,白字反著,指示直行或右行,越來越近,離必須變道的終點也越來越近。
還剩七米。
“沈植進醫院了。”
還剩六米。
“不清楚,但應該不是小病。”
五米。
“我記得明天下去你會去那邊參加攝影展,要是有空,可以順便去看看他。”
四米。
“當然,如果你覺得沒有必要,完全不關心,那還是別去吧。”
三米。
“以免給他任何希。”
Advertisement
兩米。
“救我……”
許言的心重重一跳,深吸口氣,維持直行路線,朝大橋開去。
橋上風景依舊,許言有點恍惚。下橋后開過公園,車在小區門口被攔住,門衛過來敲窗,許言懷疑自己進不去了,但門衛仔細看他幾眼,笑起來:“許先生?”
許言才發現保安沒換人,不嘆對方的記憶力。他點點頭:“好久不見。”
他被下車做人臉識別——通過。沈植一直沒讓人刪掉許言的信息,他依然可以自由進出小區。
車緩緩停在路邊,許言轉頭看著房子,里面一片漆黑,不知道沈植在不在家。
許言下了車,推開圍欄門,那棵白玉蘭比以前高了。他走到大門前,應燈亮起,許言盯著電子鎖,抬手,食指指腹按上去,嘀哩哩幾聲,門打開了。
門外的燈照亮玄關,也約約照亮客廳其他地方,總還是看不太清。但許言有種很怪異的覺,這種覺從房子的各個角落里一點點向他聚集,像來的藤蔓,纏住他的腳腕。
作者有話說:
后天更
第54章
你走的時候,就算沒有刻意去記離開時房子里是什麼模樣,但無論時隔多久再歸來,都會看出變化,因為日常的記憶已經習慣地刻在腦子里。
同樣的,當它完全沒有任何改變,你也能瞬間察覺。因為眼前的場景會和記憶中的畫面無重合,清楚告知你這里還是原來的樣子。
就比如許言從腳下的玄關,到開燈之后整個明亮的客廳,看過去,如果不是這幾年的記憶還在,他會懷疑自己本就是才剛離開了一兩天,甚至再短一點——一頓晚飯的工夫。
窗簾、沙發、地毯、壁畫、茶,玄關的拖鞋、靠枕的數量、茶幾上的雜志、懶人沙發里的遙控、垃圾桶和落地燈擺放的位置……許言在客廳里走了一圈,開始變得不能置信——眼前的一切,它們的樣式、數量、位置,跟三年前他離開時都一模一樣分毫不差,幾乎讓他錯以為這棟房子幾年間都沒住過人,所以才能一直維持原樣。但它干凈整潔,垃圾桶里有幾個紙團,玻璃茶壺里盛著半壺白開水,勉強可以作為有人居住的證明。
Advertisement
餐廳也是,廚房也是。許言站在冰箱前,看著門上的冰箱,有幾個是他旅游帶回來的,有幾個是網上刷到覺得喜歡買的,看起來舊了些,但一個不。冰箱右門上的留言板也還在,寫著“記得喝酸!”,左下角畫了個丑丑的笑臉,都出自許言之手。
以前沈植覺得許言畫得丑,總會手把那個笑臉抹掉,他抹一次,許言就重新畫一次,堅持不懈,百折不撓。
許言在冰箱前站著,站到都酸了,麻了。他轉上樓梯,到主臥門前,不知道沈植在不在里面,許言敲了敲門。
沒回應,許言打開門,房間里漆黑一片,只有臺燈亮著,他徑直走過去,臺的茶幾上歪著幾個空酒瓶,風一吹就酒氣陣陣,只是沒見到人。許言回頭看,床上是空的,但約可以看見左邊枕頭上有個黑乎乎的東西。
心跳不控地快起來、重起來,許言手到開關,視野驟然明亮的那刻,他看著那只墨綠的小鱷魚,覺有一雙手狠狠按在肩上,異常沉重的力道,將他整個人向下,讓他不能彈。
很久以后,許言的目才艱難移開,床頭柜放著他以前常用的水杯,那本沒看完的書倒扣著,許言還記得是看到第157頁——之所以記得,是因為沈植曾經隨口問了他一句看到哪里了。
許言走到床邊,拿起小鱷魚了,是原來那只,很,丑丑的,肚子底下有點線,小小的破口里可以塞進一/手指頭。
他看得出神,忽聽見帽間里傳來一聲很輕的悶響,許言放下小鱷魚走過去,打開燈。往里走,還是一左一右兩個大大的柜,沈植的柜關著,但許言的柜是開的,里面的壁燈亮著,懸掛的服被全部推到一頭,留下半個柜子的空間。
Advertisement
許言停下腳步,站在那里,一不,他的表變得茫然和震驚,微微睜大雙眼。
柜子里掛的依然是他從前的服,而沈植正蜷在空出的那一半位置里,膝蓋曲起,頭歪著抵住柜板。從許言的角度看過去,他的側臉、耳朵、脖頸都是紅的,顯然已經喝了太多酒。他懷里還抱著一件灰衛——許言的。
猜你喜歡
-
完結3081 章
名門掠婚:顧少,你夠了
他許她一世,寵她入骨,待她如寶。她以為這就是所謂的幸福。 一朝從雲端跌落,粉身碎骨,她黯然退場。 五年後,再次重逢。 “蘇可歆,我們和好吧。” “我們已經錯過了五年,想和好?晚了!” “隻要是你,多久都不會晚。”
556.3萬字8.46 3543363 -
完結110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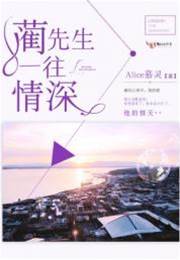
藺先生一往情深
曾有記者舉著話筒追問C市首富藺先生:“您在商界成就無數,時至今日,若論最感欣慰的,是什麼?” 被眾人簇擁,清俊尊貴的男子頓步,平日冷冽的眸難得微染溫色,回答:“失而複得。” - 人人都說她死了,藺先生心裡有一個名字,彆人不能提。 他走她走過的路,吃她喜歡吃的食物,人前風光無限,內心晦暗成疾。 情天眉眼寂淡:有些愛死了,就永遠不在了。 他眼眸卻儘是溫然笑意:沒關係,沒關係。 她的心再冷,他捂暖。 世人隻知商場中藺先生殺伐決斷手法冷酷,卻從不知,他能將一個人寵到那樣的地步。 - 但後來 人來人往的步行街頭,商賈首富藺先生仿若失魂之人,攔著過往行人一遍遍問—— “你們有冇有看到我的情天……” 他的情天,他的晴天。 · ·寵文·
138.8萬字8 78105 -
完結14 章

我在未來等你
用來穿梭時空的不隻有機器貓的時光機,還有潔白妖嬈的“Tears Stars”;給予溫暖的不隻有身邊的熟悉麵孔,還有來自未來的那個不可思議的少年。當人小鬼大的小惡魔弟弟演變成5年後翩翩少年的模樣,迷糊少女童童還會當他是弟弟嗎?可是,5年前的她和5年後的他該怎麼讓浪漫延續呢?人氣作者西小洛力作——《我在未來等你》絢麗登場!
10萬字8.18 290 -
完結210 章

崇樓如故
簡介: 眾人皆知,江北名尉沈崇樓寵愛義妹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他縱容她的驕傲,不許任何人踐踏她的自尊,單槍匹馬深入險境,隻為護她周全。可他也親手給她披上嫁衣,將她送上花轎。午夜夢回,她卻纏上他的頸脖,壓他在下。女人笑顏如花:“三哥,你這麽希望我嫁給他?”再見,她跪在他麵前,苦苦哀求:“隻要你救他,我什麽都願意給。”他冷笑著捏住她的下巴:“沈如故,你好樣的,為了他,你竟連自尊都可踐踏在腳下。既然如此,送上門的不要白不要。”眾人皆道:紅塵素錦,崇樓如故。家國天下,本是他的抱負。後來,沈崇樓才明白,任由時光流轉,他終究逃不開她。
52.3萬字8.18 228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