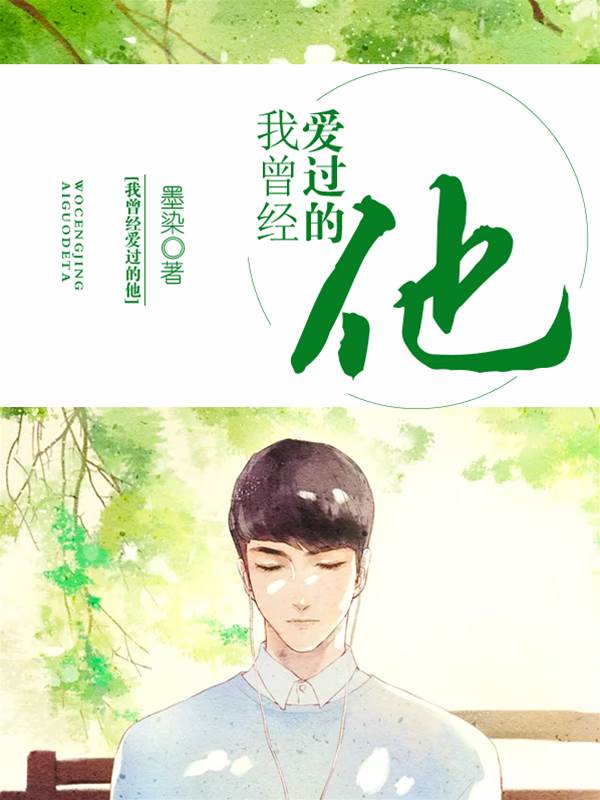《荒野植被》 65
意外的,現在有答案了,“他”是許言。
“許言,他朋友過生日的時候我們見過。”藍秋晨的語速很快,“他知道我是心理醫生。”
沈植因為他這句話才回神,側頭看他,嚨了,好像開口都困難。過了一會兒,沈植終于說:“你先走。”
其實他想說的不是“你先走”,而是“你快走”。如果他是正常的,他會很坦然,無所謂藍秋晨有沒有和許言見過,無所謂許言知不知道藍秋晨是心理醫生。
但偏偏他病了,于是連和心理醫生出來吃頓飯都了瓜田李下,他做賊心虛,沒有自若無懼的底氣,完全沒有。
“回車上以后給我打電話。”藍秋晨低聲說,“或者任何時候,覺得不對勁就聯系我。”
就沈植這種狀態,藍秋晨很忐忑,怕他又像前兩次那樣出狀況。
藍秋晨說完就干脆地往另一邊走,與此同時,到視線的許言轉過頭來,正好只看見沈植一人站在臺階下。
日落了,沈植后是燈明亮的餐廳,許言看了他片刻,扭回頭,對宋謹說:“那就這樣,辛苦你了,等我回來我們去房子里看看。”
“好的。”
“你等會兒去哪?我送你過去吧。”
“不麻煩了,有人來接我,應該快到了,我去商場那邊跟他會合。”宋謹看了眼手表,“下次見,開車小心。”
“好,拜拜。”
目送宋謹往前去過斑馬線,許言在原地站了會兒,轉朝沈植走過去,隨意地問:“來這吃飯?”
沈植一直很出神,哪怕許言走到面前了都還怔著。他覺許言的聲音很遠,反應了幾秒,答非所問:“我不知道會到你。”
Advertisement
他怕許言覺得他是在制造偶遇,他剛剛應該一走了之的,在許言看見他之前,但實在邁不開,說不上是沒力氣還是心有不舍。
“我不是這個意思。”許言說。他看見餐廳里有一群人正往門邊走,怕攔住他們的路,他手拉了下沈植的手腕,“走。”
溫熱的手心只在腕上很短暫地停留了一瞬間,沈植慢半拍地低頭看自己的手腕,接著他聽見許言問:“趕時間嗎。”
“不。”沈植覺自己的聲音輕得要飄起來,他懷疑許言沒聽到。
但許言聽到了,他說:“那你跟我去車里拿個東西。”
要拿什麼?沈植想不出來。他和許言并肩走在一起,整個人沒有實,腳下是虛浮的,只有在偶爾到許言的肩膀時才離那種恍惚,暫時地回到現實。
沒走兩分鐘,到了車邊,許言解了鎖,打開副駕門,彎腰鉆進去,到儲箱里拿東西。沈植站在一邊,像考生遇見了一道能力范圍外的題,不會做,思考無果,只能等別人給他答案。
許言很快直起,把一個小小的快遞盒遞給沈植。
里面是那摞儲存卡和U盤,沈植前幾天寄給他的。
這是分開后許言唯一問他要過的東西,沈植在決定把它們寄回時用了很大決心。它們就像一個句點,許言早就畫了無數個,沈植一直負隅頑抗,最后終于狼狽認輸,親手把自己應該代的句號畫下。
但許言告訴他已經用不上了,說會考慮考慮把它們給他。沈植沒抱希,可是當許言真的遞過來的時候,沈植才發覺自己沒辦法收下。
Advertisement
是他問許言要的,許言給了,為什麼他卻不想要了?原來是他費盡力氣畫下句點,以為就到這里,但許言更狠心,當著他的面又重復了一次。
微弱跳的心被扔進沸騰的油鍋,炸得滾燙冒泡,來來回回反反復復,還是會覺到痛。怎麼辦,別折磨我了,沈植幾乎想要掉頭離開,起碼這時候還有能力跟許言說一聲再見。
“你不是說要嗎。”許言見他半天不接,問。
沈植堪堪回過幾分神,不等他開口,許言又說:“我等會兒去機場,七八天以后回來。”
他本來打算出差回來之后再說的,但既然今天這麼巧見沈植了,也算是種詭異的緣分,不如順其自然把話講了,反正是遲早的事。干脆點,對大家都好。
沈植總算抬起手,接下那個快遞盒,手得很明顯,他不知道許言看見沒有。沈植盡力平穩地呼吸了一個來回,說:“路上小心。”
“好的。”許言回答。無暇顧及這種對話是否稍顯生,他忽然間手心出汗,久違地心跳加速起來。
就像他七年多前跟沈植告白,即便現在立場不同、景不同、心境不同,但他看著沈植,那份張的悸再次冒頭——因為他們即將面臨一段全新的關系,雖然不知道最后結果會怎樣。
試一次吧。
“沈植。”許言有些嚴肅地他。
沈植想往后退,害怕許言說出更多的,讓他無法承的話。
夕的余暉被建筑切割一道筆直的線,剛好罩住上半。他們面對面站著,晚風從兩人之間吹過,吹散過往,喧囂遠去,這里很安靜。
Advertisement
“嗯?”沈植半晌才艱地回答出一個輕音。
許言看著他的眼睛,說:“我們可以試試。”
作者有話說:
沈植(死機):……?……???……???!!!!……???!!!!!!!!?????!!!!!!???????!!!!!!???????!!!!!!!
沈植(已冷靜):是幻覺。
【甜分正在制造中】
第57章
因為料想不到許言會說這句話,以至于沈植完全沒反應過來。像踩在頂樓邊緣,差一步就要縱往下跳,他已經準備跳了,角卻被很輕地了一下,其實那力道不足以拉住他,但偏偏勾起了他最后一點求生。
他回頭,想看清拉住自己的是什麼,可只看見一片白茫茫的霧。
“你……”沈植知道自己在說話,也知道說了什麼,但他似乎聽不太清自己的聲音。目難以聚焦,他啞地問,“你說什麼?”
“不要裝聾。”許言說。
眼前的霧忽地散了,沈植站在樓頂的風里,回頭看去,拉住他的是許言——九年前的許言,七年前的許言,三年前的許言,此刻的許言。好多個許言重疊在一起,青的眉眼變得穩重,探詢的眼神變得篤定,淚水變倒映在眼底的那抹帶著日落云霞的,時差被調停擺正,那句話也被清清楚楚地回憶起。
許言說的是:我們可以試試。
沈植曾經懷著混加晦不明的緒對許言說過同樣的話,他的試探、猶豫、誤解,在后來很長的一段時間里給予許言無數痛苦和折磨,讓許言心灰意冷。
Advertisement
這句話是他們錯誤的開始,但許言現在讓它為了新的起點。
心臟到這一刻才重新跳起來,飛快加速,要沖破口。沈植像一個溺水已久的人,終于得救,被拽上岸,站在下,重獲暌違多年的痛快呼吸。但因為氧氣攝過于猛烈,腦袋眩暈,他差點沒能站穩——是需要給藍秋晨打電話的反應。
“許言……”沈植想手抱他,又怕這是夢,到就會碎——他陷兩難的境地,手抬起又放下。
許言冷靜地說:“我和你不一樣,我說試試,就是認真地跟你試,會擺正心態好好對待。如果可以,就重新開始,如果不行就算了,接嗎。”
要是現在的他們仍然無法建立好一段,那說明的確不合適,輸也輸得心甘愿了。
沈植努力地把許言的這段話聽進去,逐字逐句,在腦海里進行嚴謹分析,終于確定許言是真的要跟他試試,如果,如果可以——他們會重新在一起。
一顆心從萬里高空被拋下,眼看就要跌到底,砸碎,沈植已經不打算自救,可怎麼就被完好無損地托住了,再被輕輕放上云端,不可思議。
“你為什麼一臉考試做題的表。”許言看著他,“我的話那麼難懂嗎。”
猜你喜歡
-
連載919 章
強勢萌寶:爹地彆自大
傳聞,夜氏總裁夜北梟心狠手辣,殘忍無情。雖然長了一張妖孽的臉,卻讓全城的女人退避三舍。可是,他最近卻纏上了一個女醫生:“你解釋一下,為什麽你兒子和我長得一模一樣?”女醫生擺弄著手裏的手術刀,漫不經心:“我兒子憑本事長的,與你有毛關系!”夜少見硬的不行來軟的,討好道:“我們這麽好的先天條件,不能浪費,不如強強聯手融合,再給兒子生個玩伴……”五歲的小正太扶額,表示一臉嫌棄。
92.8萬字8 27690 -
完結19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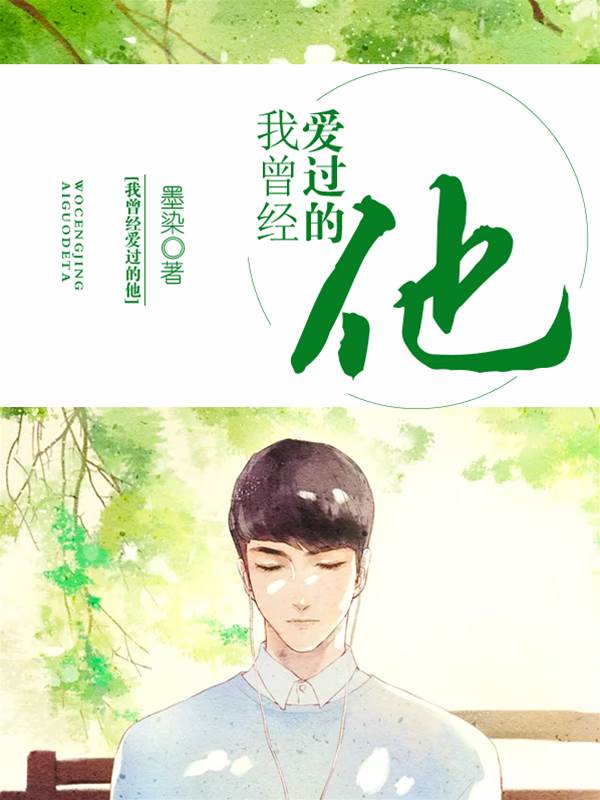
我曾經愛過的他
我為了躲避相親從飯局上溜走,以為可以躲過一劫,誰知竟然終究還是遇上我那所謂的未婚夫!可笑的是,所有人都知道真相,卻隻有我一個人被蒙在鼓裏。新婚之日我才發現他就是我的丈夫,被欺騙的感覺讓我痛苦,他卻說會永遠愛我......
33.5萬字8 10022 -
完結125 章

信不信我收了你
作品簡介(文案): 京都最近新聞很多。 號外一:聽說陳市長家那個被拐賣的小女兒找回來了,據說被賣到了深山溝裡,過的可苦了。 號外二:聽說陳市長家的小女兒是個傻的,天天說自己能看見鬼。 號外三:聽說陳市長家的小女兒強吻了樓部長家的三公子。(眾人驚恐臉:樓銘都敢惹!!) 陳魚把樓銘按在沙發裡親了好一陣。 陳魚問道:“感覺好點沒?” 樓銘瞇起眼:“丫頭,別逼我動心。” 陳魚懵逼臉———我只是在救人。 會抓鬼的小仙女VS溫柔腹黑病嬌大叔(大約) 其他作品: 《小藥包》、《重生在民政局門口》
44.9萬字8.08 12858 -
連載809 章

沖喜新娘:霍少天價小嬌妻
白家破產后,白曉嫻為拿回母親遺物、重振白家。自愿嫁給一個植物人。當眾人都在嘲諷她為了錢饑不擇食時,卻發現她被頂級豪門寵上了天。被欺負,婆婆撐腰,爺爺砸錢。而植物
168.3萬字8 398430 -
完結550 章

閃婚娶了個小祖宗,傅總拿命寵
【先婚後愛 雙潔 年齡差 甜寵 雙向奔赴】沐淺淺為了救老奶奶意外失明,三天就和老奶奶的孫子閃婚了!視力恢複前,沐淺淺每天都擔心,自己嫁給了一個沒車沒房的醜男。複明後,男人挑起她的下巴,薄唇微勾,“淺淺,對你老公這張臉還滿意嗎?”原來她男人不僅是絕世帥哥,還是千億豪門的繼承人!……傳聞中,傅家掌權人年近三十不近女色,不是身懷隱疾,就是取向異常。隻有沐淺淺知道,那位黏人又傲嬌,吃起醋來可怕得很。
97萬字8.18 5857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