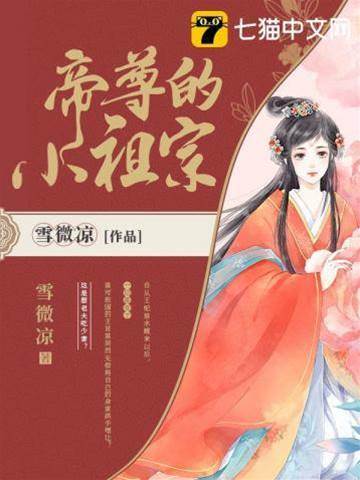《鸣蝉》 第50章 第50章
謝嘉瑯院子里當差的不是書小廝就是仆婦,好像是頭一次看到有年輕漂亮的丫鬟。
"是誰?"
青答道"是大爺撥過來服侍郎君的,小霜,還有一個是小翠。"
謝蟬走進書房,回頭看小霜,心早嘀咕,昨晚小霜來傳話,今天就了謝嘉瑯院子里的丫慧…·…
一時走神,沒注意腳下,哐當一聲撞在小香幾上,疼得倒吸一口冷氣,晃了幾下沒站穩,人往前撲倒。
眼前一道影靠近,一雙結實的胳膊過來,穩穩地扶住手臂。
謝蟬隨著慣朝前撲進謝嘉瑯懷里,雙手著他的盤領袍。
謝嘉瑯站得筆直,等靠著他站穩了,退后半步,扶坐在褥子上,雙眉微皺"在想什麼?"
謝蟬右邊小疼得厲害,隨便找了個理由"在想繡莊賬目的事……"
Advertisement
不好意思說因為小霜的事走神,他房里添不添丫紫是他的私事,不到說什麼。
謝嘉瑯抬眸看臉,眉頭仍然皺著,手托住的右,"能直嗎?"
謝蟬了兩下,直吸氣"疼。"
那一下剛巧撞在香幾下面的橫牙上。
謝嘉瑯放下謝蟬的,找來兩枚靠枕墊在底下,"坐著別。"
他快步走出去,要青馬上去灶房取一些存的冰過來。
青飛快跑著去了。"郎君想要什麼?"
小霜在院子里站了半天,終于看到他出來,強忍激,上前出聲詢問。
謝嘉瑯看一眼,沒作聲。
小霜還想再問,畏于他上的沉冷氣勢,沒敢問出聲。
不一會兒青端著一盆冰和巾子回來,謝嘉瑯接過,轉回書房,俯,坐在謝蟬面前的席子上。
"團團,子拉起來。"
Advertisement
他眼睫垂著,看著的,低聲說,"我看看你的,要是淤青了,冷敷好得快點。"
謝蟬拉起一點子,解開羅,出傷的地方,雪白上已經淤青了一塊,不過沒有破皮出。
謝嘉瑯先用巾子包住傷的部位,要放冰塊時,忽然想起一件事,作頓了一下。
"這兩天能不能涼?"他低聲問。
謝蟬愣了一會兒,意識到他在問什麼,哭笑不得他怕上有月事,不能涼。
他怎麼會知道這些!還突然想起這個!
謝蟬覺得自己好像應該窘迫,但是謝嘉瑯神沉靜,一點看不出尷尬,好像關心這個并不是什麼奇怪的事,便也不窘了,道"沒事,可以冷敷。"
謝嘉瑯章起冰塊,幫冷敷。
不知道是不是錯覺,謝蟬覺得疼痛好像減輕了一點。
謝嘉瑯要先別起來,先靠著看書,起出去,掃一眼立在階下頻頻往這邊張的小霜,問青"是哪個院里的人?"
Advertisement
青道"郎君,是大爺撥過來服侍您的。""
"回過父親,送回去。"謝嘉瑯面無表,"我院子里的人夠了,不用添人。"
院外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仆婦進門檻,"郎君,文家郎君來看你,大爺請郎君出去。"
青詫異地抬起頭,看著謝嘉瑯"郎君,咱們才回府,文家郎君怎麼這麼快來了?"
謝嘉瑯回頭看一眼書房。
文宇很著急。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