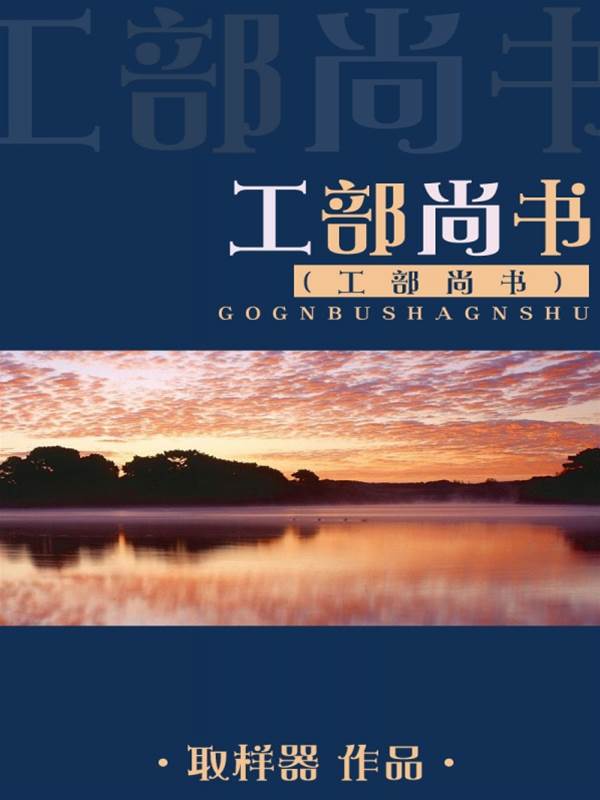《楊門忠烈傳》第12章
「不要回來嗎?」張老憨答道,「沿路做記號。」
「好!這有。豬尿脬呢?要二十個,就要殺二十頭豬,我們這個村子里一共怕也沒有二十頭豬。」
「豬尿脬是裝豬用的。」張老憨倒也通人,「既然沒有那麼多,就改用竹筒好了,不過帶著不方便,只好弟兄們麻煩些了。」
「弟兄們麻煩不要。」孫炎星說,「只要不麻煩地方就好。」
就在這樣和衷共濟的態度之下,十樣必需品,都已籌妥來源,沒有原,就用代用的東西。當天辦齊,都送到了土地廟。
「這九曲十分難走,難有三樣。第一是歧路極多,一進去就繞不出來,所以要我打頭。」
「那自然,」孫炎星說,「請你領路,我跟著走。」
「不!」張老憨說,「請你尾。雖說尾,實在也就是跟著我走。我們一共五十二個人,拴在一條繩子上。」
這時張老憨才細細說明九曲中的艱險困難。顧名思義,中為迴腸九曲,自然不在話下;歧途紛繁,也早已說過;此外還有幾樣致命的危機。
「第一樣,到都是坑坑,有的三五尺深,有的是無底,一跌下去就沒救。」張老憨說,「我要用條百丈長繩,拿大家拴在一起,就是這個道理,如果有誰掉到坑裡,前後的人,要合力拿他拉了上來。」
「這法子好!」不過孫炎星也有疑問,「只是這一來,豈不是牽一髮而全?一個出了病,連累全?」
「問得好!」張老憨深深點頭,「所以,這樣子連著一起走,有個走法。一百丈繩子拴五十個人,前後各有一丈的寬裕,如果大家腳步勻稱,前後相隔一丈,那就還有一丈的繩子垂著,本就覺不到什麼。倘或前面忽然繃了,可知有人出了病;後面覺得繃了,也是一樣。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Advertisement
「自然是先立定了再說。」
「不錯,一點不錯。要儘力站定,只牽累到自己為止,教後面或者前面的人,不影響才是正辦。」張老憨說,「等站定了,再幫前面或者後面的忙,將人救出來。說到這裡,我可有句話,必得請孫將軍關照弟兄照辦。」
「是的,你請說。」
「若是救不出來,只好犧牲。前後的人,拿繩子割斷,去掉了那個人再拿繩子接上,照舊往前走。」
「壯士斷腕,原該如此。」孫炎星問,「這鈴鐺可是傳通信息用的?」
「自然。」張老憨很清楚地規定鈴號,「小鈴鐺結在繩子上,搖兩下,關照當心;搖三下,立定;搖一陣,那就不但立定,還要當心。大鈴鐺專為出了大子,報警之用,要選派妥當人執掌。」
「好的,這個我會分派。請說第二樣。」
「第二樣,里暗,毒蟲、大蛇極多,若是被毒蟲咬了,自己敷藥,不準吵,擾大家。見了蛇,不必理它。」
「如果被毒蛇咬了呢?」
「那——」張老憨答道,「剛才不是說過了嗎?」
孫炎星想一想才明白,正就是自己所說的「壯士斷腕」那句話,唯有犧牲。自己平日發令的時候多,驅遣士卒從事出生死的任務,只有關切,並無恐懼,而此時聽得張老憨這樣說法,卻不由得悚然心驚,暗中自語:可要小心!自己被毒蛇咬了,也應該早自為計,不宜停頓,妨礙整隊的使命。
不過,張老憨只著重在如何帶領大隊通過艱險神、充滿著不測危機的九曲,而孫炎星則還要考察中的況,提出報告。今後是不是能夠開闢出一條專用的捷徑,有效扼守強敵進窺的咽之路,全看自己所提出的報告是不是詳細確實而定。
Advertisement
這是軍事上的絕大機,不便告訴張老憨,甚至也不宜明示於部下,只有靠他自己相機進行。
打定了主意,且先不言,繼續請張老憨提示必得當心的行。
「將軍,」張老憨卻只對孫炎星一個人說話了,「讓弟兄們暫時歇一歇。」
孫炎星明白,這是單獨有話要談。看天已近黃昏,這天反正不會出發,當即傳令,飽餐歇息,如果在規定就寢時分以前,別無命令,大家按平常作息時間行事。
這時馬鄉約已單獨備了兩壇汾酒,殺了一頭豬,抬來勞軍。孫炎星也是肯與士兵同甘苦的人,吩咐白學登,按人均勻分派——當然,要多提一份,整辦好了,款待張老憨與馬鄉約。
就趁這飯前片刻,他約了張老憨在廟后一個小山岡,閑步談,張老憨首先問起出發的日期。
「自然越快越好。」孫炎星答道,「倘或你認為都預備妥當了,我們明天一早就可以走。噢,」說到這裡,他想起最要的一句話忘了問,「老張,穿過九曲要多時候?」
「如果順順利利,要一整天。」
孫炎星心想,照這樣算,拂曉出發,暮抵達,休息半夜,布置疑兵,等天一亮,正好讓契丹兵發覺驚。時機正好,就點點頭不作聲了。
「不過,」張老憨有些憂形於,「只怕不會順利。」
孫炎星大驚:「怎麼呢?」
張老憨不即回答,仰首天邊,若有所思。好久,才低下頭來看著孫炎星,眼中是十分懇摯的神,看不出一戇憨之態。
「將軍,不瞞你說,我這個人戇得很,心裡總是在想,明明一條捷徑,偏偏沒有人敢走,其中總有使人怕到願繞好大的圈子而不敢冒險的難在。我十年前就立志要打通這條路,一個人走過八次,只有兩次走通,的確是不容易過得去。老實說,我現在自己都有些害怕。」
Advertisement
這豈不糟糕!孫炎星著急地說:「老張,老張,你不能先害怕!你一怕,教我們怎麼辦?」
「現在,當然害怕也要去。我的意思是,話要先說明白,請你自己斟酌,如果弟兄膽子不夠大的,最好不要去。」
「是的。」孫炎星聽他這一說,略略放了些心,不過他的警告,大意不得,一定要先弄清楚真相,「到底怎麼可怕?容易迷路、有陷阱、毒蛇毒蟲,還有呢?」
這是一種心靈的,張老憨實在無法形容。九曲中,暗、、寂寞,其中,不由自主地會興起一種被埋墳墓中的恐怖,會嚇得人發瘋。張老憨記得他第一次時,不自地出聲狂喊,震得滿的迴音激,竟至震落壁上的一塊大石頭,當頭砸下,幾乎喪生。
回憶到此,比較有實在的東西好說了。「將軍,」他說,「九曲里的可怕,不是經過的人不知道,知道了也形容不出。打個比方,小孩子做了噩夢,驚醒過來,一片漆黑,娘娘不應,喊爹爹無聲,那種味道,就稍微有點像了。」
「噢!」孫炎星不敢多想,想起來會自己嚇自己。
「再有一樣,裡面不能大聲說話,更加不可以狂喊,不然,聲音在九曲里鑽來鑽去鑽不出,會出大子。」
聲音會鑽來鑽去,這話似乎新鮮,但細想一想,卻知並非瞎說,如果在峰巒環抱之發聲長嘯,不也有山鳴谷應的回聲麼。
然而會出子,倒是不曾聽說過的,行船到水深不測的險,船家會預先關照乘客噤聲,怕驚起蛟龍,興風作浪。莫非九曲中,也有潛伏著的妖魔鬼怪,不能驚?
「不是的。」張老憨回答他的疑問,「怕將頂上的石頭震落下來,如果只是打死個把人,倒還是小事,就怕正好塞住了出路,那時候地方狹窄,迴旋不轉,不好著力移它開去。軍爺,你想想看!」
Advertisement
不用想也知道,大家都活埋在裡面。孫炎星有些不寒而慄,覺得整個計劃要改過了,至去人不宜那麼多。
「頂妥當的辦法是,先去探一探路,安下標誌,該怎麼當心,出了危險,該怎麼樣應付,都弄得清清楚楚,就好得多了。只是辰來不及,沒奈何!」
孫炎星不即回答。他越來越覺得此行關係重大,可能會得到很高的就,但也可能落得一個極悲慘的結果。行止計劃自然要修改,怎樣修改,眼前還無法知道,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絕不能切從事。此行的功還是失敗,都決定於考慮得是否周詳。
「我們先喝酒去吧!」孫炎星已當張老憨是一個極的好朋友,因而略了形跡,拍著他的肩,改了稱呼,「老憨,你一點不憨、不戇嘛!」
張老憨笑了,是極憨厚的笑容。他也知道這件事還要從長計議,而孫炎星此時正在用心思盤算,所以不願再多說什麼,免得擾了他的思路。
回到廟裡,「伙頭軍」已經整制好了酒肴——黃沙碗里盛著微碧的汾酒,一瓦罐的大雜燴,僅此而已。
主客四人,席地而坐。這樣的場面,自然用不著客氣,大碗喝酒,大塊吃。白學登和馬鄉約都是健談,張老憨的談鋒也不弱,只有孫炎星不大說話。
這一頓飯吃完,孫炎星已經盤算停當。兵在不在多,冒險犯難之事,更是如此。他認為此行有十個人就夠了,人多了呼應不靈,反而累贅。
於是連夜挑人。第一大膽,第二力壯,第三機警。這三樣以外,還有要的一點:任勞任怨,不會急功,更不喜表功的。
這就難了,挑來挑去只得七個,加上孫炎星和張老憨,十個都湊不滿。
「也夠了!」孫炎星說,「我想通了。所謂疑兵,原有兩種:一種是要顯得人多,看起來彷彿藏著千軍萬馬似的;一種是要顯得出奇,不應有敵人的地方,居然出現了敵人,豈不嚇了一大跳?我們現在要設的疑兵是后一種,只要有幾面大宋的旗幟就行了。」
其實旗子的分量不重,不帶旗桿,每人至可帶十面,九個人有九十面也很夠了。此外,孫炎星規定了每一個人的特定任務,主要的是記住沿路的況,其中有兩人的任務最枯燥,但也最要,是記住步數,用死法子測量路程。
任務分配講解完畢,已是三更時分,孫炎星關照:「放開心思好好睡一覺,能睡多久睡多久,養足了神,從明天黃昏開始,盡一夜的工夫辦事。」
事實上睡到中午都已睡足了,這就無須空耗辰,飽餐一頓,扎束停當,檢點無缺,由張老憨帶路山。
九曲口,巨石矗立,藤蘿布,如果不是來過的人,絕難發現。張老憨搖手示意大家停住腳步,仔細看了看西下的夕,對孫炎星說道:「時間倒是正好。此刻進,半夜裡可以走完一半。那裡有個,直山頂。今天是十四,月亮也圓了,半夜月直照下來,我們就在那裡歇腳再走。」
他說一句,孫炎星應一聲,一切都聽張老憨指揮。用十來丈長的麻繩,將九個人從腰際系住,各人前掛一串鈴鐺,安然前行時鈴並不響;如果傾跌在地,鈴鐺撞發聲,所有的人就都須停下來,共相扶持。
這些應該遵守的約定,由孫炎星重新提示了一遍,然後點起風燈,由張老憨領頭,孫炎星殿後,魚貫。「老二」——為了招呼方便,九個人如九弟兄,張老憨是老大,孫炎星了老幺,次序第幾,便是老幾。老二與老三的任務是報數,一個報單,一個報雙,遞相傳呼,報到一百,拿塊小石子丟另外一個口袋;報到一千,老三和老四的差使來了,用提著的一桶石灰水,在崖壁上記上數字。他們兩人還有一個任務:每遇轉彎之,加上記號。
走到一千步外,離口已遠,漸漸聞到霉爛氣息。這是張老憨預先關照過的,遇到這種形,便須服藥。葯是行軍常備的「避瘟丹」,各人從囊中取了出來,拿下一塊,放口中嚼化了,乾咽下肚。
忽然間,鈴聲大響。這是張老憨在搖大鈴,聞聲停步,聽他喊道:「老三、老四!」
這兩個人初次聽得有特殊任務派,未免張,答應一聲,扯開腰間繩子上的活結,提著石灰水急急上前。
「當心,當心!當心頭上。」
張老憨急急警告,已來不及,老三一頭撞在下垂的石上,頓時鼓起好大一個包,眼中金星,兩耳雷鳴,幾乎支持不住。
「怎麼樣?」張老憨問道,「不要吧?」
老三住了答道:「不要。」
不要就辦事。張老憨喊他們,正因路中突然垂下一長條石,倘不當心,就會頭,所以要用石灰水塗白,好讓大家注意。
這時孫炎星亦已解開繩子,趕來探視究竟。發現這條石,實在礙路,便主張乾脆將它設法弄斷。
「那得費好大的工夫,今天是來不及了。」張老憨說,「還是趕路要。」
孫炎星有把削鐵如泥、形似匕首的短劍,去除這條石,並非難事,只需將斷之,用劍尖在周圍鏤刻一條深槽,然後使勁一推,自能斷落。但雖不甚難,卻非舉手之勞,為了顧慮一費時間,二耗氣力,接了張老憨的勸告,只用石灰水在石尖及前後道路上抹白,作為警告小心的記號,等回程再作理。
就這樣一路小心前進,不但由於彼此默契甚深,能夠履險如夷,而且也因為心靈相應,互信互倚,一個人等於長了九個人的膽子。所以儘管中慘慘、綠火磷磷,時而有梟鳥發笑樣的怪聲,時而有大蛇在暗中窺伺的紅眼,在常人一步一驚,可能會嚇得癱瘓在地的大恐怖境界,他們九個人卻都能沉著應付,不至於驚惶失措。
猜你喜歡
-
連載60 章

從廢太子到帝國暴君
穿越成廢太子?開局就是絕色太子妃寢室!美人在側,皇位在前!江山,權勢,應有盡有!他從廢物太子,一路逆襲成為帝國暴君!文武百官:“必須讓他做皇帝!誰不服我等跟誰急!”皇帝:“皇位交給他,我放心了。”天下第一:“我跟他斗了三百回合,才知道他只出了一成功力。”將軍:“在他面前,我的軍事才能就是個笑話!”敵國皇帝:“讓此子做皇帝的話,整個天下沒人能擋住他!”敵國女皇:“若是他愿意娶我,我就把我的整個王國當嫁妝!”
11.8萬字8 2298 -
連載866 章

北宋穿越指南
北宋穿越指南無彈窗是王梓鈞的小說作品,情節緊湊,人物鮮明,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北宋穿越指南無彈窗全文閱讀最新章節吧就在筆趣閣.
234.7萬字8 1883 -
連載576 章

大明暴君,我為大明續運三百年
【權謀】+【熱血】+【爭霸】+【殺伐】+【無系統】 “朱由檢,安心的去吧,你的一切將由我葉軒來繼承, 從現在起,我就是大明的第十六位皇帝——崇禎,朕在這裡立下誓言: 你朱由檢殺不了的人,我崇禎來殺, 你朱由檢做不到的事情,我崇禎來做, 李自成、張獻忠造反?那也要看朕給不給他們機會! 建奴屠我中原族人?那朕便屠了建奴,亡其種,滅其族! 八大晉商私通建奴,為其耳目?那朕便抄家滅族! 文人無知、無能、無恥,叛國投敵
105.1萬字8 15547 -
完結379 章

開局成反賊,獎勵燕云十八騎
【反賊+攻略+打造王朝】一朝穿越,饑寒交迫。什麼?朝廷宦官當道,百姓民不聊生?什麼?邊境西夏入侵,軍隊不戰而降?什麼?官吏貪污成性,屢布苛捐雜稅?這樣的大黎朝,要之何用?我江眠,今天就造反了!于是,一個平民百姓,身懷反賊系統,崛起于微末!【殺縣令,獎勵燕云十八騎】【殺知府,獎勵玄甲軍】【占云州,獎勵吳起】......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從最底層一步一步走到最高,成就九五之尊,橫掃天下!
70萬字8 6824 -
完結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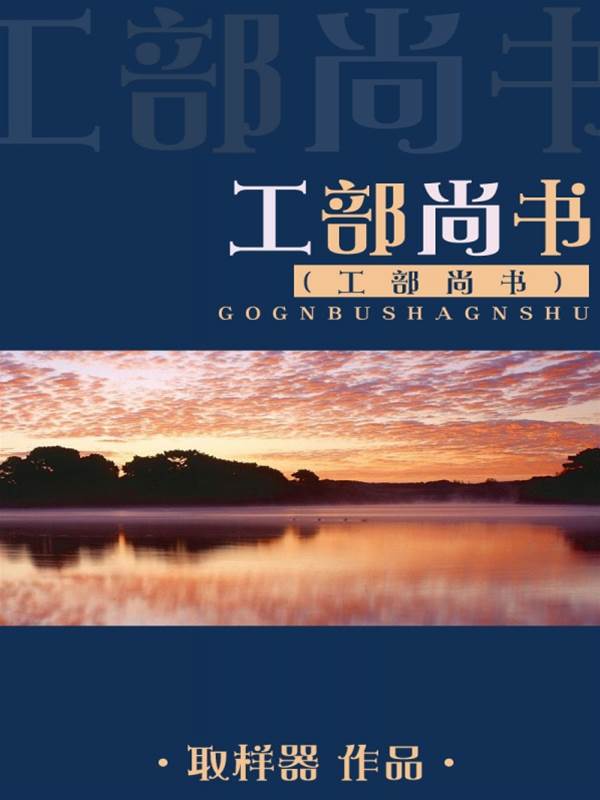
工部尚書
鋤禾日當午, 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 粒粒皆辛苦。
14.7萬字8 32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