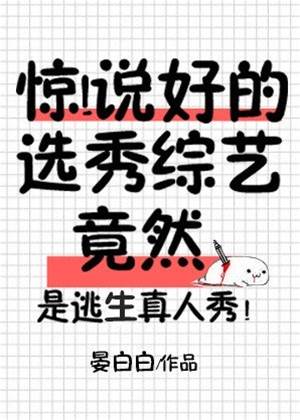《一劍霜寒》 第17章
第十七章 回廊異響
雲倚風目狐疑:“什麼”
季燕然隨手從懷中扯出來一隻打瞌睡的小團--方才在離開西暖閣時,順手牽了只貂。
雲倚風果然笑出聲, 從他手裡抱過來, 一把那嘟嘟的肚皮, 喜歡得很。
金煥站著聽了半天, 兩人一直在低聲說笑, 沒聊到任何有關殺手的事,反而是自己被蠍尾花毒弄得再度有些頭暈, 只好黑回到床上, 昏沉沉又睡了過去。
屋外積雪鬆, 雪貂先是傻顛顛滾在裡頭, 將自己裹了滿冰碴子, 後又連爬帶躥鑽進雲倚風懷中,著腦袋撒歡。季燕然碎一塊點心, 將餡兒喂過去:“方才去西暖閣時, 地蜈蚣說他前幾日在縹緲峰下,曾見過數十隻純白雪貂。”
“數十隻”雲倚風拍了拍手裡的小東西,疑道, “雖說不算珍, 卻也不是隨隨便便就能找到的,況且雪貂天喜歡獨居,數十隻聚在一起……有人在養著它們”
“是啊。”季燕然用拇指蹭那茸茸的腦袋,漫不經心答一句, “金煥不就明晃晃地在養”
雲倚風微微皺眉。
“沒想明白”季燕然一笑,“上回還是你先發現的, 金煥邊的雪貂經常會換,可這賞雪閣裡也沒見過雪貂群抱窩,那其餘的去了哪裡”
“在山下。”雲倚風順著他的意思,猜測:“你是說……”
“這裡沒有能容納年人的道,可未必就沒有它能走的路。”季燕然把最後一點糖餡喂過去,“就如當初所言,岳名威定然會在山上安一個線。”
雲倚風道“嗯。”
雪貂聰明靈活,馴化之後甚至能去集市雜耍,往返送信自然不在話下。雲倚風往回廊下看了一眼,金滿林的依舊停在那裡,一隻胳膊掉出白布,被嚴寒天氣凍得青白發紫,慘不忍睹。若金煥當真是嶽名威的眼線,哪怕過往樁樁命案皆與他無關,可現如今連親生父親都離奇喪命,不知他心中又該做何想
Advertisement
“你怎麼看”季燕然問。
“金煥是家中獨子,平日裡備寵,金滿林對他幾乎有求必應。”雲倚風將懷裡的小團子放回雪裡,“我實在想不出有什麼理由,能令他被岳家收買,甚至做出枉顧父親生死這種禽不如之事。”
“想個法子試試便知。”季燕然道,“不過金煥在雙目恢復之前,大概也不會再採取行。”
“這倒不急。”雲倚風道“看他瞳仁的,最遲明早便能康復。”
季燕然意外“你對毒也有研究”
“風雨門做的就是這種生意。”雲倚風揣起手,看著雪貂一路跑遠,“什麼蒜皮的事,只要有人肯出銀子,都能打聽。”
季燕然點點頭,覺得人生在世,倘若能有這麼一位事事皆知朋友,也是一件頗為有趣的事。
當然,前提得先找到靈芝,否則不被全國追殺已經算是佔便宜。
畢竟此人記起仇來,貌似也不比自己差。
雲倚風無辜被腹誹,一口氣連打了三四個噴嚏。
季燕然“……”
季燕然虛偽叮囑“多喝熱水。”
晚些時候,眾人又聚在飯廳,一盆火鍋吃得索然無味,玉嬸見雲倚風臉不好,特意給他蒸了一小碗銀魚蛋羹,叮囑要多吃兩口。
“雲門主。”柳纖纖仔細看他,“你是不是染了風寒,怎麼病怏怏的。”
“無妨。”雲倚風咳嗽,“老病,睡一夜明天就會沒事。”
季燕然放下筷子,掌心門路上他的額頭,微微發燙。
柳纖纖依舊擔憂“該不會又要像上回一樣,毒發了吧?”可還記得那滿被子的,嚇人得很。
“先吃飯。”季燕然替他盛了碗熱湯,目在桌上環視一圈,手一指,“你,今晚來觀月閣住著,照看金兄。”
Advertisement
“我?”地蜈蚣先是一愣,後又大喜,趕忙答應下來。他正同暮雪相得頭疼胃疼全疼,總覺得對方下一刻便會拔出隕劍,將自己砍個七零八落,實在瘮得慌,現如今終於能搬出西暖閣,無異于天上掉金餑餑,焉有不肯之禮。過了陣子,又得寸進尺嘿嘿笑道:“不如往後就由我一直伺候金兄吧,或者大家搬到一起住也,彼此多個照應。”
季燕然還沒開口,金煥已經在旁推辭:“雲門主說這蠍尾花的毒明後天就能解,我也不是滴滴的大小姐,哪裡需要人一直服侍。”
地蜈蚣聞言耷拉下臉,雙目向雲倚風,指他能幫自己說兩句話。卻被對方額上的細汗珠驚了一驚,江湖中只傳風雨門門主中奇毒,可也沒說那毒究竟是什麼,不過看這來勢洶洶的架勢,似乎嚴重
“諸位慢用。”季燕然扶著雲倚風站起來,又對地蜈蚣道,“金兄--”
“放心”地蜈蚣舉手發誓,“保證寸步不離。”
邊的人已經快被冷汗浸,季燕然也無暇再細細吩咐,總歸在山上這些人裡,地蜈蚣算是最清白無辜的一個,武功不低詭計多端,盯著金煥一夜應當不問題。不過即便如此,他還是沒有回飄飄閣,而是將雲倚風帶往了觀月閣的臥房。
小廚房裡又響起“呼哧呼哧”風箱聲。
雲倚風勉強靠在床頭,聽全骨骼細細作響,連耳都鼓脹出清晰的痛來,細瘦手指擰住床柱,指甲嵌進木屑也渾然不覺,流了半掌心。季燕然進門之後看得皺眉,隨手扯過一邊枕塞進他懷中,厲聲命令:“抱好!”
世界原本只有混沌煎熬,突然被嘹亮吼了一嗓子,如一把雷霆劍穿重重霧霾,雲倚風驚得渾一,也來不及多做考慮,立刻鬆開雙手,一臉茫然地將那枕頭抱了起來。
Advertisement
季燕然頗為滿意“乖。”
療傷這種事,同生孩子是一個道理,也是一生二。有了上一回的經驗,季燕然已經大致清了他毒發時的脈絡走向,所以照舊讓人躺在自己懷裡,單手按住那孱弱心口,將真氣緩緩渡過去。
氣息漸平,刺骨之寒也散了些許。
雲倚風費力地睜開眼睛,像是正在辨認眼前人。
季燕然原想讓他好好睡,後來轉念一想,靈芝。
那就多看兩眼吧,也,最好能多看一百一千眼,牢牢記住自己此時此刻的心模樣,將來正好還幾分人。
於是他鎖眉頭,雙眼帶愁,儘量讓自己顯得憂心忡忡。
雲倚風微,呼吸急促,半天方才說出一個字:“疼。”
“疼就對了。”季燕然大手輕,溫哄他,“你放鬆,放鬆就不疼了。”
雲倚風聽得模糊,想說話又實在沒力氣,看了他半天,最後索煩躁地閉上眼睛。
你住了我的頭髮。
疼!
蕭王殿下渾然不覺,還在想,這是什麼爛脾氣。
又不是我讓你疼的。
兇瞪我作甚。
嘖。
有人從院外走了進來。
地蜈蚣將金煥扶回臥房,小心翼翼賠笑道:“金俠可要喝茶?”
“不必了。”金煥索著坐下,他雖氣惱這盜賊弄傷了自己雙眼,卻也知道目前況特殊,出不得太多子,便只推說想早些上床歇著。地蜈蚣自在江湖中爬滾打,自是能屈能,毫不在乎對方的冷漠差遣,燒水端盆做得比老媽子更勤快,伺候金煥上床之後,又溜去隔壁門看了一眼,就見層層床帳下,季燕然還在給雲倚風療傷,屋有一濃的藥味。
“世道不太平啊。”地蜈蚣搖頭晃腦歎一句,自己在廳裡尋了個暖和地方,也打起盹來。
Advertisement
黑雲吞沒了最後一抹日,原本就黯淡的天,終於徹底陷漆黑。
夜寒涼,寂靜蕭瑟。
地蜈蚣守著火盆,昏沉沉一覺睡到半夜,被烤得口乾舌燥熱醒過來,原想去廚房找些水喝,那茶壺拎著卻沉甸甸的,不知裡頭堵了什麼東西,好不容易才倒出半杯水來。心尖上正得火急火燎,也顧不得細看,一腦全部倒口中,哪裡又能嘗出半分茶味,反倒鹹濃稠,一子鐵銹濃腥。
“咳咳!呸!”地蜈蚣被嗆得幾作嘔,拿到燈下細細一看,就見杯中腥紅深褐,竟掛滿半乾漿,頓時駭得連連後退,一跤踉蹌跌空,大汗淋漓自夢裡驚醒。
廳中一切如故,沒有漿,更沒有厲鬼。
地蜈蚣心臟“砰砰”狂跳,在夜裡著緩了片刻,總算分辨出來自己何地。可夢境雖退,耳邊卻又傳來怪音,嘎嘎、吱吱呀呀……好像木架子在搖晃,其中還混了些含糊不清的說話聲。
噩夢殘影未消,再一想回廊下金滿林的,地蜈蚣後背發麻,挪到窗邊,將那厚重布簾掀開一個小,想看看究竟出了什麼事。
此時月盤正亮,明晃晃照在雪地上,發出慘白的。而金煥只穿了一裡,瘋癲顛中邪般赤腳站著,眼神空木然,裡還在喃喃念叨著什麼,雙手更是按住金滿林的斷頭,推了一下又一下,像是要將那玩意再生生安回去。
三更半夜淒風寒月,是站在院中都會覺得後有鬼,更何況還要親眼看這恐怖場景,當金煥將那腦袋半捧起來時,饒是鑽遍墓的地蜈蚣,也被嚇得夠嗆,他哆哆嗦嗦牆出門,頭也不回地沖進了隔壁房間。
黑暗中,雲倚風一把握住他的胳膊,做了個噤聲的手勢。
地蜈蚣驚魂未定,死死攥住那白袖,宛若撈到救命稻草。
而在屋子外頭,金煥的詭行還在繼續,雖說終於不再那搖搖墜的斷頭顱,卻又開始索著在金滿林上按,直將那首推得快要跌落在地,方才僵麻木停下手。地蜈蚣看得實在晦氣,心說這賞雪閣也真是絕,謀暗殺失蹤命案一應俱全,現在還多了個中邪,自己不知是倒了幾輩子的黴,竟會挑這種時候上山。
細聲細氣哭了一陣之後,金煥雙眼一翻,直向院中倒去,“咚”一下砸了個滿地雪飛。
“這個我懂!”地蜈蚣趕道,“是附的邪靈走了,得趕把他弄回房。”
季燕然將人從雪地裡拎起來,探手試了試鼻息。
雲倚風問:“人還活著嗎?”
“有氣。”季燕然道,“只是暫時昏了過去。”
金煥牙關咬,臉慘白,躺在床上一不。地蜈蚣後怕不已,哭喪著臉對雲倚風解釋:“我就稍微打了個盹,沒想到他就自己中邪跑了出去,深更半夜的,誰能想到會出這種事?”
雲倚風問:“你覺得這是中邪?”
“啊,不然呢?”地蜈蚣低聲音,“好好的覺睡到一半,突然就去回廊親爹的首,又推又摟不算,裡還要念念叨叨,這不是中邪是什麼?”
雲倚風看向季燕然,先前在兩人療傷時,聽到隔壁有窸窣響,出門便見金煥正彎腰凝神,細細著金滿林的殘軀,慘澹月下,他一頭枯發被風裹得飛如草,煞白臉面上鑲一對黑的眼窩子,畫面確實森。難怪地蜈蚣會懷疑中邪--除此之外,也實在想不出其它理由。
季燕然道:“這裡有我看著,你先回去睡會兒吧。”
地蜈蚣非常,趕忙道:“我不困,我不困。”
季燕然又試了試雲倚風的額頭溫度,替他將大氅拉高了些,繼續道:“我的被中有暖玉,你氣息未穩,需好好歇著。”
地蜈蚣:“……”
哦,沒跟我說。
雲倚風笑笑:“多謝。”
季燕然將他送回隔壁,回屋就見金煥已經醒轉,正在索著想下床。
猜你喜歡
-
完結58 章

離婚
關鍵字:弱受,生子,狗血,惡俗,古早味,一時爽,不換攻,HE。 一個不那麼渣看起來卻很氣人的攻和一個弱弱的嬌妻小美人受 發揚傳統美德,看文先看文案,雷點都在上面。 一時興起寫的,想到哪兒寫到哪兒,什麼都不保證。 原文案: 結婚快四年,Alpha收到了小嬌妻連續半個月的離婚協議書。
7.7萬字8 9015 -
完結2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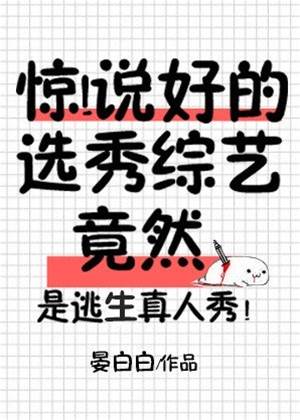
驚!說好的選秀綜藝竟然
某娛樂公司練習生巫瑾,長了一張絕世美人臉,就算坐著不動都能C位出道。 在報名某選秀綜藝後,閃亮的星途正在向他招手—— 巫瑾:等等,這節目怎麼跟說好的不一樣?不是蹦蹦跳跳唱唱歌嗎?為什麼要送我去荒郊野外…… 節目PD:百年難得一遇的顏值型選手啊,節目組的收視率就靠你拯救了! 巫瑾:……我好像走錯節目了。等等,這不是偶像選秀,這是搏殺逃生真人秀啊啊啊! 十個月後,被扔進節目組的小可愛—— 變成了人間兇器。 副本升級流,輕微娛樂圈,秒天秒地攻 X 小可愛進化秒天秒地受,主受。
89.5萬字8 8616 -
完結149 章

美貌廢物被迫登基後
《美貌廢物被迫登基後》作者:謝滄浪【完結】 文案 李氏王朝末年,朝局風雲詭譎。 新任平南王雲殷,狠戾果決,與當朝太子相交甚篤。 一朝宮變,天子崩、太子被毒殺於宮中。雲殷帶兵平叛,親手將弒父殺弟的大皇子斬殺於階前。 自此,帝位空懸。 就在世人皆猜測,這位雷霆手段的異姓王將要擁兵自立之時,雲殷入了宮。
21.3萬字8 53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