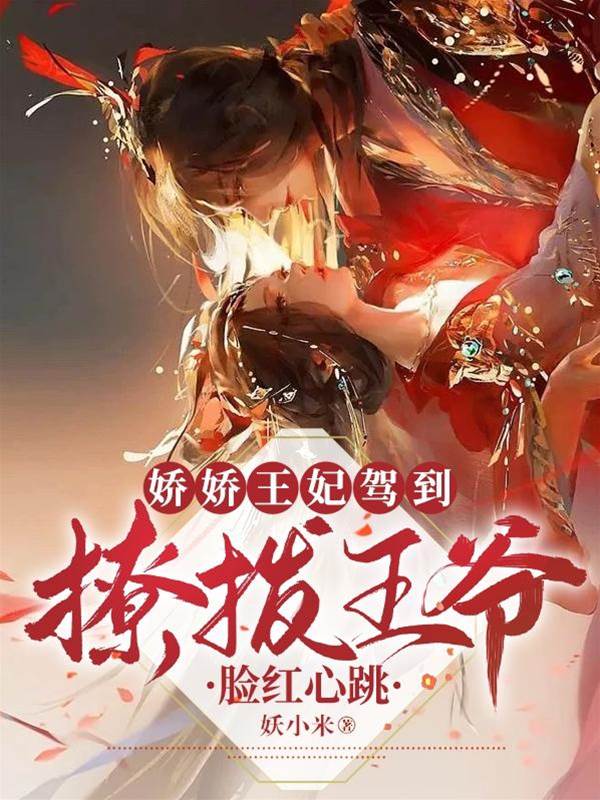《古早文女配改拿爽文劇本》 第32章 第32章
皇帝直視著永安, 語帶深意地勸道:“阿姐,別鬧了。靜樂來你府上做客,你這個做主人也太慢怠了。”
皇帝語氣有些重, 額角也有青筋暴起。
永安臉頰發白, 翕了翕,終究沒有再說什麼。
在看來, 該做得事應該已經做了,都這會兒了, 哪怕盛兮的骨頭再,也該聽話了。
晴閣里頭的兩個嬤嬤都是從宮里帶出來的老人, 是當年母后用慣的, 最是會調/教人, 宮里頭那些不聽話的宮嬪妃,一旦落到們的手里,保管讓往東就不敢往西,讓跪著就不敢趴著。
盛兮這會兒想必也知道厲害了。
有丫鬟小心翼翼遞上帕子, 拿過了一把臉上的酒漬,勉強出一點笑容,干地說道:“靜樂, 本宮只是與盛大姑娘開了個小玩笑,我帶你去尋就是。”也算是低了頭。
永寧的聲音剛落, 靜樂還沒回應, 眼角的余突然瞥到了一個遠遠走來的纖纖影, 過茂的樹影灑在的上, 仿佛為鍍上了一層微,在的后還跟著一個手拿竹籃的丫鬟。
永安怔了怔,忍氣吞聲地說道:“靜樂, 盛大姑娘不是回來了嗎,犯得著你這般氣,失了分寸。”
靜樂沉默了下來。
待一主一仆走近,靜樂又注意到,昔歸手上的竹籃子里裝著的全都是綻放的杏花,開得一朵比一朵艷。
其他人倒也罷了,但方才在花榭的那幾個婦人是親眼見過為了簪不簪杏花而起的軒然大波,如今這又是什麼況?這一波三折的熱鬧,讓們快要得心悸了,以后出門還是得看看黃歷。
永安有些詫異,然后就見盛兮帶著丫鬟走到了自己前面,一副恭敬的樣子。
Advertisement
抿的角略略放松了一些,審視地問道:“盛大姑娘。你這是去哪兒了,靜樂等你都等急了。”
盛兮目在狼狽不堪的面上定了一下,就算盛兮再聰明,也想象不出來,才這麼一會兒工夫,永安怎麼把自己折騰了這樣。
盛兮眼簾微垂,福道:“殿下,臣去摘了些花。”示意著讓昔歸把竹籃給,給永安看了。
籃子里頭的確都是杏花,沒有別的花樣。
是踩壞了一籃子杏花,又采了一籃子來跟自己賠罪?
這麼想著,永安眼底的抑郁淡去了一些。
看來,兩個嬤嬤的手還沒有生。所以啊,對付盛兮這種不聽話的野丫頭,就該讓人去好好教教什麼作尊卑,免得永遠認不清分寸。
永安的心里終于舒坦了。
這會兒其實不得想看盛兮和靜樂這對未來婆媳相殘,但是,皇帝顯然是惱了,只能安自己說,盛兮這枚棋子是要留著日后用來通風報信,這次就饒過了們。
“既然無事,你就回靜樂那兒去吧,免得靜樂以為是本宮把你藏了起來。”冷笑著,又瞥了一眼靜樂道,“靜樂啊,以后做凡事都得想清楚了,別總是燥燥的。”
靜樂瞇了瞇眼,心里頭相信盛兮這丫頭,怕的唯有不知道永安是不是對小丫頭做了什麼。
“……”
靜樂正要讓過來,就見盛兮竟又朝著永安走了一步,擺搖曳間出了繡鞋上的兩顆珠珍。
輕啟朱,溫和但又無比清晰地說道:“長公主殿下,臣方才路過一棵杏樹,覺得花開得正好,就折了些來,長公主您可要用來簪花?”
永安:“……”
心里頭不“咯噔”了一下,不再度審視起盛兮,這一看之下,就覺杏目清澈,不含半點惶惶,除了額頭略有薄汗外,神采奕奕。
Advertisement
照理說,盛兮不該如此的,難道……
一個念頭剛起,還等不及細想,就聽盛兮接著道:“殿下,臣聽聞,當年在北疆,老王爺過世后,所有的軍民全都自發簪上杏花,以示不忘國恥,不屈北燕,軍民一心,才有了其后的堅守江越城七日和燕山關大捷。”
盛兮的笑容更盛,不可方:“長公主殿下,方才您也是為了……”說到這里,刻意停頓了下來。
永安的目略漸驚駭:“夠……”
盛兮恰到好地打斷了,把話說完:“效仿北疆,為戰死的鎮北王和北疆眾將士戴孝,以示不忘當年之恥吧。”
“哎,倒是臣誤會了您的好意了。所以,臣就又去摘了一籃子,請長公主……簪花。”
皇帝先前并不知道永安干過什麼,但如今他瞬間想明白了其中因果,臉大變,著扇柄的指節微微泛白。
永安心虛地避開皇帝的目。
昔歸在心里暗自為盛兮好,過來的這一路上,昔歸無數次忍不住去猜特意去摘了這一籃子杏花的意圖,萬萬沒有想到,姑娘竟然直接就拿杏花向永安長公主起板來了。
這簡直太太太爽了!
昔歸低眉順目地站著,眸中異采連連。
比任何人都明白,這是姑娘對永安長公主的回擊,又快又狠,而且完全不似長公主的肖小手段,是這樣的明正大,冠冕堂皇。
永安的臉白了白,終于可以確認,盛兮沒有去晴閣!不然,在嬤嬤的百般手段下,絕不可能還會囂張如斯!
這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
永安含怨地看了嬤嬤一眼,眼神里是指責沒把這件事辦好!不但沒能把人領過去,而且出了岔子居然也不跟自己稟報。
Advertisement
虧還一味的以為盛兮已經乖覺了,這簡直像是往的臉上又狠狠地扇了一掌。
這輩子,都沒有像今天這般丟臉過。
“殿下。”盛兮把竹籃又往面前送了送,笑得天真無邪,但里說出來的話,卻讓永安心里發寒,“難道是臣理解錯了,您不是這個意思嗎?”
“當時,臣見您讓人拿了一竹籃的杏花來,還以為您是想讓所有人都簪上一朵呢。”偏了偏頭,一臉無辜地說道:“難道您只是想讓靜樂郡主簪嗎?”
這句話,讓永安所有上不了臺面的狠念頭昭然若揭。
盛兮的意思十分的清楚明確,若大家一起簪,那就是為北疆將士和鎮北王服孝,若單單只是讓靜樂郡主簪,那永安就是其心不良,心存故意。
在場的大多數人并不知道花榭種種,但是,鎮北王戰死沙場,尸被北燕人折辱,當作花泥埋在杏樹下的事,他們都是聽聞過的,但凡有的都忍不下這口氣。但是,朝廷和皇帝不是一向都頗為善待鎮北王府嗎?
他們的眼中或驚或疑,更有人出了沉思,又小心翼翼地來回打量皇帝和靜樂的臉。
皇帝用扇柄敲著掌心,默不作聲,眸幽暗。
靜樂在短暫的驚訝過后,眸一亮。
當年,父王的死訊傳到京城,無論是民間還是朝堂,都有聲音說,請皇帝下旨國喪,但是,皇帝只當沒有聽到,輕飄飄就把這樁事給揭過了。
父王為國而死,為民而亡,為了北疆,為了大榮,死無全尸,鎮北王府為大榮守衛疆土百余年,每一代的楚家人有能善終的,大多都是沙場埋骨,馬革裹尸,如今也只剩下了阿辰他們兄弟倆,竟連一個國喪都等不到。
Advertisement
當時,靜樂是不服的,但是兒子還在北疆,又有強敵環側,不能和皇帝翻臉,所以,忍了。
忍了四年。忍到了現在。
的確,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是永安親手遞到鎮北王府手上的機會!
“原來是我誤會了殿下的意思。”靜樂淡淡一笑,嘆聲道,“殿下這般惦記鎮北王府,有意為北疆的將士們服喪,這也是好事。”
主從竹籃里挑出了一朵杏花,盛氣凌人:“長公主殿下,請您簪花吧。”
立場一下子對調了過來,在花榭時是永安著靜樂簪花,而現在,卻是讓靜樂占據了主導。
皇帝的臉越加沉,扇子敲擊的作也變得毫無節奏。
他早知永安對靜樂不滿,這心結由來已久,但到底是同胞姐姐,平日里,不管是挑釁還是打,他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但沒想到,永安居然能任到這種程度。
大榮朝的藩王執掌兵權,在藩地,那些百姓和將士只知有藩王,不知有朝廷,哪個帝王能夠忍得了?對于大榮來說,這簡直就是心腹大患,父皇當年也給過他們機會了,但他們一個個都私心甚重,把持著兵權不肯放手。
世人皆是眼狹隘之輩,他們只看得到藩王的功勞,卻看不到藩王的野心。
要鏟除藩王,也不能留下把柄,讓野史上那些不明真相之人,以為是皇家在卸磨殺驢。
于是,從父皇到自己,好不容易,費盡了心機,才鏟除掉兩個,但是還有鎮北王府這一座大山在。
鎮北王府如今是功臣,楚元辰又剛剛立下了開疆辟土的大功,自己現在對鎮北王府也只能敬著,永安這般行徑,落到別人的眼里,豈不是會徒惹揣測?
到時候,他還怎麼明正大的對鎮北王府下手?!
簡直就是給自己添。
皇帝眼神不善地斜了永安一眼,永安心中發虛,是先帝的嫡,先帝已逝,能靠的就只有這個同胞弟弟了。
永安憤憤然地從靜樂手上接過杏花,簪到了自己的鬢角上,沒有說話,但眼神中的意思,就像在問:這樣總可以了吧!
靜樂主拿過了竹籃,走到皇帝跟前,說道:“也請皇上為北疆將士們簪花。”說到簪花兩個字了的時候,靜樂郡主心里一陣痛快,平靜的外表下,熱沸騰。
皇帝:”……“
他忍了又忍,艱難地點了頭,臉上一副深明大義,語帶沉重地說道:“說得是,此役耗時四年,北疆將士死傷無數,就算現在北燕已降,但逝去英靈也不會回來了。我大榮子民就該牢記國恥,才能永保不失。”
皇帝咬了咬牙,用盡了全力氣才控制住面部的表,從齒里出了聲音:“這是應該的。”
四年前,朝中的武將們也不知道是不是了鎮北王府的攛掇,非要他下旨舉國為楚慎和北疆哀悼。再這樣下去,別說是藩地了,怕是連大榮的百姓們都會被這區區所謂的恩惠所蠱。
當時,他“悲傷過度”,罷朝數日,才算把這件事給了下去,事隔四年,如今卻讓靜樂趁機舊事重提。
而且,靜樂還直接破了他的份。
若是沒有破,哪怕心知肚明,他也能把它作為是私事。但是現在,以他皇帝的份,一旦拿了這朵花,那就意味著,他向鎮北王府服了,意味著他四年前的堅持就是一場天大的笑話。
但他要是拒絕……
永安的荒唐行為就再沒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蓋住了,一旦傳揚出去,世人皆會認為是他的意思,是他讓永安故意折辱鎮北王府。
如今楚元辰正是聲名赫赫之時,若是讓世人都以為他容不下鎮北王府,日后他再提要削藩必會惹來多方揣測。
皇帝的結了,終于抬起手來,從竹籃子里拿起了一朵杏花。這個簡單的作在他做來極其艱難,就好像拿起來不是杏花,而是一已經點燃的炮竹,隨時都會在手中炸開,讓他模糊。
靜樂的邊揚起了一抹快意的笑,再向昭王道:“王爺呢?”
昭王看了看皇帝,見皇帝默不出聲,就也拿了一朵,自己給自己簪上了。
靜樂:“我父王和北疆將士必銘五。”
無論是皇帝,還是靜樂,其實心里都清楚,只要雙方在明面上沒有撕破臉,鎮北王府就還是皇帝的肱之臣,甚至朝中的大部分人都沒有發現兩者已經勢同水火,雙方依然維系著表面的君臣和樂。
猜你喜歡
-
完結1709 章

攝政冷王悄醫妃
特工軍醫穿越為相府嫡女,受父親與庶母迫害,嫁與攝政王,憑著一身的醫術,她在鬥爭中遊刃有餘,誅太子,救梁王,除瘟疫,從一個畏畏縮縮的相府小姐蛻變成可以與他並肩 ...
255.2萬字8.18 63160 -
完結449 章

郡主囂張:誤惹腹黑世子
一場精心謀劃的空難,顧曦穿越成了安平公主府里人人欺賤的癡傻嫡女。親娘早死,渣爹色迷心竅,與妾室母女狼狽為奸,企圖謀奪公主府的一切。前世的顧清惜,以為裝瘋賣傻,隱忍退讓便能茍活,卻仍被姨娘,庶妹奸計毒害。今生,顧曦決心將忍字訣丟一邊!專注斗姨…
120.8萬字8.09 87940 -
完結691 章

公府貴媳
晏長風嫁給病秧子裴二少,是奔著滅他全家去的。后來,她眼睜睜看著這病秧子幫她滅了全家,又一手將她捧成了天下第一皇商。……晏長風的大姐莫名其妙的瘋了,瘋言瘋語地說著一些匪夷所思的事。她說爹爹將死,母親殉情,家產被姨娘霸占,而她們姐妹倆會被趕出家門。她說她未來的世子夫君是個渣,搶奪嫁妝,寵妾殺妻,連親骨肉也不放過。晏長風難以置信,卻也做足了準備。后來證明,爹爹確實身處險境,姨娘確實狼子野心,她為了不讓后面的悲劇發生,代替姐姐嫁入國公府。然后,她嫁給了國公府最不起眼的一個病秧子。當她要大開殺戒時,那病...
110.4萬字8 25343 -
完結10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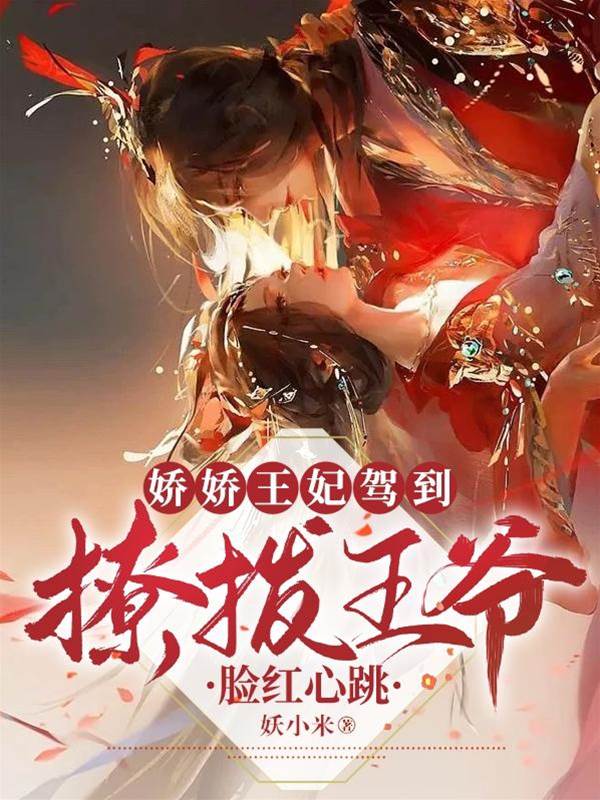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83.7萬字8.18 106609 -
完結236 章
選秀當天被爆孕吐,冤種王爺喜當爹
【女強+萌寶+醫妃+偽綠帽】 一朝穿越,神醫沈木綰穿成丞相府不受寵的四小姐,第一天就被人「吃干抹凈! 被狗咬了一口就罷了,竟然在選妃當場害喜! 還沒進宮就給皇帝戴綠帽?! 沈木綰:完了! 芭比Q了! 瑾北王表示莫慌:我,大冤種。 人在家中坐,綠帽天上來。 御賜綠帽,眾人皆諷。 催眠術,神醫術,沈木綰生了娃打腫他們的碧蓮! 不要臉的瑾北王每天拿著鋪蓋送上門:「媳婦兒,孩子生下來吧,我跟他姓」
42.6萬字7.93 1386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