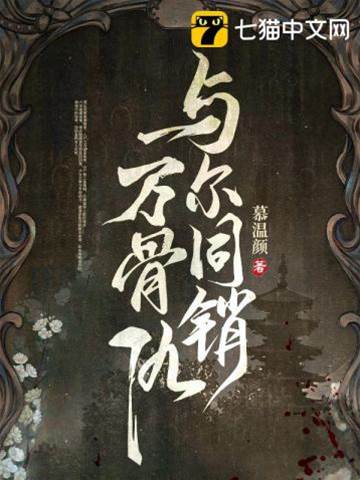《家有賢妻:寡婦鰥夫一堂親》 第七百二十一章 頑固
天明以後,黑人夜襲的消息傳遍了整個京都。
衙門室,檀香裊裊,紗幔重疊,高大人坐在靠椅上,此時的臉仍有些蒼白。
他給自己倒了一杯茶,狠狠飲了一口,眉目間籠罩著一團雲。
「大人現在,信我了吧?」
雕花木桌的另一邊,許漫不經心地把玩著一隻白玉茶杯,微笑著道。
元君羨坐在側,一雙黑眸靜謐地注視著,眸子深現溫。
高大人重重點了一下頭。
他嘆了一口氣,了自己的太道:「你料得果然不錯,這事另有。」
經過昨晚這一出,他已經相信了許的話。
若不是王浩上背負了,黑人怎會連夜前來殺人滅口?
高大人苦笑了一下,對眼前的子已經不敢再有半分輕視之心:「多虧你昨日讓我加強看守,否則,真會被那小賊得逞了去。」
「我只是簡單猜了一下。」許站起,饒有興趣地逗弄著屋的雀兒。
角的笑意看似漫不經心,卻又有竹。
「王浩在同黨的幫助下好不容易逃出監獄,卻隔日後回來自首,而且,還是為了一件與他幾乎無關的案子。」
「他那樣激怒高大人,無非是想要大人趕將他以小麗案犯人的罪名決,然後結案。這種兇狠殘的人,肯這樣做,自然是有理由。除了幫別人掩蓋罪名以外,我想不出別的。」
許從窗外探進的翠竹上折了一片竹葉,將其放進鳥籠里,看著雀兒好奇地啄食葉子,角笑意愈來愈深。
「所以,我才會勸大人暫時將王浩收押,仔細調查,這樣一來,王浩不斷沒有停止小麗案的調查,還引起了我們的懷疑。對他想掩蓋罪名的那個人而言,這是一種拖累。」
Advertisement
轉過,清亮的眸與高大人對視。
「所以,才有了昨夜的殺人滅口。」
高大人臉蒼白,失神地盯著桌上的,他的子居然也有些抖。
「好狠的心......好高明的算計......」
他喃喃著,著許的眼神亦是充滿了敬畏,卻不知後半句到底是在說黑人,還是在為許的智謀而驚嘆了。
「是啊,大人。」許笑瞇瞇地看著他,輕輕擊了擊掌。
「王浩那邊,希大人也能讓我們介調查,以助力大人破解冤案,查出真兇。」
高大人無力地點點頭。
許自然地牽起元君羨的手,拉著他走到門前,後者只是眸微微一閃,便安靜地順從了的舉。
一隻腳已踏出門檻,許回頭,燦爛一笑。
「那麼,我們便告辭了。」
說完,二人的影便消失在門口。
屋頓時安靜,空氣中瀰漫著淡白的檀香煙霧。高大人心神不寧地坐在遠,怔怔地盯了一會兒許元君羨二人曾坐過的位子,忽然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另一邊,出了衙門,目便是明的晨,許了個懶腰,嘆氣道:「一夜沒睡,好累啊。」
轉過頭,瞅了瞅元君羨,忽然用手攬住他的脖子,微微往下拉。
「低下頭,讓我靠靠。」
元君羨忍不住笑了,卻真的微微低下頭,仍由懶洋洋地靠在自己肩膀上。
子眼圈下白皙的果然泛著淺淺的青灰,漆黑的長睫微微合攏,覆住了那雙清亮的眸子。靠的太近,他甚至能聽到輕微的呼吸聲。
「回房去睡吧,我們一起。」
元君羨意味深長地微笑著,看著那白皙的上泛起櫻的紅暈。
「登徒子!」
許睜開眼,氣哼哼地罵了一聲,臉頰卻燒得比平時還要紅。
Advertisement
元君羨眸微深,記起昨晚的事,笑意染上了一層曖昧。
不顧許驚,他忽然大手一抬,竟然將攔腰橫抱了起來。
「走,回房去睡,我們一起。」
正是清晨,男子的嗓音低沉中帶著沙啞,卻更加富有磁,仿若羽般輕輕挑著許的心弦。
「不許輕薄我。」
許臉早已滾燙,將小臉深深埋進他的懷裏。
兩若是長久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外面是好的晨景,然而,此時的衙門牢獄,卻是宛若地獄般的景象
空中不僅泛著發黑稻草的霉味,犯人上的酸臭味,以及,濃郁新鮮的腥味。
「狠狠給我打!」
獄頭一聲令下,沾了涼水的長鞭劃破空氣發出尖利的鳴聲,重重在漢子模糊的上,皮裂開的聲音聽得人心驚膽。
兇神惡煞的獄頭冷眼看著被打的半死不活的王浩,然而轉過頭時,卻換上了諂的笑容。
「高大人,這犯人著實,您看看怎麼辦?」
旁邊,一張紅木雕花靠椅上,高大人皺著眉,看著眼前這一目驚心的場景,手上雖然拿著一塊糕點,這會兒卻也沒胃口吃了。
胃裏泛起一陣陣酸水,他用帕子捂住鼻子,皺眉道:「用刑是不是太重了?」
「哎喲喂我的大人啊,這可一點兒都不重,只是看著滲人而已,小人們可早都習慣了。只是,這廝得狠,怎麼也撬不開,大人看看如何是好?」
獄卒賠笑著,小心翼翼回道。
高大人半晌無言,嘆了口氣道:「繼續吧,直到他將一切說出來為止。」
然而,卻是渾都不自在。
他一向坐於高堂,掌控犯人生殺大權,幾時親自來過這種腌臢地方?
若不是王浩這犯人與皇上有牽連,事關重大,他又如何會親自來審問。
Advertisement
只是看著眼前的況,審倒也審不出什麼東西來。
高大人無奈地想著,忽然聽到獄卒驚道:「這傢伙昏過去了。」
「用涼水潑醒繼續!」獄頭冷冰冰地說。
此時牢房,王浩灰白的囚早已被染紅褐,出布料外的皮都被一道道打綻開來,腥味刺鼻至極,甚至糊得人有些睜不開眼睛。高大人彷彿能看見腥傷口深出的白森森的人骨。
「停手吧。」
他擺了擺手,閉上眼,不忍再看。
獄卒一愣,連忙停手。
「大人這是......」為首獄卒賠笑著問道。
高大人站起來,背著雙手,板起了臉孔。
「弄醒他,讓本大人親自來審。」
朦朧中,王浩被涼水澆了一頭。
意識稍微清晰,與涼水相的傷口傳來火辣辣的疼痛,未及的傷口也在鑽心地刺痛,痛徹骨髓。
上的囚彷彿已經和粘在了一起,輕輕一扯,就有皮被撕下來的覺。
他......還活著嗎。
還是......已經死了。
也是,這便是地獄吧,只有地獄,才會讓人盡這樣的折磨。
「給我起來!」
耳邊模模糊糊傳來人的呼喝,有人狠狠踢了他一腳。
很奇怪,這次已經覺不到想像中的疼痛,好像已經不是自己的了。
王浩慢慢這睜開眼。
眼前是,紅的世界。
他不知道,在外人眼裏,此時他的雙眼已經被鮮染赤,配上他醜陋的容,彷彿地從地獄走出的惡鬼。
「給他喝點水吧。」又有人在說話。
他們在說誰,是自己嗎?
王浩茫然地想著,此時思緒一邊空白。
然而,很快到一個冰冷堅的,一清涼的傳來過來。
彷彿甘泉,泛著微微的甜意。
Advertisement
意識更加清晰。
牢房外,高大人憐憫地看著已不人形的王浩。
「若你坦白一切,本大人便赦你無罪!」
牢房,王浩慢慢地抬起頭,渾濁的雙眼茫然地盯著他。
然而,彷彿被什麼驚醒了一般,那雙的眼忽然綻出強烈的。
「咳咳......狗,咳咳......沒有什麼真相,老子什麼都不知道。」
王浩劇烈咳嗽,氣管好像了風,聲音更像是野的嘶吼。
鮮順著他的角溢出,滴落到前的襟上,和融為一。
「休要再狡辯,本已經知道,你此次前來是想為你的同黨掩蓋罪行!」
高大人提高聲音,神嚴厲。
「王浩!你可知,昨夜有一黑人闖進衙門要來殺你滅口!」
王浩猛然抬頭,可怖的臉上五扭曲,勉強能辨認出是震驚的神。
但他沒有說話,只是低下頭,像野一樣匍匐著。
「本不過是將你暫時收押,日後調查,便已經有人要前來殺你,可想而知,你的同黨是多麼怕你泄消息。」
高大人試圖觀察王浩的神,但模糊一片,委實看不清,只得繼續道。
「那人如此心狠手辣,你癡心為他頂罪,卻還想殺你滅口。這樣的人,如何值得你去維護!若是坦白真相,本定會為你討回公道。」
「公道......」
卻聽見王浩沙啞地低笑了一聲,竟有些不屑。
他的雙眼如荒原一般蒼涼,了無生機。。
「不用問了......再怎麼問......老子都不會說的......」
王浩劇烈地咳嗽著,慘笑道,神竟是不顧一切的絕。
「你!真是頑固不仁!」
高大人慍怒,這王浩果然至極,甚是難辦。
他沉著臉,在獄中走來走去,一時竟想不出辦法來。
猜你喜歡
-
完結1962 章

腹黑狂妃︰絕色大小姐
殺手?特工?天才?她都不是,她是笑顏如花、腹黑兇猛、狡猾如狐的蘭府家主。 想毀她清白的,被剁掉小指扔出去喂狗;想霸她家業的,被逼死在宗廟大殿;想黑她名節,讓她嫁不出去? sorry,她一不小心搞定了權傾天下、酷炫狂霸拽的攝政王大人! 他︰“夫人,外面盛傳我懼內!” 她眨巴眨巴眼楮,一臉無辜︰“哪個不長眼的亂嚼舌根,拉出去砍了!” 他︰“我!” 她︰“……”
180.4萬字8.09 132272 -
完結137 章

招魂
-落魄的閨閣小姐X死去的少年將軍-從五陵年少到叛國佞臣,徐鶴雪一生之罪惡罄竹難書。即便他已服罪身死十五年,大齊市井之間也仍有人談論他的舊聞,唾棄他的惡行。倪素從沒想過,徐鶴雪死去的第十五年,她會在茫茫雪野裡遇見他。沒有傳聞中那般凶神惡煞,更不是身長數丈,青面獠牙。他身上穿著她方才燒成灰燼的那件玄黑氅衣,提著一盞孤燈,風不動衣,雪不落肩,赤足走到她的面前:“你是誰?”倪素無數次後悔,如果早知那件衣裳是給徐鶴雪的,她一定不會燃起那盆火。可是後來,兄長失踪,宅田被佔,倪素跌落塵泥,最為狼狽不堪之時,身邊也只有孤魂徐鶴雪相伴。 伴她咬牙從泥濘里站起身,挺直腰,尋兄長,討公道。伴她雨雪,冬與春。倪素心願得償,與徐鶴雪分道揚鑣的那日,她身披嫁衣將要嫁給一位家世,姿儀,氣度都很好的求娶者。然而當夜,孤魂徐鶴雪坐在滿是霜華的樹蔭裡,看見那個一身紅的姑娘抱了滿懷的香燭不畏風雪跑來。“不成親了?”“要的。”徐鶴雪繃緊下頜,側過臉不欲再與她說話。然而樹下的姑娘仰望著他,沾了滿鬢雪水:“徐鶴雪,我有很多香燭,我可以養你很久,也不懼人鬼殊途,我們就如此一生,好不好?”——寒衣招魂,共我一生。 是救贖文,he。
50.1萬字8 22373 -
完結609 章
毒后歸來之鳳還朝
一朝錯愛,她為薄情郎擦劍指路,卻為他人做了嫁衣,落了個不得好死的下場。上蒼有眼,給了她一次重新開始的機會。這一次,有恩報恩,有仇報仇,她手持利刃,腳踏枯骨,鳳回天下。看慣了人們驚恐的目光,她本想孑然一生,卻陰差陽錯被個傻子絆住了腳步。這世上,竟真有不怕她的人?逆流而上,他不顧一切的握住了她的手。
153.9萬字8 14787 -
完結36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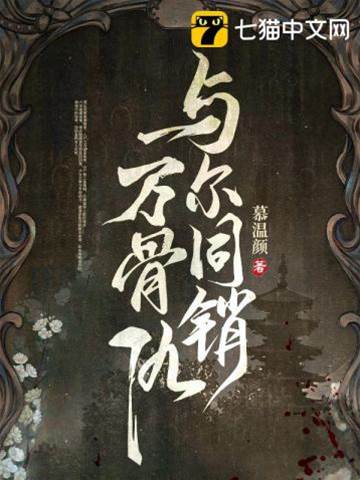
與爾同銷萬骨仇
深山荒野狐狸娶親,人屍之內竟是魚骨,女屍愛上盜墓賊,吊滿詭異人影的地宮...... 六宗詭譎命案,背後隱藏著更邪惡的陰謀。 少女天師與年輕尚書,循著陰陽異路解決命案,卻每每殊途同歸。 暗夜中的枯骨,你的悲鳴有人在聽。
32.6萬字8 7479 -
完結508 章

嫁給瘋批太子衝喜後
慕家不受寵的嫡女,被一道聖旨賜婚給命在旦夕的太子周璟沖喜。 不少人看笑話,可別把人給衝死在榻上。 周璟一睜眼,就多了個未婚妻。 小姑娘明明很怕他,卻還是忍不住的表忠心:“殿下,我會對你很好的。” “殿下,你去後我定多多燒紙錢,再爲您燒幾個美婢紙人。” “殿下,我會恪守婦道,日日緬懷亡夫!” 陰暗扭曲又裝病的瘋批周璟:…… 很久沒見上趕着找死的人了。 成親那天,鑼鼓喧天。 數百名刺客湧入隊伍,半柱香前還在裝模作樣咳血的太子劍氣淩厲,哪還有半點虛弱的樣子? 周璟提著沾血的劍,一步步走至嚇得花容失色的她跟前,擦去濺落她右側臉頰的血,低低似在為難:“哭什麽,是他們嚇著你了?”
84.6萬字8.18 1434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