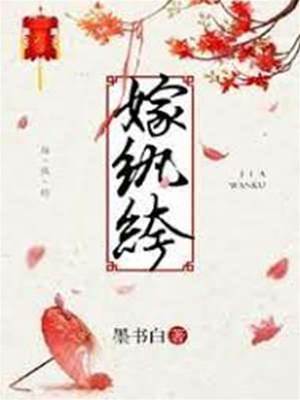《農家醫女:獵戶王爺掌心寶》 第三百零九章 往后別再與我生疏了
秦懷景抿,未曾說什麼,只是想好好看一看。
“有些話,楊越已經告訴你了。”他并非是陳述句,只是想知曉是不是。
程菀頷首,“樓死了,我們接下來很難找出月妃娘娘的破綻了。這個案子,應該是沒有后續了。”
為這件事愁,愁的臉頰都深陷進去了。這幾日事太多,照銅鏡的時候都發現自己瘦了。
原來這世上最好的消瘦訣就是——勞心。
已是冬日。鋪子門外迎來一陣寒風。程菀穿得不算太厚。
秦懷景淡淡拂下上的狐裘,走到前,罩住了這一抹小團子,在抬起頭疑的看著他的時候。
他扣住的后腦勺,單膝微屈,指腹挲著雪白紅的臉蛋,啞聲道:“信我麼?”
那沉寂在心頭的心跳,被他迎面撲灑來的炙熱氣息,像是點火了一樣重燃。
能聽到“撲通”響個不停,跳的聲音。
程菀鬼使神差的點頭,“我信你。”
自始至終,他做事,向來放心。
秦懷景勾一笑,大手捧著他的小人兒的腦袋,了,“菀菀,我不勉強你。王府,你想回就回,想走就走。想見我,我隨時會來。”
至于不想見他時,他也會暗暗的過來看幾眼。
程菀對上他的眼眸,被滾燙的目所燙到,偏開了頭去。
“你……手上的毒,確定已經好了吧。”耳廓微紅,程菀咳嗽一聲,看向別。
他這樣屈膝,從下往上看著。
手放在的腰后,像是他的專屬一樣。
秦懷景眉梢微,大手握住細膩的小手,“你不妨看看。”
Advertisement
像是電似的,程菀彈了開來。
用眼打量了幾下,咕噥道:“瞧著像是好了。我的藥應該不會出錯。”
昨日,他雖然進府見面。雖然知曉他沒有黑影所說的毒發,但明明是看見他的臉龐與都是蒼白的。
而且,還是白的很過分的那種。程菀就覺得,他是不是其他方面病了。
為此,想了一整夜。
秦懷景低笑一聲,勾了下漂亮的下,“本王的妻,醫湛,怎會出錯?”
被了下,程菀瞪他一眼。
“我沒有要跟你和好的意思,你別來。”挪著椅子,往后移。
離這個男人遠一點。
他卻跟著移,去哪兒,他就在哪兒。
程菀有些無奈,盯著這個厚臉皮的人,說道:“你不要得寸進尺。我只是為昨日的事到小小的愧疚而已,不是要給你好臉看,讓你開染坊的。”
又搬著椅子往后挪。
直到看到他沉默在原地,未曾再追著上前來。程菀的心口,又疼了起來。
秦懷景聲音沙沙的,低聲道:“菀菀。往后,別再與我生疏了。”
男人站起,走到的前。
不清楚他想要做什麼,程菀坐在椅子上,抬眼木訥的看著他。
只見,他眼神迷離灼熱,攫住了小巧的下,俯首一吻。
“咚咚!”
心跳到嗓子眼,程菀茫然的睜著眼睛,看著他。
秦懷景按住不安分的雙手,扣住的后腦勺,加深吻。仿佛要將吻到骨髓里去,深深刻在里,不讓離開。
程菀清醒了幾分,要推開他時,他卻主的分開。
Advertisement
看著微微著氣,紅著臉的樣子。秦懷景松開了,“只要這一點甜頭,足夠。”
再親,也要保持合適的距離。
之事,需要小火慢燉,急不得。
程菀抬起手背,捂著,含糊不清的說道:“你先走吧。我鋪子里還有要事要忙。”
那抹嫣紅的,有些腫。
秦懷景手,淡淡攏上的狐裘,深深看了一眼,轉負手離開。
外頭,寒風獵獵作響。吹他單薄的袍,一掩蓋的鐵骨。
程菀注視著他離開的背影,喃喃道:“原來,你也有這樣的時候。”
誰主,誰就輸了。
誰更深,誰就輸了一輩子。
……
兩日后,葡萄酒鋪前來了不尋常的一幫人。
鋪子的小掌柜在里間的簾子外頭喚著:“掌柜的,宮里來人了。”
門外,穿著統的玫紅對襟芙蓉花邊的宮婢候著,滿臉的坦然,不茍言笑,后跟著幾個侍衛,一齊等著。
程菀聽見宮里來人,立刻放下手頭的事,出去了外頭,一眼就看見打眼的宮婢。
“不知幾位,所來為何?”皺起了眉頭,鋪子安分守己,理當沒犯什麼過錯。
打前頭的宮婢掃了眼后頭的葡萄酒壇子,清高的扯著嗓子說道:“我家娘娘,想要在此訂購五十壇葡萄酒,為三日后的宮廷夜宴助興。”
娘娘?程菀做過宮里的生意,但不知這是哪位娘娘,便問道:“敢問,是哪個宮的娘娘。我讓人送去時,也方便。”
宮婢清了清聲音,說道:“當然是當今最得圣寵的,我家月妃娘娘了。”
Advertisement
月妃?!
程菀如同被什麼擊了一下。
這是巧合,還是?
宮婢兀自的將銀子用赤紅的布蓋著,遞給,“錢先給了,貨可別耽誤了。要是葡萄酒出什麼問題,你們酒鋪逃不了干系,可得仔細著些!”
“上回,就有一個做布料的丫頭,不小心心大意把針放在了裳里頭。娘娘得知,讓人親手一一,拔斷了那丫頭的十手指頭,那一個鮮淋漓……”
言語里,帶著恐嚇。宮婢的眼里犀利尖銳,看著程菀。
程菀卻表現的很是自若,“姑姑放心。我定會謹慎小心,不會給娘娘添麻煩的。”
宮婢冷哼一聲,“那就好。”
回頭,帶著侍衛一起走了。
端著手里沉甸甸的銀子,程菀尋思了下。如果是三日后的話,存貨夠。只是需要新鮮的口味更好。
把銀子放進賬房里頭,程菀問小掌柜的。
“郭興,我們工人每日能量產百壇酒。若是追求新鮮的話,你說我應不應該第二日開始命工人工最好?”征求他的意見。
小掌柜沉了一下,說道:“就怕臨時變故,姑娘還是明日讓人開始做。差一兩日的新鮮度應當差不多,口味不會變到哪里去。他們不懂酒的,自是不能辨出區別來。”
有道理。程菀緩緩點頭,“那你明日一早回去王府的酒坊,通知他們。務必比往日更加謹慎小心,這是宮里所需。要出了事集遭殃。”
這可玩笑不得的。
什麼生意都好做,唯獨皇商最難做。
小掌柜點頭,“是。”
待到第二日。程菀是被鼻子醒的。
Advertisement
有什麼茸茸的東西在掏的鼻尖,打個噴嚏坐起,對上了年清澈的笑容。
“卿卿。我回來了。”年雙手撐著過去,在榻上坐著,湊近,“你有沒有想小五?”
面對如此近的距離,程菀接不得。
火速地掀開褥子起去洗漱,邊問道:“你這幾日,去了哪里。”
年純粹一笑,眼里像是含著水。
親手遞過去給布巾,程菀接過。
倚在的旁,年陪著,說道:“只是傷口有些疼,早上起來時發現彈不得。一下,后背的傷就開裂。怕見到卿卿,要為我擔心。索養了幾日再來找你。”
程菀洗完臉,漱口。
“是嗎?”
走去桌旁,小掌柜已經買了小籠包。打開咬了幾口吃。
年笑著撐著手,看著的吃相,“我想你了。卿卿,你有沒有想我?”
程菀吃一口,噎住了,喝了碗豆漿。
“行行,我想你了行嗎?我在用膳,別跟我說話。”嗆得滿臉通紅。
年角的笑容更加清揚。
桌子底下,腳尖勾了過去,沿著程菀的小來回。
程菀正喝著豆漿,整個都吐了出去,臉發白的看著他,“誰教你這一套的?”
年眨著無辜的眼睛,小心翼翼的問道:“你不喜歡嗎?可他們說,這樣就表示喜歡。卿卿臉紅了,一定也覺得舒服。小五在給你舒緩呢。”
腳不喜歡,上手。
年的手了上去,握住程菀的小。程菀頓時怒了,放碗就走。
“卿卿!”有些著急了,年追過去,牽住的袖口,“對不起,小五錯了……你別生小五的氣。”
程菀背對著他,深呼吸。
正轉好好教導他一番時。小掌柜在門外匆匆的進門來,“掌柜的,不好了!”
眼看著人滿頭大汗。
程菀走近過去,問道:“郭興,怎麼了?有什麼事慢慢說。”
小掌柜郭興就著氣,道:“工人昨夜集罷工,留下字條就走了,連當月的工錢都不要了。今早的時候,人已經走空了!”
“什麼……?”程菀趔趄了一步。
年及時抱住了,不讓跌倒,“卿卿,沒事的。我在。”
培養一個人才很難,培養一群人才更難!何況這些人已經是練工了,流程、作,都無比的上手悉。
眼下,人走了?!
程菀凝重的質問道:“究竟怎麼回事,難道沒有說明原因麼。”
小掌柜正說什麼。
門外,王府的馬車停下。秦懷景負手,拔的形走進,瞥了一眼年,“菀菀,隨我出來一趟。有事。”
猜你喜歡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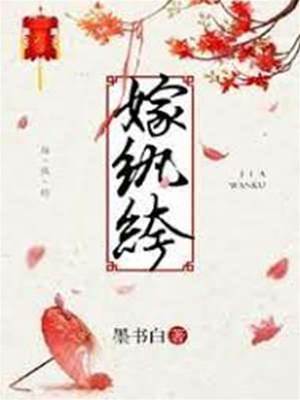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48727 -
完結737 章

妃常妖嬈:王爺盡折腰
現代具有特異功能的西醫一朝穿越到失寵和親公主身上。白蓮花一瓣一瓣撕下來。王爺高冷傲嬌也無妨,某女揮起小鞭子,收拾得服服貼貼。
127.4萬字8 102826 -
完結216 章

不夜墜玉
師蘿衣與錦鯉小師妹爭斗。 不甘心比了一輩子,敗了一輩子。青梅終究比不過天降,最后連她的竹馬未婚夫也不可救藥地愛上了小師妹。 破廟瀕死,無人殮骨。 就很氣啊! 她驟然想起,很久之前,自己也曾贏過一次:她不可描述了小師妹看得和眼珠子一樣的凡人兄長
33.5萬字8.33 879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