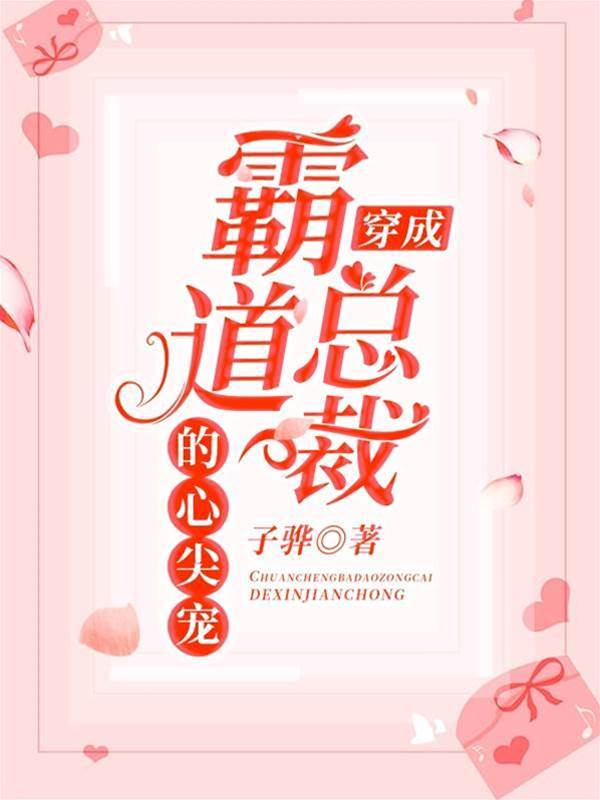《掌上嬌卿》 第90章 晉江正版90
玄塵微的角已經慢慢滲出跡,滴落在手中陶氏兄長畫押的信之上。
謝危樓眸鋒利,注視著他:“本王還不曾問,大師不是服用了延長壽命的丹藥麼,何故衰竭至此?”
玄塵幾乎沒有力氣說話了。
最后一枚忘心丸給大長公主之后,他才完全意識到,當年因一時念所犯下的罪孽,便是終極一生也難以解。
為此,他會不斷付出代價,甚至他能想到,將來有一天,他或許還做出十惡不赦的事來。
這一生罪孽深重,已經破了佛門的戒,他不能連人都不做。
于是他用銀針將的靈放出,當年那枚靈丹帶來的、所有不屬于他的生機也隨之迅速流逝,接下來的每一日,都似普通人的十年,到今日,五臟六腑徹底衰竭。
等到向謝危樓解釋完,他的氣息已經開始只進不出了。
Advertisement
這時候有暗衛叩門而,腳步非常急,附在謝危樓耳邊低聲稟告:“后山廂房出了事……下藥之人已經控制住了。”
謝危樓霍然起,立刻往外走:“夫人呢?”
暗衛道:“夫人怕沈老夫人和江姑娘那邊出事,聽到靜就過去了。”
謝危樓面幾乎在一瞬間沉,手掌攥,出門之后想到什麼,又轉過來,看著玄塵被染紅的長須,冷冷笑道:“大師若能再撐一會,或許本王還能看到一出一家三口相認的戲碼。”
謝危樓大手一揮,竹屋外立刻就有暗衛帶著方才記錄的證詞,拿過玄塵的手指,在那份證詞上畫了押。
按完指印,玄塵枯手垂下,徹底閉上了眼睛。
……
將催--藥撒在燃香的爐鼎之中,幾乎是寸草不留的對策,玉嬤嬤也是頭一回使用,卻不知這藥在爐火的催灼之下,更易揮發藥。
Advertisement
院中做使雜活的小沙彌已經有些暈暈乎乎了,玉嬤嬤捂口鼻躲在假山之后,目不轉睛地看著陵侯府的丫鬟端著疊放裳的托盤進屋,裊裊白煙從門中鉆了進去。
此刻謝斐房中也有了靜。
一路乏累,謝斐幾乎是將一盞茶喝到見底,開始只是下腹發熱,慢慢地連呼吸都有些沉,他攥拳閉了閉眼睛,再睜開時,凌安就已經發現了不對勁:“世子爺,您眼睛怎麼紅了?”
謝斐渾都在發燙,額間出了一層細的汗,手掌撐著桌面,連桌子也跟著搖搖晃晃,滔天的火自下而上,快要將他整個人吞噬。
他時常出煙花之地,都到這個份兒上還能猜不出麼,可這是佛門重地,怎麼會有這種腌-臜東西!
可現在不是追究的時候,催--藥無藥可解,唯有男-合。
Advertisement
凌安這些年跟在謝斐邊,助興的熏香見過不,有些人覺得這些手段下作,但也有公子哥就好這口。
他立刻反應過來,“爺是不是被人下藥了?”
謝斐攥著桌角,呼吸凌,只覺得腔都要炸了,他火燥地扯開礙事的領,果然口漲紅一片。
凌安忙開門到廊下喚人:“來人!來人!”
想讓人打一桶冷水進來,可那白霧飄過的地方,使的和尚們一個個頭重腳輕,雙頰紅,雙虛,哪里還有人回應。
凌安嗅到外面的白煙,察覺出不對,立即捂住口鼻,他深知這時候即便十桶冷水從頭澆到腳,對自家主子來說作用也不大.
電火石間,忽然就想起來隔壁院子住著的夫人。
“爺,院子里的香好像有問題,咱們現在該怎麼辦?”凌安關門,立刻回到謝斐邊,給他倒了杯茶:“先喝點水緩解一下。”
凌安毫沒有懷疑在這壺茶上,看著謝斐連灌了三杯。
猜你喜歡
-
完結1340 章

梧凰在上
斬靈臺前,眾叛親離,被誣陷的鳳傾羽仙骨被剔,仙根被毀,一身涅盤之力盡數被姐姐所奪。寂滅山巔,她的未婚夫君當著她好姐姐的面,將變成廢人的她打進葬魂淵中。挺過神魂獻祭之苦,挨過毒火淬體之痛,人人厭棄的她卻成了淵底眾老怪們最寵愛的掌上珠,而她卻放棄了安逸生活,選擇了最艱難的復仇之路......
192.8萬字8 14959 -
完結37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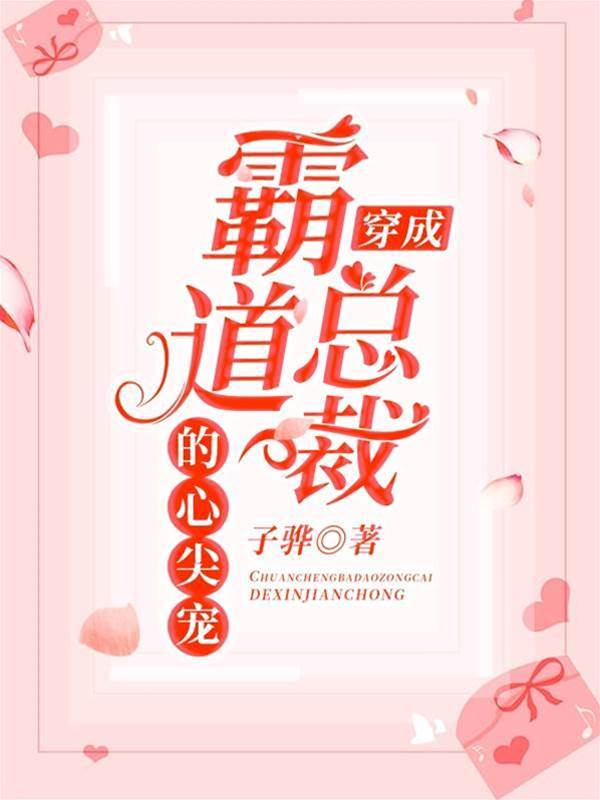
穿成霸道總裁的心尖寵
金尊玉貴的小公主一朝醒來發現自己穿越了? 身旁竟然躺著一個粗獷的野漢子?怎會被人捉奸在床? 丈夫英俊瀟灑,他怎會看得上這種胡子拉碴的臭男人? “老公,聽我解釋。” “離婚。” 程珍兒撲進男人的懷抱里,緊緊地環住他的腰,“老公,你這麼優秀,人家怎會看得上別人呢?” “老公,你的心跳得好快啊!” 男人一臉陰鷙,“離婚。” 此后,厲家那個懦弱成性、膽膽怯怯的少夫人不見了蹤影,變成了時而賣萌撒嬌時而任性善良的程珍兒。 冷若冰霜的霸道總裁好像變了一個人,不分場合的對她又摟又抱。 “老公,注意場合。” “不要!” 厲騰瀾送上深情一吻…
34.6萬字8 23508 -
完結165 章

名門醫妃
韓雪晴穿越到古代,成為寧瑾華的王妃,安然病了,韓雪晴是唯一一個能救她的人,生的希望握在她的手里。不過慶幸的是她曾是一名現代的優秀外科醫生,是一個拿著手術刀混飯吃的她在這里一般的傷病都難不到她,只是這個世界不是那般平靜如水,有人在嫉妒她,有人想讓她死……
44.6萬字8 8301 -
完結179 章

病美人嬌養手冊
南楚攝政王顧宴容操持權柄,殘暴不仁,其兇名市井盛傳。 皇帝爲攝政王選妃之宴上,世家貴女皆人人自危,低眉斂目不願中選。 獨獨鎮國公府裏那位嬌養深閨的病弱幺女,意味不明地抬了抬眼。 謝青綰天生孱弱,卻偏生一副清幽流麗的美貌,怎麼瞧都是懨懨可憐的模樣。 顧宴容奉旨將人迎入了攝政王府,好生供養,卻待這病美人全然沒甚麼心思。 只是他日漸發覺,少女籠煙斂霧的眉眼漂亮,含櫻的脣瓣漂亮,連粉白瑩潤的十指都漂亮得不像話。 某日謝青綰正噙着櫻桃院裏納涼,一貫淡漠的攝政王卻神色晦暗地湊過來。 他連日來看她的目光越發奇怪了。 少女斜倚玉榻,閒閒搖着團扇,不明所以地咬破了那枚櫻桃。 男人意味不明的目光細密地爬過她溼紅的脣瓣,聲色暗啞:“甜麼?”
27.7萬字8.18 588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