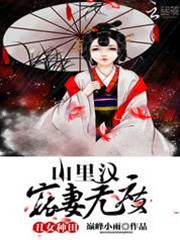《星漢燦爛,幸甚至哉》 第85章
皇后近侍的首領是一名和藹面瘦的宦者,名曹,管理宮中事宜,宣達皇后旨意,行奉引詹事之職,乃秩高達兩千石的大長秋是也,其下除宮婢之外還掌理許多黃門令小黃門以及中黃門。不過皇后素清凈端肅,既不手朝政也不喜頻繁宣召命婦宮八卦,所以曹大長秋的工作十分清閑,除了龐大宮廷的日常運作,就是每年為皇后張羅幾回盛大隆重的筵席。
皇后雖對曹并無不滿,但是多一事不如一事的,殿中的瑣碎事宜往往就近了結,不過如今翟媼漸老,力不足,而駱濟通婚期在即,留在宮中的時間是越來越,加上皇后有意讓商學著斷事用人,于是天時地利人和之下,商就順勢頂了上去。
起初商在宮里忐忑不安,是因為人生地不兼男大佬社會地位太高。在大姐頭那里犯了錯頂多被k一頓或逐出臺球室,在老師犯了錯不過訓斥一頓寫份檢查頂天了全校通報,可帝后卻是天下至尊公母,真惹急了可是管殺不管埋的那種。
如今既獲得了他們對自己努力的肯定,戒慎恐懼之心漸去,商自然而然開始流本了,雖非有意為之,但日常相難免出痕跡,天長日久,長秋宮眾人俱知這位看似□□弱的程娘子實實在在是個既促狹又腹黑之人。
有兩個宮婢打架,都說對方先的手,商二話不說讓們再打一架給看看,兩人都想示弱,于是一個比一個拳的慢落手的輕,仿佛電影慢作回放,又像意綿綿刀與**掌在喂招,直笑的殿一眾宮婢和小黃門笑的腹痛。
打完假拳,商問們還要不要告狀,兩人還說要請商給們主持公道,商笑瞇瞇的就把們送去給了曹手下掌管刑責的黃門令——別逗了,只是沒經驗,又不傻好嗎?皇后再溫和也不是能登鼻上臉的,宮闈這種地方,宮婢私底下有了爭執不但不遮掩還搶著鬧出來,當沒混過道嗎!
Advertisement
又有兩名外庭種植花卉的宮婢爭執一只漂亮小的貍花貓,一個說從宮墻角撿到后如何細心養,一個說省下口糧喂養如何辛苦,兩人都聲嘶力竭。商道:“這個好辦,你們倆說的都很有道理,這樣吧,將這只貍花貓對半切開,你們一人一半怎馬樣。”
說著,就宦者去拎刀來,兩個宮婢先是齊齊一愣,其中一名當即哭著跪下了,連聲道那貍花貓不是自己的,的確是另一人。而另一名宮婢始終遲疑不能言。
商便學著包老爺開庭的模樣,莊嚴的宣布不論原主是誰,那只貍花貓應該歸更疼它的主人,本庭不理再度上訴。
皇后在旁冷眼看著,忍不住哼哼道:“你倒有幾分急智。”
商:不敢不敢,只是站在了兒讀的肩膀上。
又有十五六個宮婢因為點蒜皮的小事在底下暗暗慪氣,分兩邊陣營對壘,連日冷言酸語,言語紛爭不斷。這種事很討厭,既沒升級為矛盾,但又影響宮氣氛。
商便人去尋了條自己小腕細的麻繩,足足有十來丈長,然后將這兩個陣營之人對半打散再組隊,然后讓們拔河。
第一注,商押勝隊每人可得五枚錢。
孩們如何肯跟鬧了幾日別扭的‘仇敵’們合力,別別扭扭使了些力氣,最后讓巧合力更大些那隊贏了去。
第二注,商押勝隊每人可得十枚錢。
眼看適才贏了的人領了叮了哐啷的錢幣在手上,另一隊孩眼珠都瞪大了,商再將們打組隊——依舊是當初兩陣營之人各半,這次不論是哪一隊都使出了吃的力氣。
第三注,商加注到勝隊每人可得二十枚錢。
Advertisement
孩們眼睛都紅了,哪怕在宮里這也是不小的一筆錢財了,這次分在同組的孩再顧不得舊日恩怨,紛紛同心同德,肩挨肩腳抵腳,齊心協力使力氣。
這時稍微出了些意外,商雖剛得了一筆橫財,但并未隨攜帶,便向翟媼借了錢做彩頭,可押到第三注時翟媼的錢袋已空,商只得人回家去取。誰知不過片刻之后,一名小黃門滿臉堆笑的捧來一口半臂寬的沉甸甸匣子,里面竟是近三百枚五銖錢。
“……凌大人都知曉這里的事了,他說您空口許諾未免掃興,便給您送些錢來,若是不夠他人快馬再去取。”
商捧著錢匣,發起愣來,所以說,終于也過上了花用男票錢財的日子咯?
三回拔河過后,孩們疲力竭,既無力再賭氣又多得了錢財,個個心中高興,便是那最倒霉的四個始終沒能贏錢的孩,商也一人賞了五枚。隨后,又板起面孔,舉事實講道理,說了好些冠冕堂皇要團結友互助互敬的話,直把大多數宮婢說出了眼淚——幾乎趕上當年鮭魚團支書的演講了。
施恩完畢,該使威了。
商又點出兩個陣營中素日領頭的幾個宮婢,責罰們一人十板,以儆效尤。
起初,商只是照計劃行事,誰知隨著拔河緒熾烈,周圍的小黃門和宮婢都圍攏過來笑看,還有為好的孩揮拳加油的,連皇后都忍不住站到廊下含笑觀賽,看到彩不免歡笑出聲,待到看商恩威并施解決了問題,便低頭對翟媼道:“放心吧,十一郎的府邸,以后不了。”
轉回殿時,皇后看見商猶自捧著那口空了一半的錢匣,靜靜佇立廊下,神清冷。皇后不由得微微一愣,一時間竟好像有些不認識了。
Advertisement
其實,這個孩理事時并非一直這樣明快果決計策百出的。
前幾日有個小宮婢生思念過世的家人,夜里啼哭不止,商制止了要杖責的宦者,耐心的問原籍何,然后畫了一副州郡簡圖,指著小宮婢的原籍告訴那里兵禍已漸消,可能還有些餒,不過以后只要好好耕種,再不會有無父無母的孩流離失所,被轉折販賣了。
——事自然不會如此,皇后自失父,也經歷過兵禍戰,深知世,世上哪會沒有人牙子呢。不過在這寂寞的深宮中,些許虛妄而好的言語就足夠給一個無親無故的小宮婢好好活下去的勇氣了。
皇后再去看商。有兩道婉的眉,不濃不淡的劃在雪白的皮上,宛如迷茫茫的煙雨留痕,雙目清澈秀,看人時仿佛眸中有水波流,才過了短短一夏,小小孩容更盛。再配上這樣矛盾復雜的,難怪迷住了養子。
……
午睡起后,商奉命去尚書臺外殿取兩筒竹簡,恭敬的拜別看管藏書殿的黃門侍郎后,商施施然的往回走,卻不想在宮巷里遇上了多日未見的袁慎。
其實自從宮‘進修’后,算上這次,已有三回在宮巷中遇上袁慎了。
頭一回是和凌不疑一后一前慢慢走著,袁慎側避過,然后冷冷的看了他們幾眼,不發一言;第二回是被凌不疑牢牢的抓著手并排而走,袁慎當路對上,看著他們握著的手發出數聲短促的冷笑,結果凌不疑凝視回去的目比這笑聲更冷。商扭頭不想看他倆。
這回遇上袁慎時,商剛被后追來的梁邱飛喊住,年侍衛跑的額頭冒汗,把手中一個扁扁的蒼枝盤紋漆木盒遞給。商一接過手來,就險些就把盒子砸在腳面上,打開一看竟是整整齊齊碼放的五十個金錠,散發著人澤的足金,每一枚都鑄拇指細的馬蹄金,小巧玲瓏,金閃閃。不由得張大了。
Advertisement
梁邱飛笑道:“……主公說,您如今在長秋宮里事多,賞賜宮婢用些銅錢尚可,可賞賜有秩的宦者可不行。這些您就放在宮中隨要隨取,平日托付翟媼保管即可。”
“這,這怎麼好意思?”商氣困難,呆笑數聲——當男票為你買包買服時,你尚可義正言辭的拒絕,堅定的主張婚前財務獨立,可男票直接過戶給你一套房子呢。覺得自己有些把持不住了。
梁邱飛皺眉道:“君不要再說這樣見外的話了,上回您不肯收那兩匹良駒,害的我兄長了主公一頓斥責。這回您可不要害卑職了。”
“放心,我不會的。”商無力嘆道。
待梁邱飛走后,一輕袍緩帶的袁慎風姿翩翩,緩緩走近時正看見被盒金錠照的滿臉金的孩,忍不住發問,待商后的宦者替答后,他再度冷笑起來:“沒想到你竟這些黃白之。”
商立刻道:“這盒里的都是金錠,只有黃的,哪有白的。你不要說哦!”
袁慎一噎:“……所以你就被收買了?日裝的一副賢良淑德的模樣,如今都城里倒是都在夸你,說你終于被皇后教養的品行出眾了。”
“什麼收買這麼難聽。”商將匣子給旁的宦者,然后示意他們退開些。
“沒有這些金錠,難道我就不能學著賢良淑德啦?再說了,這是我未來郎婿給的,我有什麼不能花用的。”有些話,果然是越說越理直氣壯的,“還有,我是不是賢良淑德,我有沒有被收買,關你什麼事!我吃你家粟米啦,我用你家財帛啦!”
袁慎這回卻沒有生氣,看著道:“你有沒有發覺,自你我相識以來,你最常對我說的,就是這句‘關你什麼事’。”
商一愣,……好像是的誒,“這是因為,你總是無緣無故來多管閑事!”
袁慎了腰上玉帶,低聲道:“你,如今過的好麼。”
“自然好!”商傲然一笑,“當初人人瞧不起的程家小娘子,連外出赴此筵席都有人跳出來說我鄙無文,蠻橫無禮,現在還會有嗎?現在我進出宮廷,就是皇子公主都對我客客氣氣的,當初那些人哪個還敢再來為難我!”
袁慎嗯了一聲:“其實,我覺得你以前好的。”
商嗤之以鼻:“善見公子,咱們還是就此打住吧。你自己擇妻都要東挑西揀,什麼宗婦德行,什麼禮儀嫻……憑什麼我就得一直鄙下去呀!”
“人前裝一下就好了,哪個讓你真的學什麼禮儀嫻啊。”袁慎恨恨道。
商恍然大悟,謔笑道:“哦,原來如此呀。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善見公子,莫非你自己就是如此行事的?…咦…我為什麼要學禮儀嫻,這與我有什麼干系。”
袁慎卻不去理的挑釁,再問:“你還沒回答我,你究竟過的好不好。不是人前,而是人后?你心里高興嗎。”
商抬眼看向宮墻,淡淡道:“我知道你想問什麼。不過,我也要告訴你,無論怎樣,我總是會讓我自己過的好的。這與旁人無關,與任何人都無關。”
袁慎凝視良久:“這年頭,說大話的小娘是越來越多了。如此,吾便拭目以待了。” 過渡章節結束,下章開始推進劇。
猜你喜歡
-
連載1129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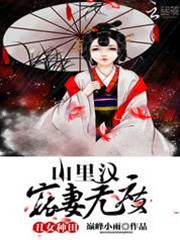
丑女種田:山里漢寵妻無度/錦繡農女種田忙
又胖又傻的丑女楊若晴在村子里備受嘲弄,被訂了娃娃親的男人逼迫跳河。再次醒來,身體里靈魂被頂級特工取代,面對一貧如洗的家境,她帶領全家,從一點一滴辛勤種田,漸漸的發家致富起來。在努力種田的同時,她治好暗傷,身材變好,成了大美人,山里的獵戶漢子在她從丑到美都不離不棄,寵溺無度,比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好多了,豈料獵戶漢子不單純,他的身份竟然不一般。
1988萬字8.46 774707 -
完結549 章

澹春山
春山澹冶而如笑,從累死的社畜到知府家的千金,檀悠悠非常稀罕現在的好日子。 呼奴使婢、山珍海味、歲月靜好,她所欲也! 當嫡姐把不想要的婚事推過來時,她正好夢見一隻香噴噴的烤雞腿,糊裡糊塗應了一聲好。 從此,不想宅斗的鹹魚遇上冰火兩重天的夫婿,一切都變得不同起來。
94.7萬字8.18 10545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