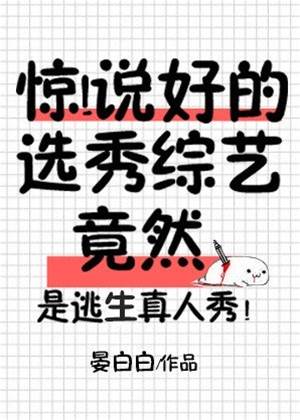《放肆》 第61章 夏夜長┃人啊人
陶然沒走, 但是留下來也沒辦法對盛昱龍笑臉相迎。盛昱龍問:“你這兩天怎麼老在外頭跑,下雨天你們都還去哪玩?”
“我沒玩,我想找個暑期工乾。”
這是陶然原來就有的打算。他們家如今不比以往, 他想學人家勤工儉學, 暑假打打工,賺一點是一點, 而且他聽說大學功課比高中松閑,也可以兼職, 他現在就練練手。
只是如今就業形勢嚴峻, 差不多的工作都搶著有人乾, 他也不大可能會像余和平那樣到工地上去搬磚,出環境也會影響人的擇業標準。
過了兩天,盛昱龍跟他說:“我給你找了個暑期工, 在一個餐廳裡端盤子,你乾不乾?”
陶然搖搖頭說:“不乾,我自己找。”
“一周乾四天,每天五十。”
陶然就驚訝地看向盛昱龍:“做什麼的?”
不是他沒骨氣, 而是一天五十,工資實在太高了。就算一周乾四天也兩百塊了,那一個月就是八九百, 比他爸媽的工資都高。天底下能有這樣的餡餅?
“是個高級餐廳的服務員,要求比較高,不是人人都能乾的,得懂點英語, 長的也得面,還得年輕,你條件正合適。”
陶然抿著想了想,盛昱龍問:“乾麼?”
“乾。”陶然說。
盛昱龍對他還是很好的,何況有他爸爸在,盛昱龍也不敢騙他。這種工作雖然天上掉餡餅,但盛昱龍本來就人脈廣,能找到這樣的好差事也不奇怪。
不過盛昱龍說:“你要乾呢,後天就能上班。不過我有個條件。”
陶然張地問:“什麼條件?”
盛昱龍就笑了,手指頭敲了敲自己旁邊的位置,好像個頤指氣使的大老板。
Advertisement
陶然不大願地坐到他邊,盛昱龍說:“你在家得給我好臉看。”
“可你威脅我。”陶然說。
盛昱龍說:“你幹嘛當威脅呢,你怎麼不想,是我一個人太孤單,所以想讓你上大學之前多陪陪我?你總不至於覺得那天是我故意弄你的吧?”
“弄”這個字明明很尋常,用在這裡就特別猥瑣。陶然臉上微熱,說:“沒有。”
他是真的沒有覺得盛昱龍是故意跟他發生那些事的,在他心裡,盛昱龍雖然渾,但也是個正常的男人,不至於會有那麼匪夷所思的念頭。他還是覺得主要是因為那天他們兩個都喝多了,兩個喝多了的男人做了一件糊塗事,只是區別在於他對這件事諱莫如深,盛昱龍卻不在乎。
“我就是搞不懂你。”他說,雲裡霧裡,他真的有些看不懂盛昱龍在想些什麼。
“哪能都讓你搞懂。”盛昱龍說。
陶然有些局促地坐在那裡,渾都是繃的狀態,明顯很防備他。盛昱龍心裡一,就說:“陶陶,你覺得我是壞蛋麼,會害你麼?”
陶然搖搖頭,看了看盛昱龍,不知道為什麼臉上的神很有些無力悲傷。
盛昱龍就說:“有些事不是想避免就能避免得了的,已經發生的東西,如果不能改變,就只能盡自己所能做到最好。”
陶然不大明白盛昱龍說的是什麼意思,是說他們倆已經睡過一次,就要接這件事麼?可是他們倆又不是真的發生了關系。
只是親親,不算發生關系吧?
不過這事他即便是隨便想一想也覺得非常難為。他跟盛昱龍摟在一起,親親,或許還有更過分的事發生,這畫面一旦浮現在他腦海裡,他都恥到打哆嗦,不止恥,還覺得丟人。
Advertisement
“你真的只是因為覺得寂寞,想讓人陪麼?”他問盛昱龍,“那我爸媽給你介紹對象,你又都不願意……”
“我覺得們都還不如你。”盛昱龍說。
陶然愣了一下:“們怎麼會不如我呢?”
們都是人啊,就單別上就甩他十萬八千裡。他甚至都不覺得應該拿他和那些人相比,都不屬於同一個種類。
“你還不懂。”盛昱龍說,“以後會懂的。”
陶然沉默了一會,臉慢慢地變紅,抬頭問盛昱龍:“你不會還想跟我一起睡吧?”
盛昱龍問:“你要聽實話麼?”
陶然低下頭來,不說不要,也不說要。
然後盛昱龍就說:“我天天都想跟你一起睡。”
陶然驚駭地看向盛昱龍,盛昱龍問:“你說我是怎麼了,是不是病了?”
相比較於陶然,盛昱龍在人上經驗富,他語氣曖昧又正經,尺度拿的剛剛好:“陶陶,你說我是不是病了?我怎麼會想跟你一起睡呢,你沒比也沒的。”
陶然臊的滿臉通紅,他無法相信盛昱龍會跟他說這麼魯的話。他站了起來,卻被盛昱龍抓住了手,他卻像是電一樣一把甩開他,跑到自己臥室裡去了。
盛昱龍給他介紹那個餐廳果然是高檔餐廳,發統一的製服,正式上班之前要先培訓一周。經理對他很照顧,他原以為這種走人過來的員工質量不會怎麼樣,沒想到陶然本人那麼帥氣白淨,簡直可以做他們餐廳的門面。
這家“聚福樓“的餐廳坐落在市政府大樓後面最繁華的十字路口,經常招待政府要員和外國來賓。陶然發現他們有員工宿舍,就問經理他能不能住在這裡。
“你不是在龍哥那裡住麼?”經理問。
Advertisement
“我想住在員工宿舍裡。”陶然說。
結果他們經理令他很失地說:“這個不好說,因為你是特招進來的,員工宿舍沒有空床位了,而且我們員工宿舍條件一般,跟你現在住的地方可沒法比。”
這經理轉頭就告訴了盛昱龍。他培訓完回到家裡,盛昱龍就問他:“聽說你想住員工宿舍?”
陶然說:“我就是問問。”
“住什麼員工宿舍,”盛昱龍說,“不準。”
陶然的手指微微蜷起來,沒說話。
他還在驚慌失措的階段,對於盛昱龍基本上是屈從於他的威之下。不過他有一點是確定的,就是如果他不願意,盛昱龍應該不會他。他覺得盛昱龍雖然有點不要臉,但不是壞人。最重要的是他不能喝酒。
就在他準備上班的時候,劉娟打了電話過來,說陶建國在工地上被砸傷了。
他是抬樓板的時候被砸傷的,倒不嚴重,只是砸傷了腳趾頭,陶然回去看了一下,陶建國半邊腳都腫了起來,走不了路。
“拍片了麼?”盛昱龍問。
“拍什麼片,不是大病。”陶建國說。
“那也得拍個片子,你這腳都腫這樣了。”盛昱龍說著就把陶建國帶到縣醫院去了。陶然和劉娟在家裡等,陶然發現劉娟也瘦了好多,黑了很多,白頭髮已經遮掩不住了。
平時生活還不錯的人,一旦遇到變故,老的就格外快。
他把盛昱龍給他找了個暑期工的事告訴了劉娟,劉娟很吃驚地說:“工資這麼高?老六真是有心了。”
陶然說:“我都可以賺錢了,你和爸爸就不要那麼辛苦了。”
劉娟笑著說:“哪有人嫌錢多的。你爸這腳一傷,這幾個月恐怕是乾不了活了。”
Advertisement
陶建國和盛昱龍從醫院回來,說沒什麼事,他們娘倆放心。吃飯的時候陶建國要喝酒,劉娟說:“你還喝呢,都這樣了還喝?”
“喝點啤的,沒事。”陶建國最後到底還是打開了兩瓶啤酒。盛昱龍問陶然喝不喝,陶然很防備地看著他,說:“我以後滴酒不沾。”
劉娟愣了一下,笑著問:“為什麼呀?”
“他前段時間喝醉過一次,”盛昱龍說,“估計是怕了。”
“怎麼喝醉了?”劉娟有些不高興,說,“你可別學你爸,你不是不喜歡喝酒的麼?”
“被六叔灌的。”陶然說。其實他真的有些懷疑當時盛昱龍有故意灌他的嫌疑。
盛昱龍說:“在自己家,沒外人,就讓他多喝了幾杯,誰知道他酒量這麼淺。”
“現在練練酒量也好,男人哪有不喝酒的,”陶建國說,“以後上了大學,同學們出去喝酒,你要是喝幾口就醉了那可怎麼行,又沒人照顧你。”
“他喝醉酒什麼樣啊?”劉娟笑著問盛昱龍,“發酒瘋麼?”
盛昱龍笑著說:“不發,老老實實的,很安靜。”
陶然臉微紅,看了盛昱龍一眼,心裡又畏懼盛昱龍說更多,又有些驕矜,看了他一眼,不悅地扭過頭去。
吃完飯陶然幫劉娟收拾碗筷,陶建國和盛昱龍在客廳裡說話,陶然聽見盛昱龍又在跟陶建國說工作的事。
“咱們市裡年初不是最近駐了一個大型超市麼,雖然比不上這兩年駐長海的家樂福這些知名大超市,不過地理位置不錯,生意特別好,我有朋友的親戚在裡頭賣菜,說最近這超市裡空出個鋪位,招商戶駐,除了第一個月給場費,剩下的每個月給租金就行了。我想著大嫂最近一直在賣菜,也有經驗,在街上賣菜,刮風下雨的就耽誤生意,每天還得風吹日曬的太辛苦,不如買個鋪子,大超市不缺生意。”
劉娟在廚房聽見了之後立馬就走了出來,在旁邊坐下。原來對這些都不了解,自己賣了一段時間的菜,這裡頭的門道就懂了很多,能進大超市去賣,當然是他們這些小攤販求之不得的。
“就是不知道得多錢一個月,場費又是多?”
“我是這麼想的,場費和租金我來給,等你們以後賺了錢,再慢慢還。這真是個好機會,我朋友說很賺錢,也穩定,將來超市肯定是越來越火的。”
劉娟很心,看向陶建國。陶建國說:“哪能讓你掏錢,你讓我和你嫂子想一想。”
盛昱龍點點頭:“那得快點了,這鋪子很缺,過幾天那兩個商鋪的老板就要走了。”
“既然生意這麼好,他們怎麼舍得走呢?”
“聽說是一家人要到上海去了,他們兒子在上海落了戶,如今有了孩子,老兩口要去照顧。”
陶然一邊著碗一邊在廚房門口聽,漸漸地紅了臉,臉卻沉的厲害。
吃完飯他們就要回去了。等到車子開出了縣城,陶然終於忍不住說:“你要幹什麼?”
盛昱龍一愣,問:“什麼幹什麼?”
“你把我爸媽都弄過去,是想幹什麼?”
盛昱龍說:“我給他們找個工作。”
“你為什麼給他們找工作?”
盛昱龍笑了,說:“你怎麼了?”
陶然沉著一張臉說:“你不要想著把我爸媽攥在手心裡,我就怕你了。”
盛昱龍愣了一下,將車子停在了路邊。外頭天沉,好像又要下雨了。他坐在那兒沉默了一會,說:“你覺得我有那麼卑鄙麼?”
“你難道不卑鄙麼?”陶然問。
盛昱龍沉著一張臉,默默無言。
“你怎麼不說話?”
“你讓我說什麼呢,說我卑鄙麼?”盛昱龍說,“我是卑鄙的,我就這麼一個人,你今天才知道麼?”
他從來就不是道德楷模,完男人,他一直走的就是個路子。為什麼陶然以前喜歡的是這樣的他,如今不喜歡的也是這樣的他?
陶然沉默了一會,有些沮喪地說:“你怎麼變了,你原來不是這樣的。”
“我早就變了,我也從來都沒有變,只是你不知道。”盛昱龍說,“我對你不尋常的心思,難道你一直都沒有察覺?還是你期我做個聖人,在喝多了酒的時候也能控制自己的,做一個柳下惠?如果我一直克制著什麼都不做,你認為我會得到什麼?我如果跟你說我你,讓我親一下,你會願意麼?”
陶然驚駭地說不出話來,盛昱龍說:“我是人,是個男人,你以為我是想親你,就毫無心理負擔地親下去了?你以為我就毫無廉恥,毫無顧忌?”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